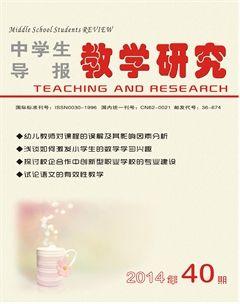浅析《诗经》的用诗之兴与作诗之兴
孙彩云
摘要:通常人们到《诗经》,总会提到“兴”这个词,但是有人往往分不清用诗之兴与作诗之兴的区别,一概而论之。笔者阅读了袁长江先生的“兴”的原始意义及兴意的引申和转换这部分内容受益匪浅,觉得很有必要把用诗之兴与作诗之兴提出来进一步讨论和学习。希望本文能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诗经》的“兴”提供帮助。
关键词:《诗经》;用诗之兴;作诗之兴
我们提到《诗经》,“兴”是绕不开的话题。在诗经学史上,一次最具权威性的整合,就是“三经三纬”说的诞生。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明确提出了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① 。这是现存文献中第一次对《诗》之“六义”进行性质上的区别,认为风、雅、颂是三种诗歌体裁,而赋、比、兴只是组成这些体裁的“成形”,即语言艺术表现技巧、手段或修辞手法。这种观念经南宋朱熹在《诗集传》中进一步继承和发挥,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三经三纬”说。现代的著名文学家鲁迅,也大体认可和继承了这种观念。鲁讯认为:“风雅颂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② “三经三纬”说把《诗经》中的“兴”界定为一种修辞手法,并在近千年来一直成为诗经学界的一种主流观念。近人也基本上认为兴是诗歌创作的一种表现方法。但是兴仅仅是作为一种作诗的表现方法,一种修辞手法吗?《诗经》的一些研究者提出有用诗之兴与作诗之兴的区别。我认为这个说法让我对兴的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非常有见地,值得深入探讨。
我们可以发现《诗经》编订与诞生的有周一代,《诗经》已经深入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只是“言志”、“咏言”、“抒情”。当时的用诗情况有祭祀用诗、大射礼用诗、燕飨用诗、人际交往用诗、教育用诗、论说用诗、为文用诗、其他用诗。周人制礼作乐,盛行王官之学,作为王官之学之一的“诗”曾是礼乐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通过贵族教育渐渐成为贵族子弟必备的文化修养。孔子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还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由于《诗经》在西周,春秋时代有特殊的作用,一直被人所重视。孔子根据当时《诗经》的使用情况,概括出“兴观群怨”四种功能。“兴”,这是古今学者谈论最多的。在孔子论诗,《毛诗序》之前,也有关于兴的说法。《周礼·大师》中有“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袁长江先生根据周大师的职责范围,推断“兴”是指乐队演奏时的启奏和指挥。《周礼·大司乐》中有“以乐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根据周代太学的教育目的是造士,学是为了将来做官,不是为了做诗人,推断“乐语”中的“兴”不是讲诗的艺术特征,而是学习“兴”的另一种意义,即用诗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以兴用诗。
用诗之兴
什么是以兴用诗呢?
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的“兴”就是从用诗之兴的角度说的。如,在《论语》中子贡提出“贫而无諂,富而无骄”。孔子首先肯定,接着指出“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师徒二人是在谈论道德修养,子贡提出的标准已属不低,但孔子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子贡想到《诗经·淇奥》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便问孔子这两句是否指此而言,得到孔子赞许。再如,《诗经·八佾》篇中,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说:“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画花。”子夏接着问:“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说,启发我的是卜商,“始可与言《诗》已矣”。从诗的某一句或某一个词出发,展开丰富的想象,让其为我所用,这就是先秦人用《诗》的普遍方法,而孔子尤其注重。这种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用诗方法,就是以兴用诗。杨伯峻先生把“兴”解作联想力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可以发现联想力在赋诗取义以便为我所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读《诗》,用《诗》渐渐成为贵族子弟必备的文化修养,赋诗取义也是上流社会人们交流的必备的能力,也即以兴用诗成为人们的一种默契和必须。
在《毛诗序》中作者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作者在《序》里没有解说赋、比、兴,但在作《传》时却下注了一百一十多个“兴”字,袁长江先生经过分析这些“兴”的涵义,得出这些“兴”的涵义实际就是指诗歌创作时使用的比喻,象征手法,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诗歌的表现方法。因为赋诗言志的环境氛围的消失,以兴用诗也渐式微,而作为艺术创作方法的“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诞生了,也就是此后人们开始有意识的使用“兴”这种艺术创作方法。
作诗之兴
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使用“兴”这种艺术方法是从《诗经》开始的,不过人们在创作过程中,是无意识的使用了“兴”这种艺术方法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无意识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特殊的地形,适宜的气候,决定了我国远古时代只能成为典型的农业国家,安土重迁,依寻时令,热爱自然就自然而然成为远古人们的本性和追求。于是,在这样的追求与思考中,天人合一的思维观念就成为人们的集体意识,成为一种远古较统一的精神观念。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回答,为什么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的诗人们更愿意把抒情的眼光投向一花一叶、一虫一鸟的世界。是因为他们总是依照自然的节律,安排自己的农耕生活。也就是说《诗经》的诗人們已经无意识的使用了“兴”这样的思维方式与作诗的艺术方式,是《毛诗序》的作者第一次把“兴”作为诗歌创作的艺术方式提到了文学理论的高度。
《诗经》中有很多地方用到了“兴”这种思维方式和艺术方式。我们可以把“兴”在《诗经》里的使用情况分为以下三类。
(一)起兴物与下文要表达的内容没有直接的意义上的联系,只是起到一个发端的作用,或仅仅是一种韵脚上的关系。如: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鄘风·桑中》)
山有苞棣,隰有树檖。未见君子,忧心如醉。(《秦风·晨风》)
采苓采苓,首阳之巅。人为之言,苟亦无信。(《唐风·采苓》)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小雅·南山有台》)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与后面的“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无论从情感上,或是地理上都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唐”、“乡”、“姜”押韵。同样,“山有苞棣,隰有树檖”与“见君子”也没有什么联系。“采苓”与“人之为言”也无瓜葛。“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与“君子”也没有必然联系。
(二)他物与所咏之事仅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便被借以起兴。如:纠纠葛屨,可以履霜。掺掺素手,可以缝裳。(《魏风·葛屨》)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小雅·湛露》)
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豳风·狼跋》)
用葛麻做的鞋子可以踏霜,比喻纤纤素手,却可以做衣裳。用露水不见太阳不干,喻那些喝酒的人不醉不归。用老狼喻王公大人的肥硕等,比喻形象生动。
(三)起兴物对下文所抒发的情感有渲染和烘托的作用。如: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
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卫风·氓》)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小雅·青蝇》)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小雅·鹿鸣》)
桃之夭夭,有贲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陈凤·月出》)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栖于埘,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风·君子于役》)
诗人以桑叶正值茂盛的时节,来烘托渲染女子青春美好。到了秋天,桑叶变黄,并且落了。诗人就以桑叶的枯黄凋落,引出男子因女子的青春不再而喜新厌旧,并烘托出一种悲凉萧条的气氛。青蝇是人们心里讨厌的东西,而谗言又甚于此。二者在人们心里上有相同的反应,所以用青蝇起兴能增强了感情效果。鹿是人们喜爱的动物,嘉宾又受人的欢迎,所以感情上也有相通之处。桃树茂盛,又结了果子,这是令人喜悦的。贤惠的姑娘出嫁,又令人满意。烘托出女子出嫁的热闹美好的气氛,也表达了诗人希望女子早生贵子的殷切祝愿。《月出》是一幅月下美人图,所思之人在月下更显的幽娴,静美。鸡进窝,牛羊下山,不由想到行人应回家,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行役在外的丈夫身上。
综上,我们论述了“兴”有用诗之兴和作诗之兴的区别。袁长江先生说:“作诗之兴是作者见到或想到外物而引起自己的灵感,因而要作诗表达;用诗之兴是想要表达自己的见解或意愿时,而联想到了《诗经》中某些相类的诗句。”③说的非常的清楚,便于我们深刻的理解“兴”的真正含义。在西周与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下,贵族统治者言必用诗,以兴用诗,在先秦时期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作诗之兴的发现,使“兴”逐渐成为我国诗歌艺术的美学理论,此外,“兴”作为一种“由此及彼”“联想式”的运思方式对文艺思想理论也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注解:
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上),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
②《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
③袁长江《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学范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参考文献:
[1]李春青.先秦文艺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袁长江.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M].北京:学范出版社,1999
[3]郑志强.《诗经》兴体诗综考[J].浙江社会科学,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