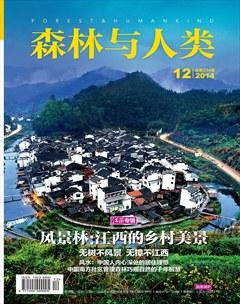树永远的乡村风景



最近的几年间,我频频造访幸存于江西大地上的乡间的老房子。许多形胜之地已经面目全非,许多风水建筑已经荡然无存。然而,即便四周是光秃秃的荒山,村庄的后山仍有一片密林。即便临村的溪水几乎枯竭,岸边却是一行行、一团团、一簇簇的绿意。至于水口建筑的遗址上,更有参天古树,郁郁葱葱。
树木是一种建筑
是永远的宝塔高阁、桥亭庙宇
吉水县尚贤乡一带,多荒山秃岭,连绵起伏的丘陵上树高不盈尺、粗不过拳,惟有栗下村周围古松、古樟、古枫、古柏和桂花树有近千株,或虬干曲枝,或蓊蓊郁郁,其中有一棵古樟浓荫遮亩,甚为罕见。而与宗祠正门相对的山头上,一株古柏历经数百年树不见长高、叶不见脱落,年年岁岁相似,被当地人敬作神树。
那许多被村人倍加呵护的树,恐怕就是他们根据村庄的布局而栽种在吉祥的心愿里的。否则,很难解释包围着栗下村的荒芜,如何甘愿驻足于村外而不继续进犯。恰好,栗下村的一些建筑物,为我的判断提供了证明。该村的地势是东高西低,水向西流,人们认为财势、运气、门风都会随水西去。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清朝同治年间,村里一位衣锦还乡的生意人,组织人在村头西流之水汇成的小溪上修筑了一道人工堤,沿堤由西向东开挖一条水渠,改变水的流向,并且在堤上栽下很多树。也许是担心这还不足以藏风聚气吧,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又在堤的对面修建了凉亭、砖塔、牌坊和庙宇,使之形成多道屏障,堵住了风水的流逝。用心的造势,刻意的经营,成就了一道引人入胜的风景。堤上古木参天,与凉亭、砖塔、庙宇相映成趣。我不由地想,在这里,树木不也是一种建筑吗?是永远的宝塔高阁,永远的桥亭庙宇。还有什么建筑能像树木那样,历数百年、上千年,任凭风蚀雨侵,任凭风云流变,用发达的根系汲取着大地的生气,即便浴火也能重生?
乐安县牛田镇的流坑村,在乌江之畔。流坑的东侧,乌江自南向北、再转西绕村北流去,村庄的西侧有一条长湖,江湖相通,合抱着村庄。这番地形水势被堪舆大师杨筠松认定,“活水出簰形,簰中人富贵”。有如石印般的两块巨石挡住乌江水流,使之折而西流的景象,被杨筠松诠释为“印浮水面,焕乎其文章”。乌江流至村庄西北角江面狭窄了,成为流坑的出水口,于是这片河谷地又被杨筠松喻作“鱼袋”,它的好处是“鱼袋若见兑,位卿相可期”。因此,他认为保固“鱼袋”地势,关系到将来流坑的兴旺,而把好水口尤为重要。于是,村人在水口处栽树植竹,蓄成一片洲林,抵挡泛滥的江水,保住“鱼袋”地形。两宋时极其兴盛的董氏大家族,到了元代日渐衰落,并遭草寇的屠戮,以至族人流散,村野荒凉。流坑人很自然地把那段屈辱的历史和风水联系起来了,认定那劫难缘于洲林被水毁之故。入明以后,洲林得到培蓄维护,林木再茂,江水复归西流,流坑董氏重又振兴。历经了盛衰兴废,人们对杨筠松更是顶礼膜拜,说是如此变故,恰恰被他言中。他说过:“五百年中犹解败,辛戍水流大,若见水流庚,依旧好流坑。”
吉安县钓源村,刻意于依山就势,把村庄建成了太极八卦形局。此地有一座东西走向、呈“S”形的长安岭,于是,钓源顺应山势,在它的两个臂弯里建起了两个自然村,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一般。而长安岭上数以万计的樟树,仿佛一道天然中分线。在钓源村,随处可见高耸的照壁,是为另一独特景观,其游离于建筑群而独立散在的形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村庄为补风水而筑的小堤,两者的设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建造它们的目的大约也是一致的,无非是要藏风聚气,力求风和圆满。
毋庸置疑,风水观念培育了人们亲和自然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假如,没有堪舆先生对山川形势的诠释,流坑的那片洲林未必能够得到人們的悉心维护,倍加钟爱。而钓源村像阴阳鱼一样游弋在“S”形的长安岭下,显然,它拿山上那数以万计的樟树当作自己的风水林了。
在江西的乡野间,风水林随处可见。虽为常见,深入其中却屡屡叫人惊奇。婺源石城村水口一侧,有古树百余棵,形成半里之长的树廊,树种也十分丰富,有枫香、白玉兰、山樱花、银杏、香榧、红豆杉、楠、槐、栲等,树林旁边是高高低低的岩石,村庄紧邻山冈,山上树,树上山,层层叠叠。下晓起村的段莘水与村溪汇合处,樟、槠、槐等十余棵古树护牢村基。虹关和严田的水口,各有四五人方能合抱的千年古樟,古樟旁又有树群。长溪村原名马源村,狭长的村庄坐落在长长的溪河一边,穿村沿溪上去,可见有巨石卧于溪河中,仿佛是长溪村的石神,乃“将军石”。与巨石相伴的,是村头5棵古枫,那是该村始祖栽下的,村人称之为“五虎”。故而,此地有“五虎守村头,将军把水口”的说法。它们是长溪村千年来兴旺平安的保证。在婺源,不仅水口,连溪河两岸,也遍植林木。拥有36座半石拱桥的坑头,四面环山,双溪合流穿村而过,古称“桃溪”。原来,晋代潘岳带领村人沿着小溪遍植桃树。也许,在坑头人眼里,正是那灼灼耀耀的无边红花,唤来了得意春风,为族人铺就了“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的锦绣前程。下晓起的后龙山上,竟是一座自然生态的古树园,并依树种可分为3个园中园。其中包括,千年以上的古枫树200多棵,红豆杉、槠树、红楠、漆树等30多个树种的杂树300多棵,还有众多的樟树。有3棵平均树龄370岁的樟树,恍若三足鼎立,该村汪、俞、江三姓便将其视作了“三姓树”,象征着三姓人家基业稳固,世代和睦。
森林是山水的前胸
树木是环境的姿容
赣江边的泰和麻洲,有樟、枫、桂、柞等20多种树,蓊蓊郁郁的一片,怕有数百亩吧。如今,一些古树已被编号,我看到一则写在树干上的禁令:“严禁——乱砍乱伐,挖沙取土,捕鸟挖药,违者罚款。”落款为金滩村。无疑,这里就是金滩村的风水林了。此禁令是最近立下的,而在祖先制定的族规、祠规中,一定有着更为严厉的警告,否则,这片古树林早就该作古了。果然,金滩朱氏于900年前在此开基,就在赣江边的这片沙丘上植树造林以抵御洪水和风沙,族规中有世代相袭的禁约,称:“金滩,后有柳洲坝,弈林惧其砍伐,宜培植禁约,长此下去,是卫前翊后之要,子孙所当时守,勿替者也!”遵照祖训,直到如今,林中仍有人守护。传说,十四祖懋林公发现自己的孙子砍伐了一棵樟树,毅然召集族人开会,当场对孙子处以斩首,故而,此洲又名“斩子洲”。
瑶里古镇汪胡村的风水林,竟是一座树种丰富、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泉声瀑影、奇石峭岩藏于一座并不高大的山中,那可能是世上最为精致的原始森林了。深秋在这里俯拾即是,它是各色的叶子,各色的果实。
瑶里是有一条古驿道通往徽州的古镇,曾有200多座古窑遍布在群山中,曾有许多架木制水轮飞旋在溪流边。自战国时期开始点火烧窑,长盛不衰,直至明初景德镇兴建官窑,随着窑厂纷纷迁往百里外的大江边,瑶里萧条冷清了。往昔的红红火火,变成了漫山遍野的历史碎片。令我惊奇的是,那么繁盛的一段历史,竟被繁茂的植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满山瓦砾上竟长出了无边秀色。
我浪漫地怀想着民间的浪漫。我想,当窑厂纷纷迁徙,也许有一些陶瓷艺术家没有走,领着他们的子子孙孙,以山为坯,以水为料,在蛮荒的高山上画着釉下彩,画在煅烧过的丘陵间,就是釉上彩了。否则,很难设想,被窑火熏黑、被瓦砾覆盖的古镇,会有这种血脉相承的自觉。或者,他们养山养水,是为了保养永远激荡于内心的艺术感觉,为了保养崇尚山水师法自然的人生境界。
而在汪胡的原始森林里,我听到的也是“杀子禁伐”的血腥故事——明初的汪胡村长亲手杀死了上山伐木的儿子,以儆效尤。从此,那座山被当地人命名为“罪山”。这座山成了一棵树的纪念碑,这片林成了一个人的墓志铭。
类似的故事可能会在每一座风水林中生长,因为它本来就是千年古树上的寄生藤。汪口村的溪河边,有座向山,沿溪逶迤800米,像屏风护卫着村庄,山上林木蓊郁。然而,它原来不过是一座寸草不生石壁山。传说,明朝时一位在京为官的族人还乡时见此情景,动了改造它的念头,便发动村人用桐油拌石灰砌石垒成篼窟,填进泥土,栽苗成林,并规定在外谋生的族人每次回家都要带上一二种不同的树苗栽上。族人乐此不疲,愚公似的,持之以恒地做着这件事,想想看,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以致于如今山上树种繁多,有专家认定此山树种达250多种,其中还有数十种为名贵树种。为了繁育成林,封山的禁令被郑重地写进了族规中。那禁令也是噬血的大刀,历史上它就曾砍断了一个违禁村人的手臂。
我在金溪县的蒲塘村,看到刻在石碑上的禁伐令,也是字字铁面无情,毫不暧昧,称:“合众严禁:墩埂岭山不许窃取一枝一叶,犯者罚银十两,不服者,送官究治。”从语气上看,显然是当时族中制定的规矩。刻着禁令的石碑镶嵌在村口西成门的墙体上,据蒲塘徐氏族谱记载,西成门建于明代中叶的洪熙元年,即公元1425年。这就是说,西成门建成距今580多年了,禁伐令的颁布,恐怕更早。可贵的是,村人世世代代严守禁伐令,所以,至今此地古树随处可见,其中有棵罗汉松据说已是1200岁高龄,依然蓊蓊郁郁。江西各地的许多古树,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大炼钢铁而烧成炭化为灰的,而蒲塘的珍稀古木却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劫难,至今仍生长在那数百年前的禁伐令中。
那道禁伐令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族人,村人爱惜草木,甚至养成了难以改变的生活习俗。以前做饭、烧水用的是松针、落叶、脚柴、茅草甚至牛粪,如今,尽管用上了液化气、燃煤,村中仍保持着在墙上晒牛粪块的旧俗。可是,信仰崇拜的生命力却不及那道禁令,我在村中看到,许多人家已经改换门庭投靠上帝去了,依然住在祖先留下的老房子里,而大门“芳传东海”的石刻匾额上,竟被贴下了这样的对联横批“哈利路亚”。别处还有什么“荣耀归主”、“神爱世人”、“家靠上帝恩常在”等等。迎新的对联和横批十分鲜艳,就像攻城略地插下的一面面旗帜。
在这千年古村里,尚存古建筑60多幢,而人们内心里的精神建筑却早已是一片废墟,既然如此,“哈利路亚”的进驻也就不奇怪了。但是,那些树依然神圣,那些树仿佛是人们可以托付终生、托付百代的最可靠的荫护。
鄱阳湖畔的都昌县有个高塘村,位于三县交界的群山之巅,是该县海拔最高的村庄,且村口有一口大池塘,故得村名。始建于南宋的高塘,村之四周峰峦绵延,白云缭绕,古木参天,遍地奇花异草,村口山坡上有棵银杏,已逾千年,冠高20余米,需4人方能合抱,周边还有6棵树龄200多年的银杏树拱卫着老树,它们仿佛是老树的子孙,和世世代代的村人一道,陶然生活在这鸟鸣空谷的幽境之中。
兴国县三僚村的秤杆形山上,长着一棵三人合抱的千年古杉,人称九尾杉,是堪舆大师杨筠松亲手植下的风水树,人们对它无不顶礼膜拜。说来也奇,三僚先后遭清军、北洋军、国民党军三次血洗,九尾杉却一再逢凶化吉。不幸的是,如今竟有人确信它能治病,将树皮扒下来煎汤。我听见古树忍着创痛,在吟诵三僚廖氏族谱上的诗句:“松生鳞甲尾生杉,造化生生总不及;一本根株培厚土,九棱骨节露层岩。浅深次第光华并,长短高低茂密咸;寄語儿童毋剪伐,甘棠守护总宜严。”
村庄不是讲究山环水抱么,森林就是山水的前胸,贴近它就感觉到那生机勃勃的心跳。居所不是希图山明水秀么,树木就是环境的姿容,看见它就能领略到那丰富生动的表情。
述说树的神圣和神秘
唤起对树的尊崇与敬畏
人们不仅依靠强大的宗族力量来保护关乎风水的林木,还创造了许多神奇的故事,述说树的神圣和神秘。生长在口口相传的语言中的古树,唤起的正是人们对树的尊崇,对树的敬畏。
泰和麻洲的密林里,生长着笔架樟的传说。从前的金滩,是个大村庄,邻村人要去沿江当圩,必须穿过麻洲,而达官贵人、婚娶人家每每到了笔架樟旁,便被笔架樟横着的树枝挡住了去路,人们只能勒马下轿。相传,有一次外村人家娶亲,为了不下轿,他们锯断了那根横枝,不承想,从树的创口流出来的竟是鲜血,这是一个凶兆,随后那个村庄有八十多个青壮死于非命。麻洲上还有一棵古樟,因所有的枝条都伸向赣江,颇似驼背老人,被称为驼背树。撑大船的船工却视之为鬼神树,因为这里有个急水滩,大船上滩总是为那些枝条所羁绊。然而,一旦船工在船头燃放鞭炮、打起号子,以此表达对神树的敬意,大船便可顺利上滩。
栗下村有堵照壁,其上的对联说得好:“万里垂杳观日月,百年种树长风云。”难怪栗下村至今有古树近千,原来,在它看来,植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林掩其幽,更重要是树长风云。所谓风云,应该是一个村庄、一个宗族的旺势吧?
由遍布村里村外的古树,我联想到它的彭氏大宗祠,矗立其中的百根长十米的房柱,何尝不是一座茂密的森林呢?
那样的百柱宗祠在江西乡间比比皆是。我相信,在以百柱为自豪的祠堂里,柱,支撑的不仅仅是梁枋和屋顶,它还承载着一个宗族精神的重量。向上,它意味着宗族发达的根脉汇聚在一起,托起了百世相传的基业;向下,它意味着在祖先神灵的荫护下,宗族繁盛的心愿忽如百柱擎天。
百柱是根脉发达的宣告,也是人丁兴旺的寓言。既然如此,人们在宗祠建筑中那般重视使用立柱,也就毫不奇怪了。我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林立的木柱切割着我的视线,切碎了我对祠堂内部的完整打量,是的,立柱总在抢着对准祠堂的镜头。立柱是成群地站立在宗祠里的主人,就像宗族全部的男丁!
有趣的是,那些把树木大规模地引进宗祠的村庄,通常也是绿荫如盖的村庄。树木与立柱,有着怎样的瓜葛,怎样的约定?
自古以来尊贤重教的传统,为梅冈村创造了人才辈出、代不乏吏的历史,自宋代以后,涌现了明代政治家王鸣臣、清代文学家王愈扩等16位名儒学者。高悬于王氏宗祠本仁堂中的牌匾,永远津津乐道于祖孙科甲、父子进士、叔侄柱史、兄弟科贡、一门节义的佳话。
在梅冈,宗祠里精心摆布的柱,宗祠外刻意经营的树,形成了建筑与环境、内心与外在的相互映衬、相互呼应的关系。我之所以不肯把那些树仅仅看作是营造宗祠建筑环境的需要,是因为在我看来,立柱和树木是被宗族寄寓了思想和情感的。柱是树的历史,树是柱的未来。柱是树成材的证明,是树的荣耀。树是柱不死的心愿,是柱的慰藉。柱与树的关系,恰好象征着祖先与后人的情感源流,象征着宗族荣耀与理想的历史联系。
也许,宗祠周围乃至村庄内外的那些树,便是百柱蓬蓬勃勃的分脉吧?蔓延的绿色,把叶子、花朵和果实播撒到四面八方。
燕坊村在历史上虽有“小小吉水县,大大燕坊府”之誉,但这个坐落在滔滔赣江边的村庄,毕竟是个顺水漂来的村庄。即便在今天,村委会的公开信也恳切呼吁:“让我们共享一片蓝天,共享一片资源,鄢、王、饶、江、黄、刘、肖、夏、郭等姓都是燕坊大家庭中的成员。”杂姓逐水而来比邻混居的特点,反映在建筑格局上,一目了然,百余幢明清老房子不受封建氏族大一统观念的约束,自然没有那种严谨、规整的布局,它们分别坐落在各自的池塘边,有些挤挤挨挨,有的则躲闪在一隅。粗略地看来,给人的是疏密無序的印象。民居厅堂内墙门后,多书有“群居守口独坐防心,能忍则安知足常乐”之类窃窃私语般的家训。可是,一些牌坊却是堂而皇之地巍然高耸!并且,这是一个以牌坊多著称的村庄!至今尚有题词高悬的,如“水木清华”、“青阳绚彩”、“秀毓临川”、“燕贺麟游”等等……这都是各家炫耀门庭的标志坊。
凭着舟楫之利,靠经商致富的燕坊村建在一片带状台地上。它背倚后龙山,以抵挡冬季寒冷的西北来风,山上上千棵樟树为之构筑了一道藏风聚气的天然屏障。面朝赣江流水,迎接着沁人的夏日凉风,赣江东岸有大东山与之遥相呼应。村前开阔的田野有朝阳之势,日照充足。缓坡阶地,既可免除洪涝之灾,又可获得良好视野。村里村外的树木,既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也发挥着调节气候的作用。
走进这个村庄,最让我惊奇的正是树。惊的不是绵延几公里的樟树林,奇的不是村里村外的桔园,而是树种之丰富,是村中一家一园与村外山水环境呼应交融的景观组合。围绕村庄的郁郁葱葱里,时有一树树金黄,一树树紫红,真个是“村在林中,林在村中”。这是我在别的村庄不曾看到的。燕坊号称“五多”,其中之一多,为池塘多,那许多的池塘依宅而生,就开在各家的门前,投映着各家的牌坊,仿佛是各家的气场。其实,池塘多、桔园多、樟树多,无疑也是对建筑的一种隔断。然而,当我们理解了水的承载、树的寓意之后,就不难把握这些杂姓在共享一片蓝天时的微妙心态了。
因为那些炫耀于世人的牌坊,那些耳提面命般的家训,各家的池塘各家的树,仿佛都有了各自的心思各自的梦。
树仿佛通灵。因海内外堪舆界尊杨筠松为祖师,近年一经宣传推介,兴国三僚村顿时声名大振。文化人来了,游客来了,开发商自然接踵而至。
这两三年间,我屡次陪客人前往三僚,得以见证此地旅游开发的过程。先是修建了道路、门楼、游客服务中心和停车场,并沿着游览路线设置了一些风水小品,今年五月间再去,竟见三僚村前的独石岩也建起了盘山而上、甚是扎眼的游步道。这倒是极大地方便了游客登山,可是,殊不知,那座奇崛突起于平地上的小山,却是三僚重要的风水景观。
当年,杨公曾描述过三僚八景。在他眼里,三僚独特的地形构造很像堪舆用的罗盘,上述八景则按东南西北有规律地排列,颇为符合八卦的方位;而那独石巉岩,状若罗盘中的指针。
那段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字,记载在族谱里。其实,如今游三僚,若没有村人作向导,是很难看出山水草木及村落建筑中的玄机的。不少风水作品,尤其是散落于村子周围构成风水环境要素的那些自然景观,看似寻常,道破来却是高深莫测,十分的神秘。比如,杨公门徒曾文辿给三僚断了一句偈语,称“前有金盘玉印,后有凉伞遮阴,代代能文武,世世为好官”。所谓凉伞遮阴,指的是村后山脊上兀立着一棵马尾松,树下则有两块岩石。村中老人告诉我,他做孩子时树也是这么大,几十年过去,既不见长,也不会老去。
可是,就在发现独石岩建成游步道的那天,我大吃一惊,凉伞再也不能遮阴了,马尾松枯死了。去年年底,我还领略过它蓬勃健旺的风采,半年之间,它怎么忽然老去了呢?如果是寿终正寝,应该有个渐变的过程吧?如果是因干旱所致,别忘了在南方马尾松可是最滥贱的树。
它别是为八卦图形中、罗盘指针上的赘物抑郁而终吧?别是用枯萎在警醒人们吧?
通过村人讳莫如深的言辞、一反常态的表情,不难窥见他们内心的惶惑。请原谅我的大惊小怪或故弄玄虚。我压根儿不想把一棵树的死去跟古村落的开发刻意联系起来,不过,联想到眼下一些地方高举着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大旗,大肆改造古村落,任意改变村落环境的现实,我倒是宁愿把那棵死去的马尾松看做是通灵的古树,看做是一种善意的警示。
瑶里古镇
瑶里,古名“窑里”,因是景德镇陶瓷发祥地而得名,自古就是商贾云集、车马鼎沸的贸易重镇。瑶里镇(左)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素有“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称,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中国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瑶里境内山多,均属黄山余脉,森林覆盖率高达94%,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瑶里森林公园位于瑶里汪胡游览区内,面积4471公顷。从阔叶林到针叶林,从藤蔓乔木到花草矮林,色彩斑斓、层次分明,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右)。
与瑶里古树相伴的有一个杀子禁伐的传说。相传明初,山下梅岭的张姓人家与汪胡人家争地,发生了械斗,告至浮梁县衙。知县来到现场察看,看着郁郁葱葱的林木,顿生保护之心,做出“竖着汪胡水口,放倒张家财业”的判决。知县判决后,张姓人很不服气,将汪胡老族长的小儿子骗到山上,并引诱这位七八岁的小孩砍倒一棵大拇指粗的小树。由于这件事,两村又引发了一场山权归属的争议。老族长为了保存这片森林,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将儿子一刀砍死,并告诫在场的每个人:“从今以后,谁敢再损害此山的一草一木,当与我兒子同例。”从此以后两村村民相安无事,再也没有谁敢到森林中砍伐树木。至今,这里封山育林已有700多年。
撰文/刘先锋 左图摄影/鄢新平 右图摄影/刘先锋
泰和麻州·金滩古林
泰和麻州,又称金滩古林,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塘洲镇朱家村金滩自然村南面的赣江河畔,当地人称作麻州。
这片古林面积约20多公顷,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林内古木参天,郁郁葱葱,生长着樟树、枫树、水蜡树、油珠树等多种名贵树种(右),林业部门已登记编号树龄200年以上的古树有200多株,大的樟树要五六个人合抱才能围拢。
古树是金滩朱氏在此开基时为抵御洪水和风沙种下的,族规中有世代相袭的禁止伐树的禁约,并有伐树斩首的传说。泰和麻洲的密林里,还有关于笔架樟的传说,人们经过此树必须勒马下轿。左图是作者在密林中发现的巨大的“笔架樟”。
撰文/张英能 李爱民 左图摄影/刘华 右图摄影/俞建华
燕坊村
树木围绕中的燕坊村门坊。燕坊古村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金滩镇,东临赣江。后龙山南北向贯穿村落,山上有1000 余棵古樟树,从村头延伸至村尾,郁郁葱葱。
燕坊,亦称鄢坊,始建于南宋中期,是一个有800 多年历史的古村。初由张、胡、李三姓立基。到南宋初年,王、鄢、饶三姓人丁兴旺,以鄢姓为最,以姓名村鄢家坊。后有王、饶、江、肖、夏、黄氏迁入居住。
古村各巷道均为青红石板或鹅卵石铺成,屋内描金绘凤、精雕细刻。村后古樟、古枫,村前古井、古池塘与古村融为一体。
燕坊村2007 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撰文/张英能 摄影/邓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