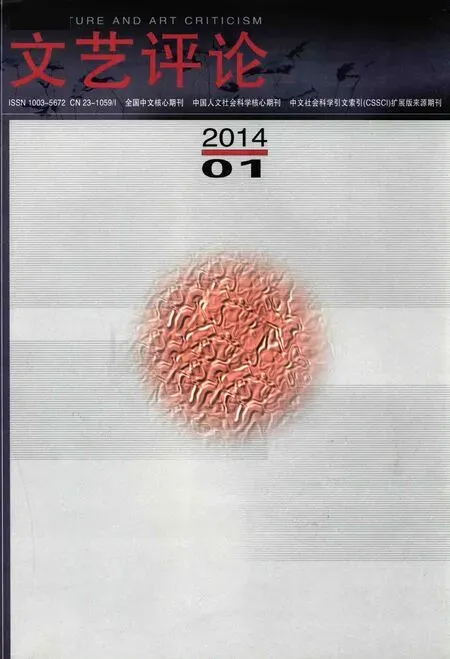跨文化视域下的艺术的“形式”和“意味”——以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和杜威为例
○李 韬
彼得·W·希格斯(Peter W.Higgs)和弗朗索瓦·恩格勒(Francois Englert)因成功预言希格斯玻色子(又称“上帝粒子”)的存在而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物理世界的假说可以通过实验得到证实或证伪,但人的情感世界一点也不比物理世界简单,至今还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途径去分析人的情感问题。也没有人找到决定人的情感世界的“基本粒子”,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停止探索的步伐。人们通过对“美”和“艺术”感受和理解来为人类的情感世界找到一种解释的途径。克莱夫·贝尔提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假说,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系辞传》中有“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记载。这里的“言”“象”“意”第一次集体出现,把“象”和“言”区分,又把“意”和“象”联系起来;也就是把形象和概念进行了区分,把形象和情感串联起来。贝尔、朗格和《易传》都试图在情感、形式和艺术观念之间寻找一种关联,从而“捕捉”艺术和人的关系。
一
一个小孩儿涂鸦了一条线和两个圆圈,然后兴冲冲的拿着对父母说,这是一个大卡车,嘴中还“呜呜……”叫着。这种通过一个线和两个圆圈所构成的“大卡车”表达了孩子最真实最朴素的情感,我们习惯上称它为“有意味的形式”。
“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是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1914年在《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在贝尔的《艺术》中“意味”即审美情感,“形式”即线条和色彩的排列组合关系。他说:“我把线条和颜色的这些组合和关系,以及这些在审美上打动人的形式称作‘有意味的形式’,它就是所有视觉艺术品所具有的那种共性。”①朱光潜先生指出贝尔的《艺术》“最雄辩,最易引起兴趣”,尽管如此,该书局限性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贝尔主张纯粹审美的情感,把大多数描述性的画作排除在艺术品之外,这就使描述性和审美性对立起来。其次,他认为称得上艺术作品的绘画就与日常生活中的利益情感没有多少关系,与各种各样的信条与教义事实与理论也没有多少关系。在这一点,贝尔达到了片面的深刻,他严格区分了审美情感和生活情感的区别,但又把审美情感“悬置”起来,使之绝对化了。这使我想起《克林伍德》中的一个比喻,“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他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最后,贝尔似乎把再现和表现对立起来,把观念和意味也对立起来。从而使再现性艺术和观念艺术排除在有意味的形式之外。这种二元对立的哲学框架也就没有能真正揭示出“意味”和“形式”对应关系形成的原因。这些所谓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他提出这一著名观点时才33岁,自信且坚定,这种个性也表现在他的著作中。
中国的“形”只是相对于“神”而言的“形”,和西方的“形式”相比,没有“形式”概念,具有宽泛的涵义。“形式”在西方美学中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都把“形式”作为一种美学的“元概念”使用,相对于中国“道”则具有本源的和形而上的双重意义。因此赵宪章认为“形式”是西方美学的核心,而“道”是中国美学的核心。②从历史的角度看,古希腊时代的艺术一元论催生古希腊艺术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风格,到古罗马时代艺术的二元论导致艺术文体的多样化,希腊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为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分析成为可能。黑格尔是主客二分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把艺术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方法,而且把它作为一种理论,提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命题。并且根据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把艺术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黑格尔提出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艺术活动中人的实践等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学提供了思想资源。
20世纪的艺术一元论重新回归,在一元论的统摄下,艺术形式多元化。杜威提出的“艺术即经验”的观点,以“活的创造物”为基础试图恢复艺术和非艺术、艺术品的经验和日常生活的经验、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美的艺术与实用艺术之间的连续性。认为艺术家在表现中所出现的情感与形式的关系归结到表现性动作上来。艺术家的情感不是在创作之前形成的,然后运用符号进行表现;而是在创作过程中产生,情感的表现过程和产生过程是同一个过程。他的观点有效地纠正和补充了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丰富了对艺术的形式和意味关系的理解。
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提出的背景是后印象派的绘画,他对塞尚的绘画有深刻的体悟,“我注意到塞尚作品最鲜明的特色是坚持追求‘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最高的目标,在这之前,我便为他的作品兴奋不已。当我注意到这种特色时,对塞尚及其追随者们的钦慕更让我坚定了自己的美学理论。我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他们的作品,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我发现了在其他每件打动我的作品中可以发现的东西”。③可见,贝尔是从塞尚的作品中找到了他自己理论的注脚和出发点。贝尔不断提到“有意味的形式”和“形式背后的意味”,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意味”和“形式”的关系,因此对“意味”的理解也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后来的苏珊·朗格提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创造”,对弥合贝尔理论的断裂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意味”究竟来自哪里?它和“形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还是看看塞尚是怎么说的,他认为“色彩愈谐和,线描就愈明确。如果色彩表示最高的丰富,形式就表示最大的充实”。④“我迄今设想色彩是伟大的本质的东西,是诸观念的肉身化,理性里的各本质。我画画的时候,不想到任何东西,我看见各种色彩,它们整理着自己,按照它们的意愿,一切在组织着自己,树木、田园、房屋,通过色块……我们的空气的温柔抚触着我们精神的温柔。色彩是那个场所,我们的头脑和宇宙在那里会晤”。⑤在这里,塞尚认为线条、色彩和形式是同一的,这些元素都有各自独立的本质,按照自己本然的样子“组织”着自己,画家的“精神”和“头脑”在色彩的世界里达到和谐。显然,他认为“形式”和“意味”是一元的,并且它们统一于“形式”中,“形式”融化着画家的“精神”和“头脑”。如果塞尚还算理智型的创作者,那么凡高就是非理智的创作者,在凡高这里“形式”和“意味”就又是另外的一种状态。
在凡高这里,情感的直接性和强烈程度似乎要压倒形式的表达,凡高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到:“亲爱的兄弟,我在生活里没有那亲爱的上帝也很能过得去,但我作为受苦难的人,我不能缺一件比我强的事物,它是我的真正的生命,它就是创造的力量……而在画里面我想说出的事物,像音乐那样安慰着:我想用这个‘永恒’来画男人和女人,这永恒符号在从前是圣光圈,而我现在在光的放射里寻找,在我们的色彩的灿烂里寻找。但这却不阻挡着我的可怕的需求,我能说出那个字来吗?宗教。”⑥凡高绘画的精华部分虽然不是直接表达宗教的,但凡高绘画的宗教感还是十分强烈的,凡高作为“牧师”的失败和作为画家的“失败”(他终其一生,就卖出一幅画)却使他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功,使他抵御了当时日益异化的世界,顽强地成为了自己。他是自己艺术的“牧师”,艺术成为他的“宗教”。凡高对艺术、宗教、苦难和生活的理解倾注在他那富有无限激情的笔端,使人忘记他是画家,忘记他是在作画。他使绘画的形式和人存在本身会合,使情感和艺术本体直接同一。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进而他对艺术活动作了说明:“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的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⑦托尔斯泰认为情感是艺术的本体,艺术形式中“声音”、“色彩”、“线条”、“动作”等是传达情感的中介和手段,艺术的目的就是把艺术家的感情传递给读者,让读者也体验到同样的感情。塞尚的形式产生情感,梵高的情感产生形式,托尔斯泰的“情感传递”论都从自身的创作实践得到部分的印证。但都没有能真正揭示“意味”来源,因此“意味”和“形式”的关系就不能很好地说明。
马克思认为:“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⑧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人的感觉形成的历史性,人们之所以能感觉到音乐、绘画、雕塑的美就是因为人在历史中形成了感受音乐感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和感受雕塑的空间感的能力。“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揭示了感觉形成的根源,美感也是人的感觉之一,它的形成不能超越人的历史。
“人的本质力量”也就是人之为人的“力量”,也就是人区别动物的“力量”。一个小孩儿在水塘边,投掷石子边掷边欣赏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涟漪,其实他何止是在欣赏涟漪,他是在欣赏自己“本质的力量”,他在感受投掷行为的过程中来确证“自己”的存在。人们对美的追求也是同样道理,齐白石的“他日相呼”画的是两只小鸡在争夺一个蚯蚓,把小动物对象化后,齐白石特有的审美情感寓于其中,传达出一种特别的情趣在里面。还有他的《柳牛图》也通过简单的线条和色块的组合表达了他对大自然的淳朴的热爱之情。如果说齐白石的艺术来自他作为农夫和木匠的社会实践,那肯定有人说那么多农夫和木匠怎么没有成为齐白石呢?海德格尔说:“诗人就是听到事物之本然的人。”⑨也许齐白石就是那位“看到”了画家之为画家的“本然”的人。因此,他就成为齐白石。
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阐释艺术品的来源时说的,艺术家是艺术品的根源,因为艺术家创作艺术品;艺术品是艺术家的根源,因为艺术品使艺术家成为艺术家。但是在这两者中间仿佛有一个先在的东西,那就是艺术。因此应该说艺术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根源。如果说艺术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根源,那么艺术的根源是什么呢?贡布里希在《艺术故事》中说根本没有“艺术”这回事,有的只是艺术家,可见他是反对抽象地谈论艺术的。但毕竟有“艺术”这个词,任何词语它开始命名的时候,都是有其感性基础的,而不是来自纯粹逻辑的观念的推演,艺术一词应该也不例外,它应该也表示着与人存在的一种关联。后来,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就把艺术定义为人对物的“解蔽”,并且认为就是人通过艺术使不“在场”的东西“显现”,使无限多的不“在场”的东西“澄亮”,从而也照亮人自身。他对凡高《农鞋》的解读,就突出表现了他这一思想。
我们以中国建筑天坛为例来说明形式和意味的关系,天坛由南到北逐步升高,给人一种上升的运动感,把人的视线引向天之“崇高”;天坛建筑突出圆的造型,圜丘、祈年殿等都是圆形,而且建筑中的同心圆把人的视角引向天之“圆融”;天坛周围大面积种植柏树,运用蓝色琉璃瓦,深蓝的琉璃瓦和浅蓝的天空形成色彩深浅的对比,更加显现天的“澄明”和“明朗”。美学家杨辛认为,“高、圆、清三点体现了天坛的崇高、祥和、清朗的独特意境。这种独特的意境,也就是天坛的神韵所在。在中国美学史上‘神韵’和‘意境’都是属于艺术美的范畴,指的是一种艺术的境界、美的境界。但两者的角度不同,意境侧重于情与景的关系,是情与景的结晶;神韵则侧重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精神内涵在艺术形式中的圆满显现。意境与神韵的共同点则是:(一)以意蕴、情趣取胜,对人的精神产生深刻影响;(二)艺术形象是一种暗示、诱导,引发欣赏者的想象,从有限中去领悟无限。所谓‘篇终接浑茫’,这‘浑茫’便是欣赏者自由想象的广阔天地;(三)精湛的形式在于对欣赏者的引发,却不炫耀形式自身,使艺术成为一种‘化境’,所谓‘但观神彩,不见笔墨’,这虽是古人论书,但也适合建筑艺术”。⑩
因此,我们认为对天坛的审美就是通过有形的天坛去体味和感受无形的天的“虚空”之美,而对故宫三大殿的审美与天坛的审美是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故宫建筑的前面空旷的广场是为了突出宫殿的雄伟和威仪,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而天坛则是由实到虚的过程。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第一讲中在阐释舞蹈“动态形象”时,表达的和杨辛对建筑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说:“一种舞蹈越是完美,我们能从中看到的这些现实物就越少,我们从一个完美的舞蹈中看到、听到或感觉到的应该是一些虚的实体,是使舞蹈活跃起来的力,是从形象的中心向四周发射的力或从四周向这个中心凝聚的力,是这些力的相互冲突和解决,是这些力的起落和节奏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是组成创造形象的要素,它们本身不是天然的物质,而是由艺术家人为地创造出来的。”⑪不管是朗格对舞蹈的论述还是杨辛对天坛的欣赏,他们都把艺术看成一个虚实结合的整体,通过艺术形式的“显”,来看到形式背后的“隐”。
二
像康德的物自体不可认识一样,朗格认为情感本身也不可用语言表达。“情感本身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或者说,情感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对象。这个命题有一箭双雕之妙:一方面,她借此回避了对情感本身的研究;另一方面,她借此说明了艺术存在的理由”。⑫她的美学思想在《哲学新解》中提出,并在《情感与形式》中全面展开。在后一部书中,她提出了对艺术的定义即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创造。他在《情感与形式》的结尾写到:“正是卡西尔——尽管他并未承认自己是美学家——在其广博的、没有偏见的符号形式的研究中,开凿出这座建筑的拱心石。至于我,则将要把这块拱心石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以连结并支撑我们迄今所曾建造的工程。”⑬
卡西尔认为:“一切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如,语言、神话、艺术和科学,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种种经验,概念作用不过是符号的一种特殊运用。符号行为的进行,给了人类一切经验材料以一定的秩序:科学在思想上给人以秩序,道德在行为上给人以秩序,艺术则在感觉现象和理解方面给人以秩序。符号表现是人类意识的基本功能,这种功能对于理解科学结构固然不可缺少,对于理解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和历史的结构同样重要。人就是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符号不是反映了客观世界而是构成了客观世界……各种符号形式的生成,就是一部人类精神成长的史诗……信号是指令行动的某物或某种方法。符号则不然,它可以传达某种意味或某种内在含义,它不是事物的替身而是概念的媒介,符号功能包括主体、符号、概念和客体,因此符号活动中包含着概念活动的能力,而概念抽象为人类独具,所以信号可以为动物和人共有,而理解符号的能力,即把关于感觉材料每一物都完全看成其所包含的特定形式的能力,是人类独具的精神品质。”⑭朗格以卡西尔思想为基础构筑她的艺术哲学思想。
《情感与形式》一书不仅提出了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这一重要的概念,而且她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这也诚如她在序言中所说,她主要论证了艺术的本质与情感的关系;某几种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本身作为艺术的基本统一性;题材和媒介的作用;艺术“传达”与艺术“真实”的认识论问题。朗格和贝尔不同之处在于她是从音乐入手,来建立她的理论大厦的。她在《哲学新解》中认为:“音乐的作用不是情感刺激;而是情感表现;不是主宰着作曲家情感的征兆性表现,而是他所理解的感觉形式的符号性表现。它表现着作曲家的情感想象而不是他自身的情感状态,表现着他对于所谓‘内在生命’的理解,这些可能超越他个人的范围,因为音乐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符号形式,通过音乐,他可以了解并表现人类的情感概念。”⑮不仅音乐如此,绘画、雕塑、舞蹈的色彩、线条和姿势无不如此。它们表现的并非实际的情感,而是情感的概念。艺术完完全全是表现性的,表现的过程就是主体、符号、概念和客体。如果说绘画、雕塑、建筑是创造了“虚幻的空间”符号的话,舞蹈是创造了“虚幻的力”的符号,诗歌是创造了“虚幻的记忆”的符号,音乐创造了“时间意象”符号。艺术的一般性就在于人们普遍可以认识的符号形式。
朗格对音乐的阐释比较多,中国古代对音乐作用的描述也很多,最著名的是孔子的“三月不知肉味”,这说明韶乐对孔子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使他达到了沉醉的程度。韶乐是上古时代的音乐,距离孔子的时代已经也有几千年的时间。是什么样的情感形式能让孔子如此陶醉呢?按照朗格的理论,那只能是韶乐是“人类的情感的符号创造”、反映了人类的“内在生命”,因此时隔几千年还可以感动孔子。中国的传统音乐评论认为韶乐是“尽善尽美”的,所以可以感动孔子。其实孔子也是欣赏形式美的高手,《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曾经对鲁国的大师乐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缐如也,以成。”“用现在的话说,即是起始时,众音齐奏;展开后,协调着向前演进,音调纯和;继之,如风聚云汇,达到高峰,主题突出,音调响亮;最后,收声落调,余音袅袅,情韵悠长意味无穷”。⑯在这里孔子也完全是对音乐形式美的欣赏,他充分肯定了形式的独立价值,以及形式对接受者情感的巨大感染作用。
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提到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生命的形式”,虽然艺术品是一个物品,但是它具有生命的一切特征,把生命体和无生命体区分起来的关键要看是否是“有机的”。艺术品的有机性特征也非常明显。她说:“如果要想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也就是说,它就必须使自己作为一个生命活动的投影或符号呈现出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⑰朗格从物理世界的生命特征出发,来论证艺术的生命特征,她显然是运用“暗喻”的方式进行这种论证,把生命体的特征和艺术的基本元素进行对比从而得出艺术是生命的形式的结论。
东西方人的运思方式的差异,也使得艺术是生命形式的命题显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朗格从生物学角度对艺术和生命形式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中国艺术家和哲学家更愿意从“精神”的角度对艺术进行探讨。朱良志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中说:“中国人以生命概括天地的本性,天地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生命,都具有生命形态,而且具有活力。生命是一种贯彻天地人伦的精神,一种创造的品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就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体、为最高真实的精神。”显然,中国的艺术与生命的关联更为根本和直接,从哲学、美学和具体的艺术门类都体现了中国人深沉的生命感和生命意识。山水画的“可游、可居”,篆刻的“通气”,人物画的“传神”,书法如孙过庭《书谱》:“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⑱的描述,这些中国艺术都在讲究一个“活”字,其内在突出一个生命的律动。即便是刻画枯木、残荷、荒寒意境的作品也要突出内在的生气。这与中国特有的生命哲学有关——老子的“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思想,庄子的“自由”和“审美”关系的讨论有直接的关系。但其核心的观念是艺术形象或者自然之物必然真实反映生命的世界,表现宇宙“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
“像倪云林的绘画,给人一种凄凄惨惨、冷冷清清的感觉。生命在寒风中萧瑟,实际上充满了盎然的生意,在冰雪的深层有地火在奔突。”⑲这就与西方的艺术拉开了距离,西方人绘画非但没有这种“天人合一”和“一体运化”的观念,而且他们更多地去表现人和自然对立甚至对抗。这种“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使西方艺术去追逐自然的“真实”,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艺术把人安放在画中,安放在音乐中,安放在园林中追求一种天地万物一体的“浑茫”和“沉醉”;西方则相反,艺术把人放在画的外面运用焦点透视的方法去观看自然,运用形式的美去打动人,让人去“审美”。东西方艺术家的运思方式的不同,也体现在对艺术形式和情感的关系考察上。
如果说“有意味的形式”没有很好地揭示出情感的表现和形式的创造的关系,那么苏珊·朗格的“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则把二者统一了起来。情感的表现和艺术形式创造的关系,是否如朗格所说就是艺术家的情感符号化的过程就是艺术的形式创造过程?在她的《情感与形式》中没有明确的解答,在《艺术问题》中她说:“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但是,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一旦艺术家掌握了操纵符号的本领,他所掌握的知识就大大超过了他全部个人经验的总和。艺术品表现的是关于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概念,它既不是一种自我吐露,又不是一个凝固的‘个性’,而是一种较为发达的隐喻或一种非推理性的符号,它表现的是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意识本身的逻辑。”⑳在这里她重审了自己的一贯主张,艺术不能表现人类情感,也不能表现作家的情感,它只能表现一种关于“生命、情感和内在现实的概念”。
“尼采则说:‘艺术乃是人类最高的天职,也是人类真正的形而上学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苏珊·朗格的意见与尼采相似,她认为艺术所涉足的乃是哲学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认识情感”。㉑因此,艺术获得了对“情感”认识的合法途径,不管朗格对艺术论证得多么复杂,归根到底艺术或者艺术品是情感的表现。至于如何表现和表现了谁的情感可能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艺术的情感特征或情感性,始终是艺术的核心。她在《艺术问题》中给艺术下了个定义:所谓艺术,就是表现人类情感的外观形式。艺术不仅是表现生命形式而且是表现其情感的形式。人的内心情感,以及真实的生命感受,它们相互交错和时强时弱程度的张力,时而固定、时而流动,时而爆发时而消失的欲望,也就是说人情感世界中变化莫测、游移不定的因素,都是用单纯的逻辑符号无法表达的,只有依靠艺术符号即表象性形式来表达。
贡布里希说,“应该怎样把装腔作势的‘冷峻’言辞和真正崇高的言辞加以区别。有人回答说,真正崇高的言辞是‘高尚灵魂的声音’,但这么说会使批评接近于表现主义美学。而严格说来,它只是将问题从言辞的表达转移到了说话者的身上,并不能使我们对问题有任何更清楚的了解”。㉒我们对艺术的情感和形式研究时,也往往犯这样的错误。当我们把形式和意味割裂,把情感和符号割裂,把艺术与经验割裂时,艺术便成为单纯的存在于人的审美领域的漂浮物。当这些美学家试图弥合这种断裂时,他们往往把问题转移了,而不是直面这个问题。因此,黑格尔的论述是最辩证的,他说:“内容非他,即内容之回转到形式,形式非他,即形式之回转到内容……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完整的统一,因为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㉓把艺术看成一个“自由的整体”,内容和形式抑或意味和形式的区分,只是人们认识的必要,而不是艺术本身所固有。
三
杜威的哲学的核心是“经验”,他的名著《艺术即经验》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作为经验的艺术”。㉔他在论述一位狩猎者和一位画家或诗人在面对同一种情形时不同的表现,但是就经验的动作来说,他们又具有相同性。他是这样说的:一位狩猎生手见到所追逐的猎物时,会激动而不知所措。他没有一系列准备和等待有效的动力反应的组合。因此,他的行动倾向间相互矛盾,相互阻碍,其结果是忙乱不堪。狩猎老手面对猎物也会激动。但是他会排除情感,将他的反应引导到事先准备好的程序上:把握住眼手一致,看准枪的瞄准器,等等。如果我们代之以一位画家或诗人,他在一个绿色而撒着点点阳光的森林里突然见到一只漂亮的小鹿时,也会有一个从直接的反应转向其他途径的变化。他没有准备好去射击,但他也没有使他的反应无目的地弥漫全身。由于先前的经验,这种动力协调立刻将他对当时情况的知觉变得更为敏锐、更为强烈,并将赋予它深度的意义结合进去,同时,它们也使所见之物落入一种合适的节奏之中。㉕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艺术家和一般的观赏者对同一个情景的不同反应。借此杜威想告诉读者,“经验”的地位。面对一个可以触发灵感的题材,艺术家和常人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镇定自若地按照平时训练来的经验来构造自己的作品,而后者则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杜威不同于朗格和贝尔的地方是他把“经验”的重要性加以强调,进而通过经验来弥合艺术各个方面的人为分裂。杜威的深刻性在于他对艺术的“实质”和“形式”的反思,以及把艺术划分为形式和内容的警惕。他认为,“我们可以说,那种将质料与形式区分开来的理论,那种为各自在经验中找到特殊位置的努力,尽管它们之间正相对立,都是同样的根本性谬误的实例……审美经验并没有被托付去产生它自己的概念,并以此阐释艺术。这些概念是从并未参照艺术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中现成地拿过来,强加上去的”。㉖杜威的关于情感表现理论是“情感的表现过程,也同时就是产生过程。这是一种情感形成的‘柠檬汁’理论”。㉗他还认为,“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并不是情感,而是带有情感的意义”。㉘在这一点上他和苏珊·朗格的理论有点接近,苏珊·朗格也认为,艺术作品并不表达艺术家的实际情感,而是表达艺术家认识到人类情感的符号。
中国传统艺术观念认为,道是其最高的范畴。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试图揭示思想与外在言说之间的悖谬关系。“按照老子的意思,内在把握到的思一旦外现为文字的表达,便立刻失去了它的丰富内涵,用老子的话就是失去了它的恒常性(‘常’)”。㉙《庄子》中有这样一段话: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之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㉚庄子呼唤的这个人,其实就是那个“道”的合理接受者。中国艺术的重“神韵”、“以形写神”、“写意”、“言志”和“得意”等提法都深刻地表明中国的艺术所追求的不是形似的模仿而是精神性的内在的“神”、“志”或者“意”。用哲学的术语表达就是“道”。
宗白华在《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中认为艺术至少有三种主要价值:一是形式的价值,二是描象的价值,三是启示的价值。他曾引用清代大画家恽南田对一幅画的描写来说明启示的价值: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邱一壑,皆洁庵灵想所独批,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宗白华认为“意象在六合之表”即“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借幻境以表现最深的真境,是艺术的“象征力”所能启示的真实。“荣落在四时之外”是说真实是超时间的,艺术同宗教一样,也启示着宇宙人生最深的真实。㉛宗白华对“艺术价值结构”的论述是对中西方艺术的“形式”和“意味”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