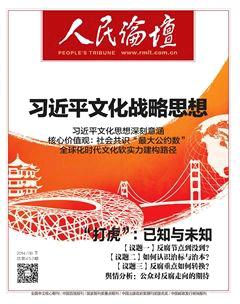死亡游戏(外四首)
□许多余
死亡游戏(外四首)
□许多余
我们曾经聊起火葬
“那烧的不疼吗?”
她的惶恐和诧异让我
这个做孙子的无言以对
我们还有几亩山地 没必要
去跟死人争夺地盘
土地在我们山区比劳动力廉价
人(包括死人)的尊严远远比粮食、房地产和GDP重要
没有像个人样活着 就一定得像个人样死去
这是奶奶的形而上学
她的逻辑简单得只剩下我
妹妹、父亲、母亲
和那只失踪二十多年的跛脚黑猫
如果赶在爷爷前面……
这是个让她困惑的问题
到底谁先走比较合适?
有生之年恐怕她难以做出选择
“我死的时候你会哭吗?”
“我快死的时候你会回来陪陪我吗?”
听到肯定答复她异常满足
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辈子的活动
范围不到五十公里
却轻而易举地听信我夸下海口
我记得那个让我心酸的游戏:
哟,到我的裤腰带了!
嘿,赶我的胸口啦。
哈,齐我的耳根了呀!
啊,跟我一般高喽。
那个比高矮的游戏
我和她玩了很多年
直至我高于她后就自然终止
我开始被动地疏远她 离开她
慢慢地她一截截下沉
现在 她的身体正在向泥土快速倾斜
一股谁也无法阻止的力量
正可怕地将她的生命压缩
死期将无限接近柏树根的距离
她关闭耳朵 喃喃低语
我看见她不止一次地偷看刚刚刷了漆的棺材
善良的木匠和老谋深算的漆匠让她既兴奋又不安
那只手抚摸过我们童年的头颅
此刻温暖的记忆在指尖衰减 冰凉
她将耳朵紧贴到棺材板上
搜寻自己未来的呼吸和世界
一如佛龛在静穆中倾听蚯蚓的蠕动和蚂蚁的脚步声
我将无法原谅自己
适度单纯
两位老人在墙角交谈
“我们都是要死的人了……”
冬日的阳光把他们的旧棉袄
晒得和头发一样白
“……就要被农具和书籍抛弃了。”
他们各自呼唤着自己的孙子
小姑娘在草垛边蹲下解手
夕阳映照在她高高翘起的小小的屁股上
村庄散发着稻谷和黄金的幽香
小男孩稚气的脸上有刀刻的痕迹
秋日
小叶蒿排着整齐的长队
爬到山顶赴死
它们挺拔的头颅 无限靠近日月
星光。风割去皱纹。
容颜枯焦,如碳。
满地都是骄傲的骨头
“你满载果实,又深染着葡萄的血……”
我珍藏着艾叶的苦,在花朵里安息。
“等大气的精灵都住在果实的
香味上,欢乐就轻轻展开翅膀。”
祖先们坐在蛇背上飞来飞去。
栗树下,几颗被遗忘的板栗
正召唤着,橙黄的落叶和带刺的壳。
秋风轻咳了几声……
还没到怒吼的时候。
乡亲们
腊月 北风没能将我囚禁在火炉旁
我单薄之躯无法抗拒山峰的刻薄
无法拒绝土地的捶打和鞭策
我弓着身子 像个年迈的老人喘着粗气
信念和幻觉支撑我爬上老家背靠的大山
乡亲们 曾在这巨大的斜坡上生产
放火烧山 种植玉米山芋茶叶和板栗
村委会大喇叭喊着令人亢奋的口号
“加把劲哟!2008年,大家都能奔小康!”
而今十几年过去 我只看见他们衰老的容颜
在杂乱无须的草丛中躲藏
在空寂悠长的马路上游荡
有的已变成僵硬尸体长埋地下
我从未谋面的娃娃满山奔跑
那群气宇轩昂的猎人 早丢失了枪
捕风捉影的叔叔也被子女们剥夺了速度
我儿时的伙伴 变成了邮件
家人年初将其快递
年底和工友们一起被打包
在拥挤的车厢里,经历
年复一年的殊途同归
他们卑微的眼神让我痛苦
腊月 北风没能阻止我的回忆
我曾在梦中见到过你们
我已经不想与你们相见
那么多天才都在受难
路边绿得发亮的草芥
告诉我们要活得更低
长高了
那就去死吧
那么多庸人都活得很好
他们忽略了所有的苦难和悲喜
像草芥一样
过滤掉遗传学和高度
大半截身体陷在泥土中
总有一些人不计后果
如松柏、银杏、石板条、苦李子和刺槐
一生都与死亡、清冷、孤独和险境为伴
一生都活在与生俱来的拒绝里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那么多伟岸的身躯迎风招展
那么多天才都在受难
许多余,现居安徽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