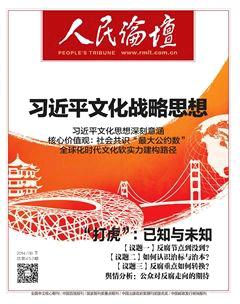一列深夜的火车(外八首)
□杨河山
一列深夜的火车(外八首)
□杨河山
凌晨一点三十八分我开始构思一首
关于火车的诗歌。于是火车便慢慢驶过来了。
它停靠在我身边,冒出一团白色的蒸汽。
(像一只大鸟亮出羽翅)此刻,我躺在床上,
四周一片黑暗。但我确实看见火车驶过来了。
那或许是1976年以前的火车。车门打开,
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人开始吸烟,然后他
擦拭着车厢上的徽章。而更多的人陆续从车厢内
走出。哦,火车是否真的存在?而那些人
又去了哪里?四周一片黑暗,但我分明看见
一列火车确实停靠在这里。一些人走出来,
像鱼贯而出的幽灵。甚至我听见了一声鸣叫
像呜咽,然后又仿佛在失声痛哭。
哦,一列火车,我看见它就站在那里。
我甚至看到在它身后的铁轨上正蠕动着
一道紫红色的月光。
我以递减的方式抹去我面前的风景
我以递减的方式抹去我面前的风景。
所有的高楼。民居。这不过是个尝试。
抹去哥特建筑和拜占庭建筑(虽可惜但我必须这么做)
抹去路灯,天色顿时暗了下来。抹去树立的黑色烟囱、
街道以及所有的机车。这顿时清净了许多。
然后抹去人。首先抹去我自己。
(但抹去了我之后这首诗歌没人写了所以暂时留着)
拔除东条英机。他是一个坏人曾经来过这里。
抹去斯基德尔斯基。对不起,我还需要抹去一些好人。
当我做完所有这一切之后,我发现,
哈尔滨这座城市从前曾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
但有些东西不能抹去。树木不能抹去,
河流不能抹去。它们始终都会存在。其实鸟雀也不能抹去,
千百年来它们始终在这里飞行。此外,
月亮不能抹去。它清澈的光辉曾照耀着这里的江水。
繁星也不能抹去晚霞也不能抹去,
它们曾是这里最美丽的一部分。
此外这里的一切就都应该不复存在了。
哦,还有一些不应该抹去的东西。
一匹白色的野马。它曾经在南岗区的高地上吃草。
一头孤狼,甚至一只东北虎。
它们曾在这片丘陵上漫步,并在地上投射出巨大的阴影。
此外,便没有什么不能抹去的了。
嗯,看来真的没有什么了。
当我以递减的方式抹去我面前的风景,
我发现,这里真的美好了许多但同时也孤寂了许多。
这时,我需要抹除我自己了。
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虚度了许多时光。
长江路
我想象自己走在冰封的江面上。
现在是二月,长江路积满了黑色的冰,
这让它看起来更像一条江。的确,江本来就是
一条公路。那些行驶的汽车,它们是鱼?
有鱼的姿态。我看见它们巡游在途中,
轻盈而小心。其实鱼也有发动机,
或许还有人驾驶它们。而路边那些树木和建筑,
在雾霾中,空旷而神秘,并预示着什么。
哦,那些行人,像一些更加微小的鱼,
或浮游生物。它们三三两两,或聚集成群,
议论着什么。但听不见它们的声音,
只能看到许多白色的气泡,那是鱼愤怒的言辞。
哦,走在长江路上,我想象自己正走在
冰封的江面上。脚下有某种东西在流动。
它确实像一条冰封的江,而我看到的,
仅仅是大江的缩影。
夜色中一匹红色的马
这游荡在某个交界处的幽灵,
酷似一匹红色的马。它俯下头吃着什么,
像从地里拔出一些青草。
因此,它的肚皮发亮。那是青草的光辉。
这个孤独的幽灵。
哦,我还是发现了它。
凭借青草钻出土地的声音和它的四个蹄子。
红色的尾巴可以忽略。
我发现了它。这匹马让我想起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
他曾这样发问:真见鬼,
你在那里做些什么?你又不耕种。
你周围的人都说希腊语。
我在心里枪毙了一只乌鸦
我在心里枪毙了一只
乌鸦。因为
它弄黑了我的视线
因为它在树上蹲着,偶尔
叫上一两声
因为它从不修剪自己的指甲
还有,因为它不会笑
而这对于一只鸟是十分重要的
它还不会哭,哽咽,或者
吸烟。总之,它让我
别无选择
其实,我并没有枪毙它
只是闭上一只眼
用食指朝它点了一下
我点了一下
它就栽落下来,它是
自己枪毙了自己
在它石头般倒下的时刻
我突然感到,这不是
自杀。它的死还是与我有着某种
神秘的关系
黑天鹅
黑天鹅是白天鹅的反派,
持不同政见者,或对白天鹅的否定。
与白天鹅几乎完全一样,
但又截然不同。
它浮游水中,有时在天上飞,
都让人想起白天鹅。
或许它就是白天鹅。
只是永远沉浸于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夜色里。
它没有白昼。即使明亮的白天,
它也在梦游。
在长白山山脚下看见五只乌鸦
它们站在树上,弄黑了树的一部分。
其实,也弄黑了长白山的一部分。就像一座
白色建筑,不小心沾染上一团油漆。
其实也弄黑了天,这似乎预示着什么。
不久之后,黑夜便会来临而乌鸦只是前奏。
哦,我望着乌鸦,其实也弄黑了我。
那一团黑色通过眼睛潜入内心,并且消融,
让人联想起清水池中的一滴墨汁。
为此,这乌鸦似乎很高兴,非常有成就感。
它“啊啊”地怪叫着,(为什么我
受到蛊惑也怪叫了几声?)我们仰头
望着乌鸦,议论纷纷。有人说它预示着
某种凶兆,但也有人说它异常聪明,
是祭坛上的神器。
一匹铁青马
我想起一匹1973年的马。肤色
如上个世纪凌晨两点的夜空,又像阴暗的
诺敏河的水。狭长的脸,布满了
黑色的雀斑,带有上世纪明显的特征。
我偶然间想起了它,但为什么会想起它?
它站在我的面前,依旧那么帅,
但脸色铁青。哦,时间过去了四十年,
可以肯定这匹马早已不在。
(1973年的夜空也已不在,而那河水也已枯竭)
我想起了它,当我想起它的那一刻,
这匹马便向我一直走来。哦,铁青色的马!
它铁青色的灵魂一定听到了我的
召唤。我仍安在,但对这匹马的思念
不知为什么正与日俱增。
雨夜的火车站第四站台
午夜,我进入第四站台时发现火车
早已停在那里。天在下雨,火车在雨中发光。
不时有人脸飘浮于黑暗的站台上
并且拖着拉杆箱。那是一列更加微型的火车。
雨越下越大。当我选择离开,
我看见年轻人在含泪拥抱。
而两个蓝色制服的人正用力摇晃着
他们手中绿色的信号灯。
杨河山,现居哈尔滨。
品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