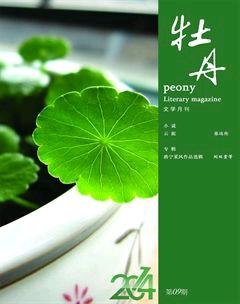白衬衣
唐诗,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湖南郴州市人。200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情相持》,作品散见《散文选刊》《海外文摘》《作品》《四川文学》《广西文学》《山东文学》《安徽文学》《芳草》《芳草·潮》《工人日报》等刊。现居深圳。
1
门没有锁,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杨城略略犹豫了一下才推开门走进客厅。房间里昏暗,杨城心里想,这该死的鬼天气,阴不阴晴不晴的,要下雨就赶紧下吧,也许一定得阵雨过后天色才会好起来。他将公文包放在门口的鞋柜上,正要打开灯,瞥见客厅角落里,有人蹲在沙发前。
走近一看,果然是苏秀。她脸色煞白,眼珠子像是被人上了透明胶,一动也不动。她的那双冻得有些僵硬的小手插在蜷缩着的双腿中间,深深弯着腰。
“你怎么了?”杨城想将她抱到沙发上去,终究只是想了想。苏秀没有回答他。他叹了口气,在沙发上坐下去,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苏秀蹲不了多久,她的腿就会麻,杨城知道。以前她最讨厌蹲着。“要么坐着,要么站着,我不喜欢中间值。蹲着是中间值。”她说过。
默默坐了一会儿,杨城站起身来,学着苏秀的样子,矮下身去蹲着,轻声问她:“抱你起来好吗?”
苏秀的眼珠子动了一下,泪水夺眶而出。这是她第一次在他面前哭。杨城心里一热,顺势揽住了她的肩膀。
“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你这个坏蛋!”她呜咽着说。
他将她用力向怀里拢了拢,说:“蛋没坏。”说完,兀自笑了笑。
两个人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苏秀说得很自信。她说:“杨城你可以出去玩,可以有异性朋友,可以完全听从你内心的召唤做出任何选择,咱们互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这话正中杨城的下怀。他与前妻离婚就是受不了那种束缚。一结婚,也不能想出去就出去了,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工作,都得向家里头交待一声,大多数时候还得交待来龙去脉,来不得半点含糊。绑手绑脚的不舒服感让杨城觉到了生活的无趣。离婚是他先提出来的。一时冲动说出口的话,前妻却当了真,把话说死了,说:“离就离!谁后悔谁是王八蛋养的!”话说到这份上,干脆心一横,离了。闭着眼睛想一句:“谁离了谁,还能活不成?”
离婚那一阵,杨城有点受不了,偶尔还会怀念被女人惦念的滋味。时间久了渐渐习惯了,下班后四处寻乐子,想干嘛干嘛,想多晚回家就多晚回家,快乐地享受起单身生活来。孤独的时候,甚至想到了“理想”这个词。杨城表面上是个律师,骨子里是个地道的文艺青年,擅长弹吉他,和几个写诗的朋友合伙租了几间厂房,建立起一座貌似与世隔绝的乌托邦。
说是与世隔绝,寂寞的时候免不了夜夜笙歌。几个诗人略有才气,相交甚广,杨城又能说会道,在深圳结识了各行各业的“能人异士”,其中不乏善男信女——比如苏秀。
2
刚认识苏秀的时候,杨城以为她还没结婚。一双单凤眼似笑非笑,说话的时候眉毛上扬,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嘴巴会下意识闭紧,像要躲避一只即将飞到嘴边的苍蝇。就是这抹显山露水的倔强引起了他的注意。“还是个孩子呢。”杨城在心里嘀咕。
他先后加了苏秀的QQ和微信。日以继夜的闲聊让两个人的关系稍显暧昧。有一天晚上,杨城约苏秀出去看电影,他在电影院握住了她的手。她表现得过于自然,让杨城很不舒服。借着黑暗,他贴着苏秀的耳朵问:“你有男朋友了吗?”苏秀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眨了眨,低下头。杨城的心沉了沉。沉默一会儿,苏秀抬起头,对着他笑了,摇摇头。
第二次约苏秀见面时,杨城坦然告诉她,他是离过婚的。他看见苏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迷茫,很快又消失不见。像是交待什么问题似的,杨城又补充说了一句:“我和前妻没生孩子。”话说出来几乎掺杂了几分讨好的意思。苏秀笑起来,眼睛看向远方。
苏秀看着远方不说话的时候,杨城在心里拿了个主意,如果她在意他结过婚就算了,情感上的事情,他遵循的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思想轨迹。可他又暗暗分析判断出一般女人都不会在意这个,特别是两个人产生了情感,男人离异时又没有孩子的话。不是有句老话是“女人想做男人最后一个女人,男人想做女人的第一个男人”吗?
沉默许久,苏秀对杨城说:“我跟你一样。”杨城愣了愣。回过神来时,第一反应就是问:“那你有孩子吗?”苏秀看着杨城笑了一下,她说:“我女儿今年六岁,跟着她外婆在乡下,上小学一年级。”
若不是苏秀说得真诚,杨城会觉得她在开玩笑。“深圳的女人可真不显老,你看起来还是一个孩子呢,殊不知已经是孩子她妈了。”杨城这话说得恭维。男女朋友之间恭维起来显得虚假,两颗心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线,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莫名距离。
“你在意这个吗?”苏秀问杨城,眼睛闪闪的,一如看电影那天晚上。杨城想随便说个答案给她,只要不是伤害她的。话到嘴边,装了糊涂,反问她:“什么?”苏秀没有再坚持问下去。她的嘴边浮现一抹不自然的微笑,喃喃地说:“人生若只如初见。”
“大家都是成年人。”杨城说。
3
苏秀买了套一房一厅的小产权房。第一次将杨城请到家里来时,她表现得有些忐忑。离婚六年了,这六年,她每天都是一个人出入家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发呆,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去上班,一个人回到家。最怕的是春节,她总是躲着不肯回去。一回家她妈就得张罗给她找对象的事情。“趁着孩子还不懂事找一个!”总是这句话。从孩子出生到六岁,这句话听了整整六年。她的孩子早已懂事了,她妈还在用这句话劝她。
自称是“外貌协会”的苏秀对中等个子、相貌一般的杨城谈不上喜欢或爱。他于她处在能接受的位置。
在苏秀家,杨城略显急促。他坐在沙发上看着她,脸上挂一丝坏笑。苏秀给他去倒茶,他贴过来,在她脸颊上云雀似地啄了一下。苏秀联想到云雀的模样,雄性和雌性极为相似。
这天晚上,杨城睡在苏秀家里,他们一如两只面貌相似的雌雄云雀。
上着班呢,苏秀会突然走神,想到杨城在她家睡着的样子,轻微的鼾声。她多半会等他睡着之后起来,要去冲个澡。她稍微一动,他就醒了,入睡极浅。“是个极为敏感的人呐!”苏秀想。endprint
同居这个词在年轻的男女眼里到底是什么,苏秀不是很清楚。她所认为的是,同居等同于彼此签了一份无须明说的协议,里面有承诺、有担当,甚至有责任。
杨城怎么想的苏秀不是很清楚。隐隐约约,她觉得杨城对她不像刚认识那般热情了。情人节那天,他早早就起床出去了,早餐也没吃,匆匆忙忙的样子。苏秀想,该不会是要赶在某个女孩子上班之前送玫瑰去了吧?又不无期待地想象成杨城之所以要早些出门是为了给她准备一份惊喜。这样的想法让一天过得特别漫长。快下班的时候,杨城说要过来和她一起吃晚餐。
苏秀早早下了班,一门心思等着杨城回来陪她过情人节。整整等了两个小时,杨城才露面。她以为会看见玫瑰,不说多了,至少有一朵吧。却没有。不仅如此,一句节日快乐也没有。苏秀装着不在意的样子,招呼杨城吃晚餐。晚餐是昨天剩下来的菜,白菜叶子缩成一团装在盘子里,几块大骨头突兀地堆在边上。夹菜的时候,她惊愕地从盘子边缘的亮光中看见自己模糊的脸,对他说:“将就吃吧。”他没说什么。刚吃两口,她霍然放下手中的筷子,像是对他又像是对自己说:“我去楼下茶餐厅买个菜吧。”
在茶餐厅等打包的时候,她有些想哭。
原本苏秀计划得好好的,想跟杨城去西餐厅吃牛扒,小小浪漫一下。杨城却说外面人太多,在家吃比较好。她在心里为杨城找理由,一面想着他是实在的人吧,一面又压根不能相信一个喜欢抱着吉他唱情歌的男人会不懂得女人想要的浪漫。“是不是我在他眼里根本就不是情人呢?可不是情人又是什么?”这个念头让她内心脆弱。
情人节过后,杨城告诉苏秀,朋友让他一起去参加相亲派对,他答应了。苏秀觉得自己俨如一个埋在地面下的地雷,被人踩到,一下子就炸开了,说:“你想玩玩吗?”杨城说不是。平息了一下怒火,她说:“想要我放手很简单,直接告诉我。我可不做你的备选!”
要说杨城矛盾的心思苏秀也不是不能理解。一如她不会甘心做人家的后妈一样,杨城也一定不甘心做人家的后爸。
没人的时候,苏秀很想哭一场。
苏秀有个同事,三十六岁了,人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至今没嫁出去,私底下不知道托了多少人求介绍。也有人怀疑此女是在正当年纪的时候错过了合适的人,可她哀叹一声,说出来的话尽是泪:“深圳女人多,尤其是单身女人,恨嫁的更是多了去。甭说相貌平平,有点能力的男人,就算是歪瓜裂枣,也学会了挑挑拣拣、朝三暮四、朝秦慕楚。”
杨城是那种相貌平平,有点能力,有点小才气,每月还有一份可观收入的男人。
4
打算豁出去和杨城好好在一起的那一刻,苏秀给自己打了预防针,要把这六年没动用的耐心和情感一次性拿出来,拼了这一次,若他杨城不珍惜,就随他去。有些人被注定了要闯到我们的人生中来给我们上一课,然后直接走掉——她是明白的。
苏秀没问过杨城,他为什么会跟前妻离婚。苏秀自己也不愿意别人问她。六年来,粗略算一下,没有二十个也有十个人问过她相同的问题:“你们为什么离?”这回答起来得多复杂。
还没离婚的时候,苏秀看过一则转自网络的小段子:“要老公干啥?饭我会做,衣服我会洗,钱我会挣,地我会拖,架我会吵,街我会逛,出去我也会玩。有了老公还要给他洗衣做饭收拾家务,还要照顾他家人,他劈腿找小三,还要满世界地灭小三。”——其实,这些都不能成为苏秀和前夫离婚的理由。
记忆里,前夫一连几天彻夜不归,手机也关了,临出门前一句交待也没有,急坏了苏秀。满世界找他,差点没报失踪。那男人绝,回来时一副问心无愧的表情,连句合理的解释也没有。苏秀气坏了,冲口喊一句:“这日子没法过了,离!”男人涎着脸凑过来,说:“离就离!”紧接着就是激烈的争吵。“谁不离谁是孙子!”这样的话也不是没说过,可吵归吵,放狠话归放狠话,冷静下来后谁也没把这事真当成一回事。
真正离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此,苏秀三缄其口。
只记得拿到离婚证那个下午,前夫无比得瑟地对苏秀说:“我们男的离了婚可以找个十八岁的,你们女的离了婚只能找个八十的!”苏秀被这一句话噎住,半天没回过神来。直到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个雷同的故事,女主人公机智果敢,说:“你找十八的,得把人家娶回去当奶奶供着;我找八十的,是去他家当奶奶被人供着,咱俩上下差四辈呢,那能一样吗?咱要是不小心整到一家去,你得早晚问安叫我祖奶奶,你得多少遗产还得我说了算——你有脸跟我显摆啥?”
有那么几回,苏秀想要找个机会问问杨城,他是不是也想找个十八岁的。
一次饭后闲聊,苏秀说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和一个离异男同居,前不久竟然被那男人给甩了。杨城脱口而出:“她不是没结过婚的吗,怎么这么傻?”
5
杨城发现苏秀有个隐蔽的衣帽间,里面的衣服五花八门,聚集了红、黄、蓝、绿、紫、赤、青……鲜艳的颜色居多。衣服的质地各不相同,棉、麻、丝绸 、呢绒、皮革、化纤、混纺 ;款式多种多样,涵盖了套装、典雅、印花、时尚、晚装、休闲、运动等系列;风格更是千奇百怪,什么百搭、嘻皮、淑女、韩版、民族、欧美、学院、通勤、中性、嘻哈、田园、朋克、OL、洛丽塔、街头、简约、波西米亚等等,杨城听苏秀说出那些衣服的标签,头都要炸了。
衣服越多,苏秀越是挑剔。每天早上站在房间里都会低声嚷一句:“没衣服穿。”
认识的时间越久,杨城越觉得苏秀神秘。两个人住在一起,面对面相处的时间多数是晚上。一到白天,杨城就跑得不见了人影。多数时间是跑去和诗人们搞各类活动,在他们的乌托邦谈笑风生。苏秀和他在一起后就再也没去那了,似乎有意避开了他的朋友圈。
和苏秀住在一起的事情,杨城没和任何人讲,亲戚朋友一个都不知道。苏秀也没对任何人讲。
“扫黄”事件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那几天,杨城注意到苏秀一直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衬衣。那是她衣橱里唯一的白色,以至于眼睛随便那么一扫就看见了它。endprint
穿白衬衣的苏秀显得格外忧郁。她给杨城讲了一个非虚构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梦想成为艾米莉·狄金森那样一个出色诗人的女孩沦为风尘女子。那个偶然事件成为她人生中永远抹不去的污点,无法剔除。她隐姓埋名,以爱情的名义嫁给了看上去敦厚老实的男人。新婚之夜,她问男人:“你去过那吗?”男人:“问哪?”她告诉了他。他否认了。可第二年,她又问了男人相同的问题。男人说他去过,并且据理力争,说那是发生在他认识她之前的事。
杨城没听懂这个故事讲了些什么。他问苏秀想说什么。苏秀微微一笑,问他:“你去过那吗?”杨城问哪。她告诉了他。他思索片刻,既没否认也没承认,他说:“未婚前的男人都去过啊!”他还想对苏秀说点什么,却看见她已经扭过头去,背对着他。
6
初夏的夜晚,苏秀喜欢棒一本书,默默地看,将一切嘈杂屏蔽在身体之外。杨城在她专心看书的时候会多半是拿着手机在玩,偶尔才拿出吉他,安静地弹一曲或唱一首。
入睡之前,杨城和苏秀会出现简短的对话。
“在看什么?睡吧。”他说。
“我再看一会儿,你先睡吧。”她说。
偶尔,他们之间也会交换说话的顺序。
“别玩了,睡吧。”她说。
“你先睡吧,我再玩一会儿。”他说。
诗人朋友给杨城介绍了一个女孩子,他去看了,那女孩眉眼清亮,活泼可爱,竟和苏秀长得有几分神似。
和女孩看了两场电影,杨城没动过一丝歪脑筋。自始自终人模人样,文质彬彬。每次电影散场的时候,他总有种莫名的紧张,似乎苏秀会出现在电影院门口。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苏秀送了杨城一份小得不能再小的礼物。长方形的立体,棱角被红色的包装纸勾勒出来,坚硬如铁。八个尖锐的角,用手轻轻触碰一下都能划出伤口那般。苏秀说:“也许有一天你要离开,那天你再拆吧。”
和杨城相亲那女孩对杨城的态度时冷时热,一如苏秀对他的态度。杨城想要表现得洒脱一些——顺其自然,随缘随心。
事情发生在冬天,是一个在南方城市难得遇见的雾霾天。苏秀从午睡中惊醒,心口发紧。她以为错过了上班时间,摸出手机一看,才睡下去半小时。一抹无法下压的慌乱感,像是某种灵异的感应和照见。她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第一个念头就是女儿,苏秀拨通乡下的电话,她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飘过来,清清爽爽的,问她这个点打电话有什么事。她又打给杨城,号码还未拨出去就挂断了。默默想了一会儿,发了一条短信过去。
“在哪?没事吧?”她说。
极少会立即就收到杨城回的短信。苏秀从不轻易主动给他打电话或者发短信。
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杨城的短信回过来了,他说:“没事。”
苏秀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她的身边一定发生了不好的事,这件事还跟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强烈的不安迫使她以生病为理由找到工厂的经理请了半天假,早早等在杨城下班的必经之路。老远,她就看到杨城车上坐着一个女孩,他对她说话的样子很亲热,笑得尤其明朗。
杨城说那女孩是他的一个普通同事。苏秀哀怨的表情让他极为不耐烦,他说:“你不是说我可以出去玩的吗?”苏秀心里一痛。
“你爱过我吗?”她问。
他低着头,不说话。
她闭了闭眼睛,强忍住涌上来的眼泪,又问:“你是想要跟我分手了,对吗?”
“随你怎么想!”他说完,甩开门,走了出去。
7
苏秀讲的那个非虚构的故事,杨城曾经想继续往下听。他缠了苏秀几次,要她往下讲。苏秀执意不肯,一脸神秘。他想了想,问她:“她不会为了这事跟她老公离婚吧?”
苏秀不置可否。
杨城不能理解:“一个曾经的风尘女子这样在乎她老公曾经去过风月场所?”
苏秀没接话,打开了客厅的电视。
“这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杨城说。
苏秀听了这话,“啪”一声将电视的电源直接关掉了。杨城看见她的脸色苍白,木头一样坐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她“蹭”一声,将客厅的电灯也关掉了。他们之间整个陷入到黑暗中去。
良久,她的声音淡淡地传过来:“去过也别说出来,那至少说明尚且还有羞耻感。”
之后的某一天,杨城发现苏秀衣橱里的白色衬衣不见了,随口问了她。
“它发黄了。”苏秀说,心事重重的样子。略微停了停,又说:“不过穿了三次,我就把它弄脏了。”
杨城说:“用漂白粉吧。”她没接话。
那天走掉后,杨城回到了乌托邦。一连好几天他都没想过他走后苏秀会怎么样,只整天和诗人们浑浑噩噩地混在一起吃喝玩乐。烦躁的时候,他甚至想过今后再也不见苏秀了,他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了。这种想法让他矛盾地度过了大半个月。
往一件薄风衣里找香烟的时候,杨城摸到了苏秀送给他的那一小盒礼物——他几乎忘了它。那种尖锐的棱角一下子就刺痛了他的神经。
拆小盒子的时候费了点劲,苏秀包得太严实了。想要用剪刀,又怕划破里面的东西。用手撕,物体又着实太小。
是一个灯泡。细细的白炽灯,犹如台灯,又像厨房或者卧室的灯。他摸索了一会儿,发现了灯泡隐蔽的开关,拧开,竟然是一个USB接口。他搬来手提电脑,将灯泡插上去,它发出刺目的蓝色的光。
是个U盘。他点开它,里面有一个文件,标题写着:希望你能看见它。他的脑子在瞬间被清空,被格式化了那般。他继续点开它。
是一首诗——
《白衬衣》
昨夜过后
我用洗衣粉清洗了三遍,我的身体
就像漂白一件发黄的白衬衣
背着阳光,晾在通风的阴影里
一件质地优良的白色衬衣
我不相信它会染上多余的颜色
一如我不能相信,是初夜的疼痛导致的
爱情的死亡
羞耻的张扬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吗
我们不小心弄脏了一件白衬衣
自此,再也不能珍爱任何身外的东西
责任编辑 杨丽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