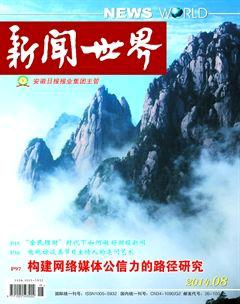受众研究的三个进程与启示
田梦
【摘 要】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受众论,到霍尔“编码/解码”对受众能动性认知的肯定,再到费斯克对受众创造性的张扬,西方受众研究呈现出一种受众由被动、被规定到积极能动参与意义编制、协商直至创造性理解的动态历程。理解这种历史演进,不仅能够清晰不同时段下受众在意义或价值建构中的地位,而且对于当今日益兴盛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也能从一个侧面进行辨析和阐释,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走向。
【关键词】受众研究 动态历程 大众文化
一、受众研究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大众文化中,受众研究的地位日渐显著。这不仅是因为受众是大众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创建者。所以,大众文化自始至终与受众群体紧密相連。文化研究中的受众研究,主要涉及受众的文化身份、受众与生产者间的关系、受众接受心理、受众对文化文本的接受态度与接受效果、影响受众的特殊条件五个方面。简言之,受众在其中经历了由被动接受到能动协商、再到主动创造的历史演变过程,具体表现如下:
1、精英本位下的被动受众
早期大众文化理论是与精英统治论密切相连的。其普遍认为,唯有根据源于文化知识精英的美学论断,才可能恰当地理解和解释通俗或大众文化,批判、谴责的基本论调就此形成。 兴起于20世纪40、5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在精英立场和意识形态批判立场下,针对当时大众文化滥觞、人们意识单质的社会背景下,将批判锋芒直指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控制方面,对受众处于被动地位的强调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其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将大众文化概括为“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意指用于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商品化了的、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凭借现代科技和大众传媒,通过电影、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等媒介操纵了物化的、虚假化的文化,成为了束缚大众意识、推行文化统治的工具手段。因而,大众文化就此成为了一种单质化、受控制的文化样态,受众因而在技术化、复制化的社会生产机制下,在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中,理所应当地被动接受了强加于其中的文化霸权主导思想而毫无反抗或者进行批判性思考。
2、精英本位与受众关系的对话
基于精英本位立场之下的受众研究,传者由于自身的高姿态,其预设的理论框架限定了对受众的合理定位,未能以一种更具客观实际特征的描述来对受众进行判别,基于精英立场下的受众观,个人意识特征浓厚,忽略了处于社会复杂环境之下的它种因素的影响制约。传受间彼此对立,互不相连的尖锐关系,在之后的理论学家的考量下,更多转向了相对灵活,或者说是相对互动的关联研究中。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尔,在1973年写成的《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一书中,创造性地通过三种受众解码方式的引入,为大众文化中传受两方的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说,主要有以下三类:其一是“主导—霸权立场”,作为解码者的受众,在对制码者的信息进行认知理解下,完全接受顺从其全部意图,这一点类似于上述法兰克福学派下的被动受众论,受众自主权完全被剥夺,制码者拥有全部话语权;其二,是“协商立场”,亦即为听从与对抗相融合、接受与反思相作用,同前一点相比,受众在承认制码者本身的主导型地位的同时,保持了自身能动的特殊个体性,受众不会简单地予以接受或拒绝,而是会有所选择的理解并部分接受,加以自我化的改造;其三,则是一种完全颠覆型的解读,受众在理解话语的所有意义内涵时,会以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解码,受众的反抗意识使得媒介中的主导性的霸权符码被完全消解。其实,完全认同或完全否定都不易发生,更多的,是霍尔所说的介于文本与受众间的妥协性阅读,受众会根据自我的认知进行判断,通过能动性的协商和妥协阅读,受众的自主权得到了有力的释放。
霍尔认为,编码者虽然可以在编码过程中尝试预先选定,但却不能规定或者保证解码过程,因为后者有自己存在的条件,解码存在于与编码的某种程度的互换关系之中,二者各具独立性。在解码阶段,受众的思想与信息媒介间相互交流,相互协商。协商暗含在接受媒介信息的过程中,受众并非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主动寻找意义的创造者。霍尔的媒介理论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受众被动接受模式,受众拥有了与具有编码权力的制造者之间平等对话协商的地位,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媒介文化研究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大众文化理论下的主动受众
20世纪80年代,受众研究在结合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其中,莫利对BBC晚间杂志性新闻节目《全国》的分析,霍布森对《十字路口》的观众的研究,莱恩·昂对《达拉斯》观众的研究,费斯克对“电视文化”的研究等等尤其令人瞩目。所有上述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其研究重点集中放在了受众的选择、创造性行为当中。
代表人物约翰·菲斯克在继承了霍尔的研究基础之上,对受众在解读大众文化文本下,如何创造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进行了重点关注。费斯克眼中的受众,充满了个性和思想,并且具有创造性。对于大众文化产品,他们不仅可以用来交流,更能借此创造出他们所需的意义和快感。对此,费斯克在肯定了受众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将之分为社会性和文本性二重身份。受众主体的社会性先于其文本性。就社会性而言,受众对于文本的理解,完全依靠由社会性所提供的评判视野和情感基础,以此作为解读文本的潜在前提。就文本性而言,文本在建构之时即为受众预留了供其预设、解读的主体性位置。作为媒介生产者在创设之时设想出来的主体性位置,由于相对个人化的创制预设视角所限,因而与受众的“社会性主体”位置不可能完全一致。二者间不平衡性或差异性会使得受众可以积极利用“社会性主体”的观念来不断审视、解读创制者的文本内涵,从而建立与大众文化文本之间的关系,不断挖掘大众文化的意义和内涵。费斯克通过对电视剧的解读,认为观众理解电视剧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从中激活意义的过程。其中,观众拥有完全建构意义和获得愉悦的自主权。这种对观众主动性的强调,一方面是对早前研究中过于拘于文本力量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受众创造性潜力的一种发掘和鼓励。其意图是为了能够使得受众对大众文化文本的解读更具抵制性,获得对文本自身解读的自由空间。当然,费斯克对于受众积极性的过分强调,使得很多学者认为,受众的创造性被过度夸大,以至于远离了批判性的审视,这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①
回顾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发展,受众观经历了忽视、贬低受众到重视、抬高受众的日趋完善的演变历程。在受众地位逐步提高的情况下,对受众问题处理的合理程度,日益成为衡量一种大众文化理论优劣与否的参照标准。
二、受众研究的启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商品化浪潮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的逐步确立,使得较解放初至文革以来,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文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由政治性的盲目崇拜转向日常化的、平面化的个人生活当中。以娱乐色彩、平民化特质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悄然兴起,对以往既有的精英文化、上层文化产生了具有颠覆性的解构效力。日常趣味、关注现实更多地被大众文化加以利用,成为渗透受众接受之处的最有力的切入点。受众在享受着复制性的大众文化产品带来的愉悦的同时,也找到了自身压抑已久的主体意识、自我表达和对生活的情愫与宣泄。较之于之前普遍庄严神圣的审美心理而言,大众文化的扩散传播消弭了此种心理,作为受众的广大人民会不同程度地接受大众文化中所蕴含的浅层化、平面化、直接化审美影响,因而其审美心理也就必然会放弃对崇高的崇拜,转向对日常世俗化人生的渴望与追求,如此,其作为受众的主体性被日益凸显,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它也不同于费斯克意义上的完全主动创造性的受众,基于中国现实社会特征,它拥有更多的中国化色彩。
就中国的大众文化而言,无论从最早的《诗经》《楚辞》,还是上世纪80、90年代流行于大陆的港台歌曲,抑或近年流行的大型电视相亲互动节目,可以看出,中国的大众文化从一开始就根植于民众之中,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其关系更多呈现为一种互为主体的辩证联系。二者之间在动态演进中,互相满足对方的愿望和要求。其中,受众获得了传播主体或者制作主体所赋予的参与权,比如各类选秀节目、春节晚会中设置的观众短信投票环节,受众的投票结果一定程度上为传播制作主体提供了可参照的价值依据,传播制作主体会在之后的制作当中,根据受众的欣赏品味和评判标准,做出相应的调整和筛选,从而更加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和价值判断。与此同时,传播主体在不断结合社会实际、受众要求的情况下,栏目样式更加多样、制作水平日趋成熟、节目内容推陈出新,在一系列的与受众互动的过程中,找到了在适应受众基础上不断拓展影响和实力的双赢之路。但是,在确立这种辩证关系时,也应该注意一些媒体由于受商业化影响,过度追求收视率,片面迎合部分人的低级趣味,使得大众文化降格为庸俗文化、媚俗文化,部分受众为此或价值观偏离、或缺乏批判性思考,丧失了作為自身存在的主体性价值。对此,在中国的大众文化中,应始终呼唤传媒制作主体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大众文化的传播者更需从人文视角出发,去关注受众自身人格、人伦、人性等方面的提升。同时,处于媒介环境状态下的受众,更应积极反思自己与传播主体和大众文化间的动态演进关系,正确认知自身所处的社会状态和外部环境,做出符合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和社会主流价值的认知判断。如此,具有中国化意义的大众文化传播主体与受众的互为主体的辩证关系,才能更好地得以确立与完善。□
参考文献
①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76
(作者:重庆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2012级硕士)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