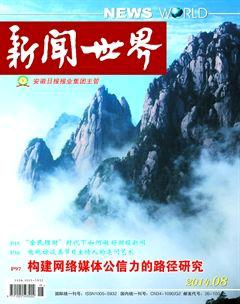浅析小说《白鹿原》的跨媒介改编
王斐斐
【摘 要】本文以小说《白鹿原》的改编版本——广播剧版、戏剧版、电影版为研究对象,运用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分析文学作品跨媒介改编的媒介选择问题,得出媒介对信息具有偏向性的结论。并认为某种媒介并不具有相对其他媒介的绝对优越性,关键是找到最佳的媒介方式来获取、呈现、交流某条信息。
【关键词】《白鹿原》 媒介即信息 跨媒介改编 媒介选择
一、理论概述
媒介即信息,也称为媒介信息论,由加拿大传播学者、媒介环境学派的开山鼻祖麦克卢汉于1964年在其《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最先提出,随即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功能层面,即任何一种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种媒介,如报纸的内容是文字、广播媒介的内容是声音。这里的媒介是指广义的媒介,包括文字、声音、言语、小说、戏剧、电视、电影等;其次是效果层面,即媒介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创新,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赋予人类从事与该媒介相适应的传播能力,每一次媒介革命都会带来信息传播的变革,从而引起人类社会的变革。
具体到分析小说的跨媒介改编,主要涉及的是传播媒介与传播内容的关系问题。媒介信息论提供的启示就是:一种媒介不仅仅是传递内容的介质和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传播特性和传播方式,因此对现实的解读和编码也存在差异,随之也必然引导受众对内容进行不同的接收和理解。比如文字小说,凭借文字的高度凝练和抽象性,因而相对更适合呈现抽象性强的内容比如心理活动;广播可以借助语音、语调、语气、音乐、音响等多种声音元素唤起听众对剧情的真实感知;而戏剧作为舞台艺术的一种,将内容压缩到同一时空,使戏剧的矛盾和冲突得到集中酝酿,从而具备强烈的爆发张力,因此更适于展现人物关系紧凑、矛盾冲突明显的内容;而电影作为视听技术的完美结合,则更擅长将信息作影像化呈现。
二、《白鹿原》概述
小说《白鹿原》是由我国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前后耗时4年于20世纪90年代初写就的长达50万字的鸿篇巨著。一经问世,好评不断、畅销不衰,并获得1997年的“茅盾文学奖”。小说以清朝末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时代背景,以我国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的世代矛盾为叙事主线,通过浓缩三代人的沧桑与家族辛酸荣辱勾勒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宗族、宗法、相约、族谱、祠堂、尊卑贵贱、封建家长包办婚姻、女子三从四德、清帝退位、军阀混乱、民国政府、现代学校、恋爱婚姻自由、砸祠堂、农会、土地改革……统统“融合为一体, 绘就一幅色调繁复而特异的民族历史画卷”③。
此外,小说还成功塑造了一批性格丰满鲜活、又极富文化历史内涵的人物形象:宽厚仁义、勤劳简朴、一辈子奉守“耕讀传家、学为好人”、但又思想陈旧的族长白嘉轩;自私狡猾、忽正忽邪、与白嘉轩明争暗斗的鹿子霖;拥有大智慧、毕生笃信“慎独”但在民族灾难前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朱先生;叛逆、敢于挑战世俗、但命运坎坷的田小娥;勤劳能干、鲁莽冲动、最终为时代吞噬的黑娃;敢于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积极投身革命的鹿兆鹏;率真的白灵;随波逐流的白孝文;忠诚的鹿三……作者正是通过书写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变迁来展示民族历史的演变。
三、小说《白鹿原》的跨媒介改编文本
《白鹿原》自出版以来,陆续被改编成广播剧、戏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并纷纷作为文化事件而广受社会关注。
1、广播剧版《白鹿原》
广播是听觉性媒介,通过在同一虚拟空间中对不同声音元素包括对话、音乐、音响等进行组合构造,诉诸于听众的感官与想象力,听众则根据不同经验对广播内容进行解读。对广播剧而言,人物对话和解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手段,音乐、音响效果等则起到渲染、烘托等辅助性作用。
广播剧版《白鹿原》有普通话和陕西方言两个版本。普通话版在小说出版不久后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此后多次联播,社会反响热烈。该剧由我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李野默先生演播,共42回,每回时长在24分钟左右,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做了部分删减;方言版由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并于2008年首播,由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晨先生演播。在尽量与原文吻合的前提下,方言版也将小说中一些故事性不强的内容做了不同程度的删除或压缩,且完全不涉及某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如性描写等,使内容保持在原著的三分之二,共54回,每回时长在26-28分钟间。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白鹿原》的两版广播剧其实应被归到有声小说之列。尽管两位演播艺术家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独特且富有质感的音色,运用语调、语气、停顿等声音技巧满怀激情地将小说故事作了完美演绎,但相比典型的广播剧,以上两版所运用的声音元素仍较为单一,不仅声音来源没有作性别、年龄上的区别设置,而且毫无音乐、音响等其它辅助声,所有对话、描写、场景的铺设和转换都是靠同一位演播者完成,致使广播剧在塑造和跨越虚拟时空方面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戏剧版《白鹿原》
戏剧是一种视听媒介,不过所有人物、情节、环境都受到舞台这个有限时空的限制。因此人物数量相对少、场景相对简单、情节矛盾突出的内容更适合在舞台媒介上呈现。
戏剧版《白鹿原》,较有影响的是西安市秦腔一团于2000年首次演出的秦腔版和林奕华导演、孟冰编剧于2006年在北京人艺首演的话剧版。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和为了突出戏剧的矛盾冲突,秦腔版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从白、鹿两家众多矛盾中选择争夺“风水宝地”,以此保留了原著中宗法制度下中国农村普遍的家族斗争这一核心。且第一幕开场就直接切到黑娃带回田小娥,在白鹿原上引起轩然大波,立刻导致白、鹿两家的冲突白热化;紧接着第二幕,白灵出逃参加革命,第三幕,鹿子霖与田小娥发生奸情,第四幕,孝文受田小娥引诱被发现、孝文分家卖地、田小娥被杀,第五幕,黑娃回来报仇,第六幕,“风水宝地”归还白家。从整体上看,尽管秦腔版《白鹿原》把原著蕴含的多重主题简单化了,但每一幕都突出了重点,且戏剧张力较强,体现出主创根据戏剧的媒介特性对原著做出了恰当取舍。此外,秦腔式对话也使秦腔版在语言特色上更贴近原著,体现出地道浓郁的关中风情,赢得了陕西观众的共鸣,但同时也由于语言的地域限制,导致该版本的传播范围大打折扣。
话剧版《白鹿原》是目前公认的最忠于原著的改编版本,在情节、人物方面与小说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小说的缩减版。除白、鹿两家争夺“风水宝地”外,话剧还重点展示了鹿兆鹏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白鹿原成立农会搞批斗、国民党政变、鹿兆鹏及鹿兆海和白灵间的感情纠结等情节,可见主创欲在舞台上尽可能完整呈现原著中复杂厚重的多重主题。但因舞台时空的有限性,要用三十几个戏剧场面来展现白鹿原近五十年的历史变迁,就必然要求情节的快速推进、人物形象与性格的相对简化。比如让第一幕开场的换地风波相对匆忙,省略了白嘉轩反复斟酌的复杂心理活动;有意放大鹿子霖的狡猾阴险,掩盖了他也曾因白鹿原淳朴的民风而向善的一面;让田小娥在祠堂的当众陈述更加无畏和直白,消解了原著中环境和命运对她的裹挟以及她在被动中不得已做出选择的无力……导致这些原本为使剧情更加紧凑、人物目的性更加明确的改编反倒引来演员在舞台上走马观花般演绎的诟病。尽管舞台上搭建了苍茫的古原、再现了真牛真羊爬上山坡的情景,在视觉上为观众营造了身处黄土地和关中农村的真实感,大段地道的秦腔和老腔表演也有力地烘托了地域氛围,并在现场引起阵阵高潮,但话剧版《白鹿原》就本身而言,终究没有将原著的“魂”与“神”展现得酣畅淋漓。
3、电影版《白鹿原》
电影是视听媒介,运用镜头和蒙太奇,诉诸光影和声音,在银幕上“还原”现实世界。尽管电影《白鹿原》的公映版本删减了最初版的近三分之一,又因为商业原因和“眼球经济”的驱使对原著主题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取舍和置换,毁誉参半,但撇开这些,单就影像呈现而言,电影版《白鹿原》无疑出色地凭借视听媒介的优势运用影像魅力为观眾展现了一个可见、可听的白鹿原。比如代表白鹿原封建礼教、宗法制度、传统文化的祠堂,电影就用“规则的构图、阴暗的色彩与缓慢的镜头运动”传递出一种无声的“压抑沉闷和不容反抗的秩序”④。而当黑娃和田小娥带人砸祠堂时,电影则“使用不规则的构图、快速的镜头运动,恰当地传达出他们迷惘混沌、妄想冲破传统秩序的勇气与无知”⑤;又如那片一望无垠、麦浪滚滚的麦田,极具视觉冲击力,让观者切实感受到白鹿原上那股旺盛的生命力和人性欲望;还有对秦腔声音的娴熟呈现,与话剧版《白鹿原》对秦腔、陕西老腔的呈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在声音上逼真还原了关中平原的风土人情和民间艺术;此外,影片还通过华丽的镜头再现了风搅雪、砸祠堂、农民起义等大场面,并用近景、特写等镜头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人物的神态表情,这正是其它媒介所无法给予受众的视听体验。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小说《白鹿原》的跨媒介改编文本,结合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理论,得出以下结论:媒介对信息具有偏向性,每一种媒介都会选择自己的信息。我们看到不同媒介在改编小说《白鹿原》时,都会根据自身的媒介特性做取舍,在呈现上则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仅仅是种类上的,而不是程度上的,某种版本也不必然优于其它版本,某种媒介也并不具有相对其他媒介的绝对优越性。因此,最关键的是找到最佳的媒介方式来获取、呈现、交流某条信息。□
参考文献
①麦克卢汉 著,何道宽 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商务印书馆,2000:33
②黄雅玲,《〈白鹿原〉艺术画卷中的特异色调》[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4)
③④吴辉、别君红,《得远大于失——也谈小说〈白鹿原〉的电影改编》[J].《当代电影》,2013(9)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2012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