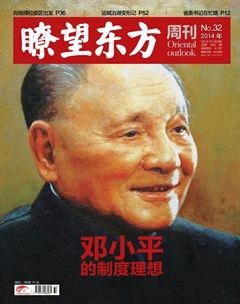吉尔吉斯斯坦:几番“革命”,几番轮回
杨成



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90年代,在相当程度上被动接受了苏联解体而获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逐渐被世界认知。“中亚瑞士”、“高山之国”等新的形象得以塑造。
尽管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只有500多万,但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表现出的韧性仍足以令人称道。从阿卡耶夫到巴基耶夫,从奥通巴耶娃到阿坦巴耶夫,数次政权更迭并未改变这个中亚小国对未来的憧憬。
透过一场场从失序到有序的轮回,外部世界看到的是,吉尔吉斯人渐次消除苏联骤然解体的冲击,在克服彷徨与茫然的心路历程中缓慢生成了促动新发展的内在能量。
如今,中国、俄罗斯、美国、欧盟、土耳其、日本、韩国等诸国,都向中亚国家抛出了地区整合的顶层设计,一度衰败的“丝绸之路”重登域外区内合作的议事日程。
这种大国竞合的微妙格局,使得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选定的集体符号,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和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行为体。
其中,吉尔吉斯斯坦能否藉由自身有利的地理位置、温和友善的合作文化走出“转型陷阱”,令人瞩目。
玛纳斯英灵庇护的“圣地”
在中国的官修史书中,有关吉尔吉斯人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1年左右,其先民先后被汉文史学文献称为“鬲昆”、“坚昆”、“契骨”、“纥骨”、“黠戛斯”、“辖戛斯”、“吉利吉思”、“乞儿吉思”、“布鲁特”等。他们曾建立起强大的汗国,也经历过各种挫折。如同很多曾经的游牧民族,吉尔吉斯的先祖们在一次次主动或被动的部落与民族交融、重组中,走过了古代和近代。
史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吉尔吉斯人原本世代居于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盆地。在汉代受匈奴统治,2世纪中叶后受鲜卑和柔然统治。北齐、隋唐时期先后受突厥汗国、回纥统治,后在840年灭回鹘后独立过一段时间,一直到924年才被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朝(契丹)统治。
元代在叶尼塞河上游设立益兰州、谦州。到17世纪,受到准噶尔汗国蒙古人和俄罗斯帝国的排挤,渐渐迁移到天山北麓的伊塞克湖一带,即今日吉尔吉斯共和国之地。清代,吉尔吉斯部落分为东布鲁特、西布鲁特。东布鲁特游牧于回部境内,受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各路驻扎大臣管制,西布鲁特为清朝境外的藩属部落。而后,沙俄和苏联的统治给吉尔吉斯带来了新的历程。
苏联解体后,阿卡耶夫当局与其他中亚国家执政者一样,在本国独立伊始就投入了无限的精力与激情,重新书写族史与国史。为此,吉尔吉斯突出本国人民及其成长史对于人类发展的贡献,与其他民族足以等量齐观。他们希望通过承续主体民族的传统象征符号来激发国民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在共同的史诗叙事、祖先信仰、英雄崇拜中寻获本民族安身立命的坚实依据。
中国的史料为新生的吉尔吉斯斯坦的祖先崇拜提供了最好的养料。吉尔吉斯人被描绘为“英勇、强大、尚武、尊崇财富、充满爱的共同体”,被塑造为一个尽管面临外敌威胁依然捍卫民族团结且崇尚自由和独立的民族。
与此同时,吉尔吉斯人急于找到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的承载者,古代口传文学中吉尔吉斯人统一的无畏战士、英雄玛纳斯,由此被塑造为民族之父。一时间,玛纳斯几乎处处可见。图书、电影、歌剧以他为主题,从货币到饮料瓶、香烟盒,也都有他的身影。
值得期待的潜在旅游目的国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全境海拔在500米以上,其中1/3的地区在海拔3000~4000米之间。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阿赖山脉绵亘于中吉边境。其中天山山脉西段盘踞境内东北部,西南部为帕米尔-阿赖山脉。在开国总统阿卡耶夫的倡议下,联合国于2002年发起了“国际山区年”。
除却高山,吉尔吉斯境内湖泊、草原众多,大概是中央欧亚地区最未得到充分挖掘的旅游胜地之一。
2009年夏天,我和朋友有幸去著名的世界第二大高山湖——伊塞克湖休憩。行前已读过无数赞美之辞,也听说过这是苏联时期高级官员的疗养基地之一,但亲眼目睹还是被深深震撼。
伊塞克湖长178公里,宽60公里,湖水清澈,能见度达十数米,90余条河流注入而无一条流出。有趣的是,湖水含盐度较高。泛舟湖上,远处的皑皑雪山,在云雾中时隐时现;近处是深不可测的大峡谷,满目纯净的绿色;海洋般湛蓝的湖水,无风时一平如镜,风起时白浪滔滔。
吉尔吉斯斯坦至今仍有不少人口从事畜牧业,高山牧场不仅是国民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构成了令人陶醉的风景资源。尤其是夏季牧场,在各种牧草自然编织成的绿色毡毯中,间或穿插着野花,在牛羊成群、牧歌悠扬中品尝羊肉抓饭、手抓面、烤包子、熏马肠、马奶酒,极为惬意。冬季时高山滑雪也是个好选择,我曾经和朋友们到一个自发形成的滑雪场地“自由滑”,没有器械的我们借用充气的汽车内胎一路高速滑行,给当初的穷学生们非常美好的体验。
当地朋友自豪地说,他们拥有四大天然空调:雪山是“白色空调”,伊塞克湖堪称“蓝色空调”,森林是“绿色空调”,遍布城市的潺潺雪水可谓“流动空调”。
的确,夏季这里光照充足,而绿荫下则自然凉爽,加上甘甜可口到难以想象的各式瓜果,从樱桃到西瓜,还有上百种葡萄,让人惊喜连连。
吉尔吉斯美食中,啤酒就鱼干是绝配;马奶酒醇香而酸爽的滋味不可不提;新鲜的土法烤馕可以让你一口气吃上几张;一种名为“绍罗”的发酵饮料具有养胃功效,比俄罗斯的格瓦斯还要美味。
总而言之,吉尔吉斯的旅游资源绝对是低调中的奢华,目前仅徒具“中亚瑞士”的知名度,但几乎完全未得以开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潜在旅游目的国。
几番“革命”,几番轮回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已经过两次重大的政权更迭。
第一次发生在2005年,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相继爆发“颜色革命”的背景下,旨在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郁金香革命”,最终借助于传统部族动员网络,以反腐败、反舞弊为口号实现。endprint
当年3月24日,反对派及其支持者联合冲击总统官邸,迫使阿卡耶夫仓惶出走。
借“革命”风潮登上总统宝座的巴基耶夫政权在5年之后重蹈覆辙,同样被迫背井离乡,走上流亡之路。
吉尔吉斯斯坦这两次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最大的不同是,2010年4月推翻巴基耶夫总统的集体行动,最初并非是有组织的,而更多的是一次由巴基耶夫政权失败的经济政策、对反对派的过度压制以及总统在人事任命方面过多的裙带主义行为,引发的国民愤怒情绪的总爆发。
一晃又是数年过去,吉尔吉斯斯坦当下面临的挑战一点也不比2010年时少。
这个以农业为主的中亚山地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依然难见起色。该国人均GDP2013年只有约1282美元,位于亚洲第40位、全球第147位;失业率据官方统计,2010和2011年分别为8.6%和7.9%,但实际数字按国际社会的评估远远超过。尽管赴俄罗斯及邻国哈萨克斯坦打季节零工,部分缓和了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的困境,但仍有大约50%的民众不得不每天仅靠2美元艰难度日。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那里留学时,不少吉尔吉斯同学连街头零售的馕和面包都买不起,只能用从老家带来的面粉加上些许盐,自己在电炉上烤,连油都舍不得放。配面包的只有红茶而已。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可能连月票都没有资格买,很多人要从遥远的宿舍步行到学校。
在1998到2000年的两年时间内,我看到首都比什凯克的最大变化是修建了两座漂亮的公交车候车亭。当1999年吉尔吉斯斯坦主办“上海五国”峰会时,这里竟然没有五星级酒店用以接待,只能将唯一的四星级酒店的四个豪华套间,分配给中俄哈塔四国领导人居住。
好在,近五年来的两场政权更迭以及民众对选票重新统计的全程监督,改变了吉尔吉斯斯坦社会与政权关系的议程设置。自2010年巴基耶夫政权倒台以来,新宪法的通过,2010年10月议会选举的进行,以及2011年10月总统选举的结束,标志着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周期。
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体制不再是超级总统制,转为半总统制中的一种重要的子类别,即总理总统制。如此体制下,权力重心转向议会,但总统仍有较大权力。与其他中亚国家的区别是,吉尔吉斯社会中潜在的抗议情绪,将不会单一指向某一权力中心。
吉的政治暴力得以暂时止息,政治紧张度下降,并且政治改革和议会、总统及地方选举,基本按时间表进行,大规模抗议潮趋于缓和。
但另一方面,吉的政治议程依然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政治权重急剧增长的议会,内部不断分化重组,代表地方部族、行业利益、外部大国的各股势力,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配置关系,议会党派之间甚至党派内部的矛盾一如从前,意识形态分野不明朗,经常出现议员流失现象,对立或矛盾的双方支持者,依然将举行大型抗争性集会作为一种常在逻辑。
在“习得效应”的驱使下,春秋两次的游行抗议季已经成为吉尔吉斯政治场域的一种标志性景观。
与中国扯不断的关联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有关中亚的内容主要是以汉武帝和张骞为中心展开的。公元前139年,张骞出陇西不久就被匈奴羁押,十余年后才率旧部逃至位于今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随后又先后到达康居、大月氏等地,所到之处包括楚河、伊犁河畔的乌孙、叙利亚的条支等。中国人与如今吉尔吉斯斯坦所属地理版图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在那段历史长河中。
当是时,漠北大族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周围许多民族,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坚昆亦在被征服之列。汉将李陵降匈奴后,受命管辖坚昆等地区,其子孙后代均融入坚昆人之中,而和亲匈奴的王昭君的后代也融入了坚昆人之中。
公元648年,一支由酋长失钵屈阿栈带队,来自唐朝西北数千里、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黠戛斯朝贡团抵达长安。失钵屈阿栈自称是汉朝李陵的后裔,与唐朝皇帝有板有眼地叙起了同宗关系。
由玄奘口述、辩机整理的《大唐西域记》中,提到了美丽绝伦的伊塞克湖。
而据郭沫若考证,李白的出生地就在玄奘西行途经的素叶水城,即距比什凯克不远的托克马克,尽管这一提法仍有争议,但吉尔吉斯斯坦还是很自豪地将托克马克和李白联系起来。我在比什凯克学习吉尔吉斯语时,那里的汉语教研室专门编译了李白的部分诗歌,并将此作为中吉源远流长的文明互动的标志性事件。
150余年前,陕西回民白彦虎起义失败后,部分回族人由中国西北地区进入俄境,定居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楚河平原上。这些被称为“东干人”、持有典型秦腔、保留了不少清朝生活传统的老回回,如今成了中国中亚民间往来的重要链条。
吉尔吉斯著名东干学者、科学院通讯院士穆哈买德.苏尚洛,曾以“在祖先的土地上”为题,回忆了90年代初期访问中国的往事;东干族著名诗人雅斯尔.十娃子曾经写过不少有关祖国故土的诗歌,《中原》、《给陕西的信》、《献给诗人屈原》等作品中,流露出绵绵乡愁。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中吉两国间曾经横亘的边界线不再仅仅扮演隔离的功能,开始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友谊与利益的链条,双方迅速完成了从以对抗为主题的冷战结构到以合作为优先的后冷战格局的转换。
中吉关系并未受到政权嬗递的影响,反而逐步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层级。在习近平主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中,吉尔吉斯斯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并可能发挥转口贸易的优势,分享更多发展红利。这也是吉方在不同场合积极呼应中方号召的原因所在。
“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清朝诗人洪亮吉在《伊犁纪事诗》中描绘的这一盛大场面,完全可能以现代方式,重新出现在未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