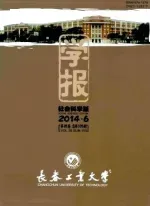《老子》的无欲不符合社会的本质
李宗岩 杨 柳
(1.长春财经学院 科研处,吉林 长春 130122;2.吉林财经大学 马列部,吉林 长春 130117)
一、人生有欲天经地义
在老子的人生哲学中,他主张无欲或寡欲。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实际上,人的天性不是“无欲”和“寡欲”,而是“人生有欲”,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美德的性质不是必然被限定为这些感情中的某一类或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感情大致分为自私的感情和仁慈的感情。因此,如果美德的性质不能无差别地归结为在合宜的控制和支配下的所有的人类情感,它就必然被限定为以自己的私人幸福为直接目标的那种感情。”[1]亚当·斯密在这里不是要求人们“无欲”或“寡欲”,而是要满足人们欲望,满足人们的欲望并不能使社会陷入混乱,相反,欲望得到满足会使人们感到生活的美好。
但是《老子》书中有些思想让人们感到很困惑。《老子·十八章》强调:“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奸臣。”[2]老子认为,大道被废弃了,才有人提倡仁义德行;智慧产生了,才有人做出来大的作为;六亲不和,才有人要求子孝父慈;国家混乱,才出现奸臣。这种思想是没落贵族知识分子对当时广泛兴起的土地私有权反抗的一种表现。在当时新兴的封建经济中,土地所有者是“所有过程及全社会生活过程的指挥者支配者”。[3]这对破产没落的旧贵族和知识分子来说是难于习惯的新形势。不论无欲或寡欲都是反对占有财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无欲是根据他们的世界观发展出来的。
万物的来源是“道”,“道”生长万物,是没有欲望,没有意志和没有目的的。道虽然产生万物,但它并不占有万物,支配万物,即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侍,长而不宰。”[2]世界本身能够长久存在,就是因为它没有想求生存的欲望,故《老子·三十二章》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天下将定。”[2]老子把这样的价值观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活中来,也应以无欲为最高要求。“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认为事物发展是有规律性的,有欲即违反规律,会使民心生乱。如果无欲,则人民自会返于“朴”。朴是自然的本性。他们认为婴儿最能反映这样的品质。人们应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认为寡欲的具体体现是“知足”,老子把知足看的特别重要,以为知足可以决定人们的荣辱和祸福。
《老子·四十四章》云:“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2]接着,《老子·四十六章》又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2]老子将主观知足作为分辨对错的标准。如知足,虽然客观上财富不多,而主观上亦可自认为富有,这是一种对的感觉,“知足者富”,“富莫大于知足”。因为“知足”所以知足,则常足矣,常足当然可以看做是富裕。反之,客观财富虽多,由于主观不知足,贪得无厌,则酿成极大的祸害。
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一书的财富观决定于主观的知足与不知足,亦即决定了“欲不欲”这种思想产生于当时那个年代,使老子看到物欲对人的刺激作用。因此,《老子·二十二章》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2]老子把无欲和知足说的十分美妙,能弯曲则将能保全,能委屈则将能伸张,地低洼则将能转为丰满,物破旧则能将转为重新,少取则可能而有之,多取则迷惑而尽失之。圣人掌握这个道理,作为天下的范模。他不自我表现,所以高明;不自以为是,所以显著;不自夸耀,所以有功;不自骄满,所以长久。正因为他知足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人与他相争。这就是老子知足、不争、无欲和寡欲的逻辑。
二、欲望不可以没有节度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关于倡导“无欲”还是“有欲”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吕氏春秋·情欲》这样说:“天生人而使有贪,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人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4]以《吕氏春秋》的观点看,天生养人就使他有贪心,有欲望,欲望产生感情,感情具有节度,圣人练就节度以克制欲望,所以才不会放纵自己的感情。耳朵想听音乐,眼睛想看色彩,嘴也想吃美味,这些都是情欲。这三方面,人们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明的还是不孝的都是一样的。即使是神农、黄帝也跟夏桀商纣相同。圣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由于他们具有适度的感情。从尊生出发,就会具备适度的感情,不从尊生出发,就会失去适度的情感。而这种情况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根本。对于欲望,特别是发财致富的欲望是任何社会都无法限制的。
当然,人们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时,总觉得有人做得不优雅适度。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在许多政府里,最高职位的候选人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因而,如果他们能达到自己的野心确定的目标,他们就不怕因自己为获得高职位而采用的手段而受到谴责。所以,他们不仅常常通过欺诈和撒谎,通过拙劣卑鄙的阴谋和结党营私的伎俩,而且又是通过穷凶极恶的罪行,通过谋杀和行刺,通过叛乱和内战,竭力排挤、清除那些反对或妨碍他们获得高位的人。”[1]在如今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有些人追求财富,常常放弃通过美德的途径。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与通往财富的道路方向不同。一些私心膨胀的人,他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品德,这就是老子反对的,他们背离了“道”。
客观的讲,老子之所以倡导“无欲”或“寡欲”,是他看到一些贪得无厌的人为了自己的欲望其所作所为太可耻,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2]任何人在追求自己私欲的时候,不可以泯灭人性,仁慈美德的性质不是必然被无差别地归结为人们的各种得到适当控制和引导的感情。近而必然被限定为这些感情中的某一类或其中的某一部分。我们的感情大致分成自私的感情和仁慈的感情。因此,如果美德的性质能无差别的归结为在适宜的控制和支配下所有的人类感情,它就必然被限定为以自己的私人幸福为直接目标的那些感情,或者被限定为以他人的幸福为直接目标的那些感情。因而,如果美德不存在适宜性之中,它就必然存在于谨慎之中,或者存在于仁慈之中。除此三者,很难想象还能对美德的本质做出别的解释。正因为这些大恶都因“可欲”而起。因此《老子·四十六章》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2]老子这种结论是消极的,有时造成人性的泯灭,是任何人都不愿见到的。因此,人们需要欲望有度,如果欲望没有节度,也许会乱生于此。
三、任何社会都要满足人的欲望
在不断进步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没有欲望是不可能的。人生某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其实就是欲望的满足。但老子的有些观念不符合人性的基本观念,没有欲望驱使怎么能产生创造财富的冲动?怎么能创造出文字和科学发明?怎么能完善人类社会的生活秩序?老子自己怎么能写出《道德经》?孔夫子怎么能编写出《春秋》、《论语》,周文王等先贤志士怎么能写出《易经》等等。其实,人类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在欲望和满足欲望的追求中产生。
美国著名的思想家马斯洛在他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中说:“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数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欲望迅速出现并取代他的位置,当这个满足了,又会有一个站到突出的位置上来。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5]这种需求和欲望在老子看来是会经常引起问题的。其实问题不可能不在,但只要人类社会恰当地、不断地解决这类问题,整个社会就会在这种不断出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当中走向进步。因此,欲望推动人们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这种欲望的出现,不断地激起人们的行动,以及因目的满足和获得内心舒畅而感到快慰,这种欲望把整个人类社会编织成一张硕大的网,每一个人都在这张网中找到自己的节点。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说:“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两方面。某一事物被人们认为是你自己的事情,这在感情上就发生巨大作用。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并不是偶尔发生的冲动,人们对于自己的所有物感觉爱好和快意,实际上是自爱的延伸。自私故其应该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欲,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其过度地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自己以及财货或金钱)的。”[6]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一生下来,就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要满足他们生活的一切需要和要得到某些幸福的愿望,并且努力具备使他们满足这些需要和愿望的本领。这种本领是对财富的创造,也是对财富的积累,同时又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人们之所以能让自己享有财富的一切,都是由自己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这辛勤也是欲望的促使。人们所创造的一切,都应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自己的愿望。
当社会满足人们欲望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快速发展。《考工记·总序》:“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之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箭,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也。”[7]这里说的是春秋时期猎国手工业的发展,此时人们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欲望要改变自然资源和利用自然资源,使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都成为一些地方有特色的名牌产品,这些名牌产品推动技术上的进一步革新,人们的欲望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
四、结语
当人类社会踏入文明时代门槛的时候,出现了越来越细致的社会分工,人们通过从事各种各样的商品交换,从而进一步满足人们的欲望推动商品交换的发展。随着人们更多欲望的满足,出现了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等。所有的发明和创造都是在欲望的驱使下产生的。因此,《国语·周语上》:“芮良夫论专利曰:夫利,万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矣?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8]古人这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利益和欲望的驱动有多么大的作用。当今社会,我们更需要满足人们的欲望,这是推动社会经济前进的原动力,这种动力永远是驱动社会进步最强大的力量。
[1]〔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卫广来,译注.老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4]〔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5]〔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7]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下)[M].北京:经济时报出版社,2007.
[8]〔春秋〕左丘明.国语[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