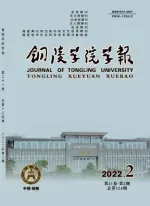从沉默到说话——论《我儿子的故事》中的历史书写与重构
姜 梦
《我儿子的故事》是南非著名白人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写于1990年,正值南非种族隔离后期。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府施行严格的审查制度,殖民地人们的话语权被剥夺,书写被压抑。一直以来,关于殖民地的历史都是由白人殖民者书写的西方眼中的东方历史,宗主国通过控制语言文化实施文化宰割和文化霸权,真正的南非历史和现状得不到展现。非洲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一直是被言说的,非洲历史亟待被本民族人民再书写。历史的反写一方面“并不在于对事实的改写,而在于对事实不同的价值判断”[1],另一方面还需填补沉默群体的历史空白。戈迪默试图从两个方面恢复非洲历史记忆:消解白人话语中心,颠覆大写帝国历史书写;建立黑人女性主体地位,书写非洲女性的历史和文化身份。
一、大写帝国历史书写的颠覆
什么是非洲书写?戈迪默认为非洲书写应该是被非洲本民族人用各种语言写就的文字;还有一些人,非洲这块大陆给予了他们与非洲人民感同身受的经历。他们写就的文字也是非洲书写。[2]历史书写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其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历史细节的真实,而是“谁在向谁讲述(或书写)什么,他们是如何讲述(或书写)的”。[3]叙述者和叙述方式的改变则意味着帝国宏大叙事的消解和非洲历史的重写。
戈迪默认为黑人应该学会用写作去记录和讲述自己的民族,只有黑人自己学会诉说,他们的主体意识才能觉醒,文化身份才能确立。传统殖民文学中,殖民地人民始终处于“被凝视”的地位。“凝视”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4]戈迪默打破白人的叙述权威,赋予黑人少年威尔言说的自由和“观看”的权利,从他的视角记录种族隔离给一个普通家庭带来的苦痛和伤害。
威尔对父亲与白人婚外情的叙述也是关于“我”的生活的记录。叙述者在故事的讲述中展现了种族隔离造成的人内心的异化。这种异化体现在种族隔离制度压抑人的心理,扭曲人的自我评价,黑人潜意识里觉得低白人一等。威尔在痛恨白人的同时又对白人充满了渴望,他会梦到和金发的白人以及汉娜发生关系。戈迪默在一篇采访文中提到:“在我们那种社会里,发生在我身上和我小说中的一种现象,就是情感的扭曲。”[5]这种矛盾的心情和情感的扭曲就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所提到的政权交替时期出现的“大量病态的症状”。[6]威尔通过对自己生活的讲述,把种族隔离给南非社会和人民内心造成的摧残和伤害真切地展现出来,他的故事作为传记体小说,“从非洲黑人的角度见证非洲的历史,……因此构成了非洲历史书写话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
小说除了使用“我”作为故事叙述者和读者交流,还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其中大量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让小说人物不再依附于“我”,而是独立反映自我意识,与威尔的有限视角和不可靠叙述形成对照与互补,多角度展现他无法窥见的人物真实心理。不同人物的自由间接引语既是人物所想,又没有直接从“我”出发,让读者以旁观者的立场更为客观地评判人物和事件。
有关索尼的大量自由间接引语为这段并不纯粹的跨种族恋情提供了佐证。汉娜的白人身份和共同的政治信念带给索尼家庭无法给予的激情:“写信给他的是汉娜,她用屈指可数的几个字就可以表达一切,更不用说500字了。……需要汉娜”。而艾拉则是无法与之产生共鸣的家庭妇女:“为什么艾拉不说话呢?为什么她从不说他想要她说的话呢?”[5]和儿子一样,黑人潜意识里被强化的白人至上思想在索尼身上也得到了体现。索尼认为与白人相恋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一种强烈而大胆的欲望在萌动:让人们瞧瞧她们彼此属于对方。彼此相互炫耀。”[5]自由间接引语对人物内心进行反讽,原本幸福的家庭在扭曲的政治情感引诱下破裂,黑人的价值感来自于同白人的亲密关系。法农对这种扭曲畸形的心理作过这样的表述:“在某些有色人种身上,与一个白种女人婚配似乎胜过一切别的因素。他们从中得以达到同这个卓越的人种,世界的主人,有色人种的统治者完全平等”。[7]自由间接引语真实记录了种族隔离和政权交替时期出现的这些“病态现象”,为非洲书写作了补充。
南非白人是南非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白人自由主义者以积极的身份参与到南非的政治生活之中。小说中汉娜从白人视角审视黑人一家,自由间接引语既揭示了人物内心二元对立的转变,也辅助黑人叙述话语重塑非洲历史。一开始,汉娜无法摆脱高傲的保护者心态:“她想必愿意成为那个女孩的年长的知心女友(看来她好像需要知己)和父母之外的家长,这对那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孩——他儿子的生活也有益处。”[5]她自信自己在索尼心中的特殊地位,对“他者”艾拉抱有同情的态度:“艾拉不能为他做任何事。他也不能为艾拉做任何事。感谢上帝,幸好她还有那个男孩。”[5]然而艾拉在平静沉默中宣告了在家庭的主权地位,让汉娜在直面艾拉的时候甚至需要通过谈话掩饰艾拉给她的压迫感。最后当艾拉参加革命并被捕入狱时,她惊讶于艾拉的改变和勇气。艾拉的成长让她由衷地产生敬意并感到自己的卑微,她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为艾拉哭泣!”[5]自由间接引语使读者窥视到汉娜的内心对艾拉的转变,处于主体地位的西方女性在心理上被“臣属”地位的东方女性他者化,由此颠覆了帝国叙述中白人至上的地位。小说通过汉娜的视角见证了非洲人民的成长和历史变迁,从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反写了殖民者书写的非洲历史。
威尔的自传式写作不仅是他作为黑人的代表,书写自己的故事,展现种族隔离之下百姓的真实生活和精神状态,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说也是南非作为帝国的殖民地,对帝国历史叙述的反写;不同身份和肤色的声音参与叙事,从不同角度讲述南非历史,与大写的殖民帝国历史相对抗,在消解白人话语霸权的同时重构了南非的历史书写。
二、黑人女性主体的建构
女性作为男性的他者,一直是被边缘化的“第二性”。非洲黑人女性作为没有历史的群体,在种族隔离统治之下“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力,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大的反证。”[4]非洲作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形象,和黑人女性一样处于被他者化的失语状态,黑人女性的沉默成为对整个非洲的沉默的隐喻。戈迪默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位颠覆传统殖民文学中黑人女性形象的角色,她们打破了第三世界女性“臣属”失语的状态,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非洲黑人女性的历史书写是非洲历史书写的重要一环。黑人女性在寻求身份认同,重获妇女话语的同时重构了非洲的历史叙述话语。
母亲艾拉完全符合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房间里的天使”的形象:美丽、勤劳、善良,拥有父权体制下男性对妻子所有美德的要求。在儿子威尔看来,母亲的自我意识来自于父亲的赞扬和肯定,因为“看起来我那文静的母亲是多么紧张……好像她的丈夫在场赞赏着她的举止”。[5]小说中用了很多类似于“沉静寡言”[5]、“她本人很少说话”[5]、“她没有说话”[5]、“艾拉从不说话”[5]等表达形容艾拉。在索尼所代表的父权制的南非,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只需要倾听不需要发声。艾拉从来没有作为主体为自己言说的机会,大多数时候她是由儿子来代为叙述的,她的形象也是在丈夫和白人汉娜的注视中逐渐建构的。
沉默并不代表不会说话。大多数时候,艾拉的声音不过是被压制了。艾拉的性格中有坚忍不屈外柔内刚的一面,她的女性意识在情感的压抑和隐忍中渐渐复苏和萌发。波伏娃认为被动等待是没有用的,因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于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他途。”[8]她开始学会作出决定并表明自己的态度,主动建立话语权。在儿子看来,当母亲作为女性主体真正觉醒时,她已经不再是房间里的天使了,“那些房间空空的。她不在那里。她出去了,不是为他,不是为我。”[5]她一改往日端庄贤淑的传统女性形象,剪掉象征女性特征的美丽长发,换上更为中性化的打扮,这些摆脱女性特质的行为并不是女性意识的消亡,反而是一种觉醒和解放: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走出家门,参与战斗,发出自己的声音。当艾拉被捕入狱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她有了焕然一新的形象,让她的丈夫感到“一种鲜明的陌生”,“不得不辨认才能认出她来”。[5]这种形象并不是容貌的改变,而是艾拉从父权制和殖民统治的夹缝中求生,努力寻找到的黑人女性新的文化身份。她的放逐让她真正挣脱了对家庭和索尼的依赖,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革命者,由边缘走到中心。
如果说母亲艾拉是由沉默到发声,姐姐贝比则颠覆了传统文学作品中黑人女性的形象,以打碎开始,重构终结。她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但与母亲不同,贝比自由奔放,大胆叛逆。她的早熟让她无法成为乖巧地待在家中的女孩。她抽烟酗酒,到处派对,很小就知道如何在男人面前展现自己的魅力。父亲的婚外情让她无处发泄,她甚至用吸毒麻痹自己,生活愈加堕落。不同于母亲的隐忍和沉默,她尝试了割腕自杀以获取父亲的注意。与艾拉的安静沉默相比,贝比是充满紧张感,个性张扬,需要宣泄的。年少的贝比对自己的家庭的破裂和自己的革命使命十分迷惘,只能采取极端激烈的方式表达愤怒与反抗(即打碎)。之后的贝比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逐渐成长成熟,成为了一位母亲和一名积极的革命战士,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获得了身份的认同(即重建)。贝比不同于传统黑人女性的沉默被动,是积极发出自己声音的典型。戈迪默寄希望于贝比,将她作为非洲青年一代的代表,重新书写黑人女性形象,这也象征了非洲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将要面临的命运和使命,即由打碎到重建,重写被殖民主义损毁的文化和历史。
非洲女性用行动发声,建立起黑人女性空洞的“能指”背后“所指”的意义。如果说黑人女性的沉默和破碎是对非洲大陆失语压抑的隐喻,黑人女性的发声和主体的重建则不仅消解了男性话语的权威,更不断解构着西方殖民话语的中心,象征着非洲掌握话语权和自我言说的开始。
三、结语
戈迪默赋予黑人青年威尔言说的自由,从被忽略和压抑的他者视角重新审视南非历史,讲述南非种族隔离后期的一系列病态现象。小说避开宏大历史叙事,以他者的文化身份发出声音。大量不同人物自由间接引语的加入使人物摆脱单一叙事声音的控制,不同种族肤色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发出声音,参与南非历史的重写,继而解构宗主国中心权力话语,颠覆了帝国书写的权威性。小说中黑人女性经历了从失语到发声,由打碎到重建的过程,形成了对父权制和殖民主义的对抗性书写,在建构黑人女性历史的同时,重写了非洲历史叙述话语。然而,“我”在结尾表明这将是一本无法出版的小说,这也预示了历史书写的前景依然困难重重,而全篇用宗主国语言写就的作品依然无法摆脱言说的困境。
[1]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242,260.
[2]Gordimer,Nadine.The Interpreters:Some Themes and Directions in African Literature.The Kenyon Review[J].1970,32(1):9-26.
[3]Maggie,Sale.Call and Response as Critical Method:African-American Oral Traditions and Beloved[J].African American Review.1992,26(1):41-50.
[4]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36,58.
[5]纳丁·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M].莫雅平,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8.259,46,60,77,117,204,11,4,33,44,46,153,200.
[6]Gordimer,Nadine.July’s People[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1.
[7]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53.
[8]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