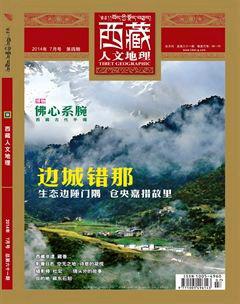阪依高原

在油画界,画西藏题材的画家不少,但像范一鸣这样心无旁骛地只画西藏题材的很少;并且,他的兴趣点不是再现浓艳的风俗,而是刻画高原人内心世界的精神影像。对范一鸣来说,藏区不仅是他创作灵感与素材的源泉,更是他身心生活的现实土壤。
美术评论家韩卫华这样评价范一鸣的作品:“……陡然生涩的出现在眼前,坚硬得如同一块顽石,灰头土脸,却又充满元气。仿若殉道者一般,艰难前行,却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命运冲出肉体的束缚,飘向非现实的时空。也许是这一度有过的天堂无边浩瀚的美丽使范一鸣迷惘,使得他在反复描绘晕染的过程中品味着那份来自人物自身的苦涩和沉重,也使得画家的劳作过程本身便具有了更多的精神意义,他在情感体验过程中做着语言个性化的努力,使自然之物在艺术创作中真正回到自然。”在“绿色”成为噱头、“回归”成为广告词的消费自然时代,范一鸣的回归是真正的回归,回归到身心与作品融为一体的创作。回归到自然人有敬畏的纯洁。虽然在形式上,一鸣并不笃信哪种宗教,但他信命运,信天意,信精神,并坦然接受,虔诚守望。不仅他的作品充满了宗教性的虔诚,他的整个身心也都阪依了高原。
范一鸣是福建人,1967年出生在大田,他的美术基础是在三明打下的。90年代初,一鸣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之后留下来当了北漂,想在都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那些年,他始终没有中断探索和研究,试图找到适合自己的绘画语言。他给自己的作品穿上过古典写实、现代写实、超写实、超现实、印象派、象征派、意象派、装饰派等许多种外衣,虽然也诞生了几幅满意的作品,但始终觉得跟自己隔着,尚未触到灵魂最核心的东西。1999年,一鸣的创作陷入彷徨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抱着去高原“换换脑子”的动机,随几位老画家去了一趟甘南,没想到此行改变了他一生。
第一次踏上高原的土地,第一次呼吸雪山下的空气,第一次离太阳那么近地沐浴阳光,第一次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原生状态,藏区的一切对一鸣来说都是全新的,天,山,云,光,近在咫尺的雪山,像液化水晶的河流,让人想投胎骏马在上面撒欢的牧场;当然,还有藏族人的形象、面孔、服饰、色彩、神态和体态。在西藏,他惊愕地发现了一个幻想过、但并不知道存在的由精神主宰的纯净尘世。一鸣说:“也不知是应了前世的授记,还是冥冥中的牵引,当我满怀热望地第一次踏上高原土地,呼吸着氧气稀薄、却异常纯净的空气时,竟觉得如此亲近和似曾相识!连绵起伏的草场;层层错错如仙镜般的峡谷;甘甜清冽的溪流;空灵的寺院;诵经的喇嘛;虔诚的朝圣者;质朴的牧民,随着行走的进一步的深入,我不断地深切感受到这片土地和她的居住者们那种千百年来一如既往的淡定与超脱。”
去西藏,说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潜意识中他早就怀揣了期待。上初中时,范一鸣有一次在《江苏画刊》上看到了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尽管那时他还没拿过油画笔,但画面使他身心受到的震撼,一直持续至今。当时他就萌生出一个念头:以后一定要去西藏。真到了藏区,他的感受多得难以表述,但状态可以简单、准确地归结为两个字:兴奋。他看到风景兴奋,看到藏族人兴奋,每天醒来,为自己能在这里活着兴奋,尽管他对那里的文化、历史还了解得很少。对一鸣来说,西藏的一切都是崭新的,与他过去经历的事情无关,受过的教育无关,掌握的知识无关,接受的灌输无关……无论有多少人去过那里,但对他而言,对范一鸣而言,这是他为自己发现的新大陆。
当时,他跟所有第一次去西藏的人一样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束手无策,他用眼睛、用镜头、用速写笔试图捕捉一切,记下一切,这才意识到手脚的笨拙、语言的贫乏和大脑的无能。即便他的大脑有上百亿的细胞,但竟然不够他用来记忆一片云。让一鸣的心灵最受冲击的是看到西藏人磕等身长头,每个人都满头满脸满身尘土,虔诚的表情和专注的神态,仿佛透射出光。一鸣说:“我被磕长头人的眼神打动了,那么纯净,那么平和,没有贪求,没有侥幸,跟在内地庙宇里看到的烧香拜佛者截然不同。”
“在西藏,我看到的都是我想要的,重新唤起了我对绘画的热情。高原给我做了一次彻底的洗涤,我脑子里再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觉得过去所谓追求个性、寻找风格都是以空对空的书生匠气;从西藏回来,我的脑子变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念头,回到画室,拿起画笔。”从甘南回来,他创作了第一幅西藏题材的作品《小朗穆》,如受天启,随后又一口气画了《暖融融》、《卓玛》和《天边的歌》。
在藏区采风,他很尊重当地人的感受,而且做事情言而有信。回到北京,他会把照片洗好邮寄到藏区。由于寄信不是总能寄到,保险起见,一鸣会在下次去时亲手把照片交给当地人,当地人看到照片都兴奋极了,像得了宝贝。一鸣说,西藏人诚实,非常守信,所以跟他们交往时,一定要言而有信。这样当地人也会把你当做朋友一样信任。由于他去甘南十分频繁,不少当地人记住了他。他画过的男孩已长成汉子,他画过的女孩已当了母亲,但是他,每次都还是同样的打扮:绿毡帽,大棉袄,每个兜都塞得鼓鼓囊囊的摄影坎肩。一路上总能碰到跟他打招呼的熟人,感觉就像是回乡探亲。
随着对西藏文化、宗教和风土人情的了解,范一鸣越发觉得自己的灵魂属于那里。在苍凉辽远的高原上,在神圣宏大的寺院里,在真纯粗犷的藏族人中,他感受了现代人匮乏的肉体雄浑和虔诚力量。西藏的草木山石花鸟人兽云雾阳光空气和高原所有的一切,都具有某种崇高得令人敬畏、寂静得振聋发聩的雕塑感,激活了画家的艺术直觉和创作欲望。每次走下高原,他都感到精神的洗涤与重生,试图用画笔将他在高原所有的记忆、感觉和顿悟都凝存在山岩般沉寂的画面里。他说:“我在作品里追求化石般的雕塑感,追求坚硬的感觉,传达肉体可通过精神达到的永恒。”
凡是看过一鸣作品的人,都会被他刻画的超时空的凝重所震动。他用沉实浪漫的色彩、肌理入微的笔触和二度半空间的绘画语言悉心经营出一个永恒的精神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不闻尘嚣,不见物欲,希望如暴风雨一样真实,沉郁的天光下彰显灵魂的纯净,他找到的是现代人失去的乐园。文/余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