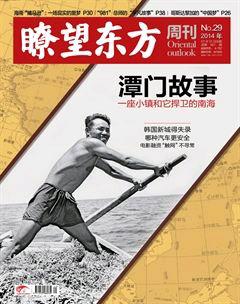启蒙时代的悲剧
杨天


和一些同行不同,77岁的樊树志一直提倡历史知识的通俗化普及,并将之看作历史学者应尽的义务。他曾公开支持易中天和《百家讲坛》,自己也身体力行,写一些通俗的历史文章。
在他看来,“放宽视野,思考消逝了的人和事,对于理解过去与现在或许不无裨益。”
日前,樊树志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读书笔记整理而成《明代文人的命运》一书,集中描绘了明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启蒙新气象”和命运悲剧。
他笔下的明代知识分子,有开国元勋、“国家栋梁”,也不乏受弃于世的落拓名人,乃至挑战名教的异端分子。他们各怀社会理想,但往往以悲剧收场。
“这些悲剧的根源就是延续千年的专制政治。”樊树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皇帝一旦翻脸,你就什么都不是。皇帝的好恶决定一切。”
“直如弦,死道边”
有人说,明朝是一个知识分子风气最坏的朝代,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都堪称空前绝后,表现出传统道德上的危机。
对这种说法,樊树志不以为然。“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懂历史。”
樊树志认为,“直如弦,死道边”的士大夫在明代不乏其人,他们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肯屈服于朱棣而被“诛十族”的方孝孺,与阉党抗争而牺牲的杨涟等人都是其中代表。
即使是屡次变节,被后人多所诟病的晚明文坛盟主钱谦益,在樊树志看来也有其无奈和身不由己。
“他是文人从政的悲剧典型。他经历了7次挫折,做官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不到两年,但始终忘不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清军南下时,他丧失了气节。柳如是曾劝他自杀,他不肯。这是他的性格弱点。”
晚明时期,中国已经卷入全球化贸易中,并始终处于顺差地位。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使人的自主性和自觉性都有所提高,社会变得多元化,思想也越发多元。
在王阳明“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大批“布衣文人”。“他们不迷信经典,敢于挑战教条。这样的思想解放是晚明很值得称道的地方。”樊树志说。
但最令樊树志扼腕的也正是晚明的文人,身处启蒙时代的大变局中的他们,最终却陷入国破家亡的境地。
启蒙的时代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评价明代的知识分子自信而开放,思想自由而又极富创造力,你认同吗?
樊树志:明中叶以后,文人中出现了新气象,有人称之为“启蒙”。我认为这种“启蒙”有两个途径。
一种是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反思,挑战一成不变的教条,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这种反思从陈宪章开始。他主张怀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怀疑什么?怀疑经典,怀疑圣贤。
然后是王阳明,更进一步,提倡“学贵得之心”,如果不是自己的心得,即使是孔子说的话也不认为是对的。这就是怀疑精神。他还说,“学”是天下的公学,不是孔子或朱子一个人可以得而思也,是非大家可以评判。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气,为僵化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后来,王阳明的徒子徒孙们继续为思想解放推波助澜,从王畿、王艮、王襞到颜钧、何心隐,最后到李贽都是反潮流的。李贽说,千百年来无是非,就是指千百年来没有是非的标准,原因是“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东林书院的顾宪成评价他们用了著名的八个字——“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清朝初年的大学者黄宗羲评价他们“掀翻天地”,“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他们在正统的儒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但经典的生命力正在于与时俱进。
启蒙的另一个途径是,从万历开始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当时叫做耶稣会士,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们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等新的东西。
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等跟着他们学习,放眼看世界。在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上,他们看到地球是圆的,中国只占其中很小的位置。这彻底动摇了“中国是天下中央”的世界观。
当时有个陕西人王徵,受耶稣会士的影响,翻译了欧洲的物理、机械、力学著作,并能自己动手制造机械。在以前,像这种既有文化又能动手制作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
所以,到了晚明时期,一个启蒙的时代来临了。
谁最早喊出“打倒孔家店”
《瞭望东方周刊》:成就这种启蒙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樊树志:因为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讲全球化,常有一个误解,认为这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实际上西方学者早就指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时代,又叫大航海时代。
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实现了全球化贸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商人先后来到中国,然后传教士也来了,这个时代就变了。他们(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外部有了更多接触。
李贽为什么会有那么激进的思想?因为他和利玛窦是很好的朋友。而王阳明的一些学生,大都看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世界观随之发生了变化。
这种相互的促进和影响在其他朝代是没有的。元朝虽然也有外国人进来,但是没有形成思想共鸣。正是在这种共鸣的作用下,徐光启这样的传统文人才能成为科学家。
《瞭望东方周刊》:这样的启蒙对后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樊树志:影响非常大。
王阳明的徒子徒孙中最厉害的是泰州学派。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中谈到泰州学派,认为他们最可贵的是叛逆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解放。侯外庐说,这种叛逆精神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他这个评价是对的。
在正统的儒家学者如黄宗羲、顾宪成等人看来,泰州学派是离经叛道的,但是我认为离经叛道好得很啊,不敢离经叛道,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叫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都是行不通的。泰州学派他们就是要对儒家教条进行挑战,所以才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所启发。endprint
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就曾写过一篇《明李卓吾别传》,高度赞扬李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观点是想通的。
我甚至觉得,最早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可以认为就是李贽,因为李贽曾从多方面来破除人们的迷信,让人们不要拜倒在孔子的脚下。
《瞭望东方周刊》:李贽等人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导致了他们自身怎样的命运?
樊树志:李贽、颜山农、何心隐他们可以说都是悲剧的下场。李贽后来被皇帝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著作全部销毁,本人也惨死狱中。
明末清初的张岱曾评价李贽“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这个评论很到位。李贽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不容于明朝当局,因此沦为了专制政治的牺牲品。
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瞭望东方周刊》:明代文人结社之风大盛,这是什么原因?
樊树志:有学者曾经考证过,宋元时期开始有诗社,真正的文社则是从万历时期开始的。
明代的文人结社,最突出的特点是都在江南,比如应社在常熟,几社在松江,复社在太仓。因为这里经济繁荣,相应的文化也比较发达,读书人多,做官的也多。
晚明文人结社公开的口号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但我认为他们真正想争取的是结社和言论的自由。
表面上看,这种结社最初与科举考试有关的,相当于成立了一个考试辅导班,但实际上往往超越了这个目的。因为当文人们考上科举之后,社还在发展,并开始逐渐涉及当朝政治。
文社的成员与一般官员批评朝政的角度不一样,他们往往重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比如万历时期朋党之争日盛,他们就写了很多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朋党的危害,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不要让党争再发展下去,影响安定。
在明朝岌岌可危的时候,几社的成员曾编了一部500多卷的《皇明经世文编》,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目的是让统治者看过后吸取经验,力挽狂澜。
复社更厉害,虽然它发起于太仓,但开过几次全国性的大会,成员有几千人,遍布全国各地,影响很大。他们所造成的舆论声势一度引起朝廷中保守派的警觉,在皇帝面前诋毁他们,但崇祯皇帝下了旨,给这些文人言论自由,不让他们因言获罪。
崇祯十一年,大批复社成员在南京参加科举考试。考完后,他们一起写了一篇楔文——“留都防乱公揭”,揭发阮大铖的老底,吓得阮再不敢出来。当时带头的就有顾宪成的孙子、黄宗羲的儿子以及著名的“明末四公子”。
所以,可以说明代文人的这种结社是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