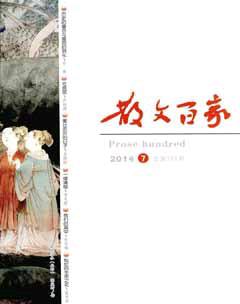一缕清烟
李光彪
天气突然变得刺骨透心的冷。一夜之间,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把云贵高原滇中楚雄覆盖得严严实实。平时葱茏的树木、山川、田野、村庄,仿佛全身披麻戴孝,正在为死去的季节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
接到大哥从故乡打来的电话,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忐忑不安的我心急如焚,驱车赶往百里之外的老家。平时车水马龙的路上,死一般寂静,只有车轮辙雪的声音在沙沙哭泣。车窗外迎面飞来的雪花,如母亲筛面似地漫天飘洒着。
跨进家门,只见母亲蜷缩在床上,由老变小了,变成个咿呀学语的孩子,语无伦次,模糊不清。但我说的话她好像全都能听懂,她说的话我只能靠猜测判断。只知道久病的母亲全身筋骨疼痛,每次回家,都要帮她按摩身子。于是,我和二姐坐在母亲床边,轮流着不停地帮母亲搓揉,希望能为母亲减轻一点点疼痛。就这样心如刀绞地、百般无奈地陪伴着久违的母亲,不停地按摩着,不停地说着话,生怕母亲溘然而去。
母亲仍在呻吟,几只乌鸦在房前屋后的树上盘旋着,唉声叹气鸣叫着。突然间,气喘吁吁的母亲打了几个喷嚏,口鼻喷出些血,如一台停止转动的石磨,悄无声息。我和二姐不相信眼前的现实,声嘶力竭喊母亲,却无半声回应。我急中生智,一边掐母亲的人中,一边抚摸母亲的鼻孔,母亲停止了呼吸。又摸摸母亲的眼睛,眼珠已经白的多、黑的少。再握握母亲的手指,已不能弯曲。就这样,患有“半边风”多年的母亲嘴合眼闭,再也没有醒来。一时间,家里仿佛发生地震,楼房坍塌;满屋就像外面的世界,冰天雪地般寒冷,全家人乱成一团。有的忙着给母亲往嘴里放“含口钱”,昭示母亲到了另一个世界有穿金戴银、吃穿不愁的口福。有的忙着“留后”,要留点母亲生前的金银首饰或是衣物,以示后人财源不断,厚衣锦食。母亲的一切后事,在美好的祈祷中展开。趁着母亲的余温,我们请来邻居,配合着给母亲洗脸、理发、擦身,从头到脚给母亲更换鞋袜、穿戴寿衣寿帽。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母亲做护理,也是最后一次。转眼间,打扮一新的母亲像个整装待发的新娘,脸盖红布,安详地躺在床上。
人死不能复生。接下来,我们在为母亲装棺,在熊熊的火把照亮下,七脚八手往棺材里铺垫草席、棉花、枕头,连抱带提,把逐步变得僵硬的母亲放入棺内,再用些平时母亲舍不得穿的衣物塞紧、镶稳、填满,给母亲盖上红彤彤的寿被,为母亲布置了一张万紫千红的床。经过赶来为母亲吊唁的舅舅家“眼盖”(过目验棺)后,棺材盖子被合上。我和母亲对视的目光,在叮叮当当锤敲钉子的声音中被扎断。母亲就像小时候和我玩躲猫猫一样,明知她藏身之处,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仿佛感觉那锋利的寸钉不是扎进棺木,而是扎进母亲的肉里,扎在我的心上。从此,母亲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母亲那千言万语的牵挂被扎进了棺材。我和母亲近在咫尺,却如一堵墙、一座山挡住了我的视线,割断了我的脐带。刚才还安详瞌睡的母亲,却变成了黑黝黝的棺材,升在堂屋里。我跪在母亲的棺材前,磕了三个头,点燃三炷香,第一缕清烟开始升腾,那是母亲的化身。
透过那一缕缕清烟,母亲生前陪伴我的如烟往事,也历历在目,飘来眼前。
我是母亲身上掉下的最后一砣肉,是母亲常说的“虾尾巴”。幼年时我很“认生”,经常像块磁铁粘在母亲身上,谁也抱不去,只要离开母亲就会嚎啕大哭。父亲爱长子,母亲爱幺儿。母亲没办法,只好用裹被背着赖茅的我干农活、做家务。有时,母亲把我带到田间地头,采几朵野花,或是摘几个野果,捉些小虫、小动物给我,让我坐在羊皮褂上,一边玩耍,一边看母亲做活计。尤其是每天晚上睡觉,我像头钻进母亲怀里拱奶的猪仔,吃着母亲的“老瘪奶”进入梦乡。直到六岁上学那年,母亲悄悄用猪苦胆汁涂在乳房上,接连几天中招,才把我从奶头上抹了下来。但我仍然像条恋娘的小狗,喜欢缠绕在母亲身边。有时母亲去走亲戚,我总要撵路。若母亲不带我,我就会又哭又嚷,大闹天宫。如果母亲隔夜不回来,晚上就会莫名其妙地怕,总要约小伙伴来家里陪我睡觉,直到母亲回来,一见如故,我才风平浪静。
上学了,母亲总会把我送到村口,一遍又一遍嘱咐我:“到学校要好好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写字,不要跟人家闹。”每天放学回家,见不到灶房顶上的炊烟,我跨进院门,就会一边喊一边找母亲,直到看见母亲,才心安理得。
童年的我最喜欢打陀螺,常遭家里人反对,认为打陀螺“不务正业”,误了拾粪、找猪草的时间。有一次,我背着家里人偷偷砍陀螺时,不小心用刀砍伤左手,母亲急中生智,迅速刮了些锅底灰敷在我的伤口上,再用布包扎,两三天换一次“药”。好长一段时间,母亲不让我拾粪,不让我帮她打下手,只让我吃现成饭。那年腊月,院子里家家进行卫生大扫除,一大堆渣渣草草就地燃烧,我和几个小伙伴赌嘴,看谁能从火堆上跳过去。个个都跃跃欲试,却谁也不敢打头阵,胆大、不服输的我却不知水深火热,蹦蹦跳跳冲过去。由于跑的距离短、起跳的助力不够,后半身栽进了火堆里。当小伙伴们把我救出来时,我的双脚已被烧伤。母亲闻讯赶来,立即用小伙伴的尿给我搽疱疹,然后背起哭哭啼啼的我,跑到山那边去找赤脚医生。那一夜,疼痛难忍的我像一个找娘的婴儿,哭声不止,弄得母亲像个陀螺围着我转,泪水盈盈陪着我,一夜没合眼。
不知什么原因,逐渐长大的我开始讨厌母亲的唠叨,开始躲避母亲的目光,开始逃离母亲的“紧箍咒”。可母亲生怕我像一颗糖,含在嘴里怕化了;似一只雏鸟,捧在手里怕飞了,总是盯得很紧。吃饭不见我回家,母亲就会站在大门口,像个高音喇叭似地呼唤我的乳名,喊我回家吃饭。有时我玩过头,晚上迟迟不回家,母亲就会找猪鸡似地满村子挨家挨户找我,生怕我在外面受冷挨饿,惹是生非“闯祸”。
背着油盐柴米到狗街住校读初中以后,与母亲彻底断奶隔槽的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可我却莫名其妙地想念那个以母亲为圆心的家。每个星期天回家背柴米,见到曾经朝夕相处的母亲,我却像只离群掉队迷路的羊失而复得回到母亲身边,倍感亲切。转眼间三年初中毕业,我已有母亲的肩膀高,哥哥姐姐娶的娶、嫁的嫁,家庭成员不断增加,侄儿男女也如一茬茬庄稼不断长大。嫂子们的心里也各自打着分家的“窝心炮”、扒着另起炉灶的“小算盘”,在一片婆媳妯娌不和的吵嚷声中,热热闹闹、枝繁叶茂的大家庭被分为四家。就这样,生活的疙瘩把一老一小的母亲和我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分家另立门户,相依为命。从此,我像一头不愿上套拉车的小马驹,像一头不愿上架拉犁的小牛犊,更像一只羽毛长硬的鸟,出巢离家,从这个城市漂泊到那个城市,到处打工闯荡,可怎么也找不到安身歇脚的地方。我像一条背叛母亲的狗、一只背叛母亲的猫,一次又一次地逃离母亲,却一次又一次失望地凄丧着回家。儿是娘的心头肉。那杯暖身的热茶,那盆热乎乎的洗脚水,那顿香喷喷的饭菜,是母亲一颗滚烫的心对我最大的宽慰。
后来,幸运进入城市的我,结婚成家,以庄稼为友、猪鸡为伴的母亲进城来帮我带了十四年孩子。十四年,目不识丁的母亲不会上防盗锁,不会打电话,不会用洗衣机,不会用电视机遥控器,不会看钟表,不会看电表、水表,不会看过马路的红绿灯,不会……十四年,不少朋友请我吃饭,母亲总是说她缺牙没齿的,从没参加过,生怕丢我的脸;十四年,母亲却背着我偷偷去捡垃圾卖钱,为我们买些小菜,给女儿零花钱;十四年,母亲不是进城享福,而是被亲情绑架、活受罪;十四年,我看着母亲的头发一根根变白,皱纹一条条变长变深,腰一天天变得弯曲佝偻。更何况母亲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病越来越重,必须天天服药,最后得了中风,生活起居不便,只好让母亲告老还乡,回到老家由大哥、大嫂照顾。可离家多年已成客的我,每次送药回家,看见风烛残年的母亲拄着拐杖、扶着墙壁挪移的身影,心就会隐隐作痛。总担心母亲像那些不知不觉消失的老房子、老农具,不知不觉枯死的老桃树、老梨树,不知不觉离去。而乐观向上的母亲总是说:“现在我领着国家的工资(高龄补贴),吃药住院不需出钱(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我要活到一百岁,多享几年福。”
母亲的死,于我们而言是悲痛的。而八十八岁高寿的母亲,却又是令我们问心无愧的。不少父老乡亲建议我们,要把母亲的丧事当做喜事办。于是,母亲的白喜事在亘古不变的乡俗中,在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指挥下,一套一套有条不紊进行着。喜事逢请必到,白事不请自来,村邻乡党来了,三亲六戚到了。杀猪宰羊,炮竹声声,一切都在为母亲践行做准备。
主丧者是家房邻居二叔家的哥哥,为母亲举行葬礼的是那帮乡间十里有名的“道师”。一声锣鼓铿锵,主丧的哥哥手握剪刀“破孝”,一块块白布、红布系满母亲的棺材,接着从大到小分发孝布,儿子戴长孝,其他人戴短孝,孩子戴红孝。全家人在母亲的棺材周围齐齐跪下,悼念母亲的仪式在“道师”叮叮当当的锣鼓声中拉开序幕。“道师”说唱有词,抑扬顿挫,忽高忽低,忽快忽慢,把我的思绪拉得忽松忽紧。顷刻间,哭声此起彼落,满屋的孝子、孝女、孝孙、孝媳都在为母亲大合唱。
送母亲的良辰吉日时不我待,我已无回天之力拉住母亲,却希望意义上的母亲能在家里多陪我们几天。母亲永远安息了,但她的灵魂还在家里。我们兄弟三人连夜为母亲守灵,香烛一支接一支点燃,烧一次香烛、跪拜一次母亲。小时候的我,一听说村里死了人,晚上睡觉就万分恐惧,常用被子把头捂紧,贴在母亲身上,巴不得钻进母亲的肚子里。那年,母亲得了一种怪病,在床上躺了好多天,汤水不进,家里人请来巫婆,原以为神药两解能为母亲治病,但从巫婆口中得知的却是母亲的名字已经上了天国的“黑名单”,阴曹地府派来的兵将正在前来捉拿母亲。巫婆的话如晴天劈雳,吓得我白天不敢接近母亲,夜里不敢回家,跑到小伙伴家去睡觉。后来,幸亏当兵的大哥及时带回针水、西药治疗,才驱散了全家人心中的雾霾,母亲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传说中死人会变鬼“回杀”害人的真相。人人都说怕鬼,其实谁也没见过鬼啥模样。母亲啊,有你在,我的根就在;有你在,老家就在;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母亲闭上了眼睛,村庄闭上了眼睛,星星和月亮闭上了眼睛。夜,在猫头鹰的吼叫中越来越深。母亲是一本书,我们三兄弟不停地翻阅着、重述着母亲昨天的故事,滔滔不绝。鸡叫黎明前,我们三兄弟在村庄外的十字路口点燃香火,为母亲烧过五更纸,给母亲留下买路钱。然后,去村庄后的坟山为母亲选择好葬身之地。举行完破土仪式,等待天明,将为母亲挖土开井,一切都在为母亲安新家做准备。
转眼就到了中午饭后送别母亲的时刻,一切准备就绪,“道师”一声锣鸣,召唤我们在母亲的棺材旁跪下,开始“应事”,为母亲举行告别仪式。“道师”用针戳扎身为长子大哥的手指,挤出一滴滴血,抹在母亲的棺材上,抹在家堂供奉的神主牌上,意指我们和母亲虽然阴阳两隔但血脉相连,母亲虽然走了但她的灵魂仍在家里。又是一阵敲敲打打,乐器声、说唱声、哭唱声汇成了一曲与母亲永别的哀歌,高亢悠扬,响彻屋里家外、房前屋后、村庄上空。随后,母亲的棺材被七八条汉子用铁链、皮条、抬杠拴稳,缓缓抬起。我们三兄弟在“道师”的指挥下,端着不灭的香火、神主牌和母亲的遗像,走在母亲的前面,为母亲引路,送行的人群尾随在母亲后面,在村庄通往坟山的路上蠕动着。炮竹声、哭诉声、锣鼓声不绝于耳,睡在棺材里的母亲仿佛是坐着花轿离开村庄喜气洋洋地出嫁。
前行的路离坟茔越来越近,我和母亲离别的时光如阳光下的雪在不断融化。母亲的身影仍让我挥之不去。在我记忆的档案馆里,父亲体弱多病,是一根村里人常说的“扶不起来的猪大肠”,不拿气,不管事,放了一辈子的牛,从没干过背挑扛抬的重体力农活。而母亲则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村里人翘指夸“嘴有一张,手有一双”的硬婆娘;是一粒有滋有味的胡椒、草果、花椒、小米辣;是一头脚不落地奔波,累不死的牛、马、驴、骡;是一株风吹雨打、冰雹霜雪冻不死的蔬菜庄稼;是一棵支撑着全家人油盐柴米、衣食冷暖的参天大树。夜以继日像只母鸡呵护着我们兄弟姊妹六个。我们一天天在她的翅膀下刨食成长,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可当把我们拉扯成人时,母亲已变成了一把砍不了刺的老柴刀,已变成了菜园埂上那棵寄生满枝、果实稀疏、越来越枯萎的老柿子树,已变成了家里那只下空了蛋的母鸡、那头失去生育能力的母猪,母亲仍在腰弓马爬地忙碌着、挣扎着。想不到眼前的母亲还是抗争不过病魔,踏上了黄泉路。母亲啊,不管你走到哪里,我永远是你眼中的孩子。小时候,你生怕我细小的喉咙咽不下饭,不知多少次咀嚼喂我;无知的我,曾经尿过床,拉过尿屎在你身上,你却从来不嫌弃,任劳任怨擦洗。那个年代的我,肚子里会生蛔虫,你让我吃了几粒打虫药“宝塔糖”,第二天解手时,蛔虫夹在肛门,我又怕又哭,你顺着哭声跑来,用手把我屁股里的蛔虫掏出来,不停地帮我揩屁股。而当你老掉牙了、半身不遂、卧床不起、需要别人照顾时,一把尿一把屎养大的我却远在天边,没为你喂过饭,洗过脸脚,端过屎、端过尿。偶尔回家,影子又一阵风飘走了。而你一听到我的手机响,听到电话里别人和我说事,就会催我回城,说我工作忙,你好好的,什么都不需要牵挂。直到今天,生不带半根草来的你,给予了我们很多;死带不走分文的你,却让我欠下了一笔无法偿还的哺乳债、母子账。我今天来送你,仅仅是个过程,也是迟到的陪衬。
安葬完母亲,我在母亲的坟前点燃香纸,叩拜磕头。面对袅袅清烟,我才方如梦醒:我陪伴的不是母亲,而是一缕清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