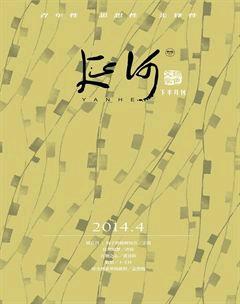时光倒影里的敦煌(外一篇)
孟澄海
黄沙接近天空。
黄沙的远方是雪山、冰川、云岫、苍崖,还有岩羊和雪豹的影子。
站在敦煌的河边,只能看见幽蓝或苍黄的背景。黄的是沙丘,或者说更像月球表面的环形峦影,在不被觉察的漂移、流动中,显出一种古远的苍茫;而幽蓝者则是祁连云峰,无论黎明还是黄昏,都发着一种蓝宝石般的光芒,若隐若现,恍如梦境。
身边的河水寂静无声,波浪不起。因为是季节性河流,所以时常枯竭。当地人说,断流后的河床乱石嶙峋,荒草蔓延,是狐狸和野兔的家园。我想,他们说的大概是冬天。现在,在我的脚下,尚有一脉清流绕过河滩,缓缓向前流淌,穿过盐渍飘白的沙漠,消失于远方。我发现,锯齿般的岸上,一些孤独的蒲公英于芨芨草,默默生长,橙黄和银白的花穗在风里摇曳,仿佛宣示老天荒的孤独。流水如同记忆,在不断流逝的过程中,将一座千年古城的兴衰历史摇荡成零落的雪片、烟尘、碎屑,然后再进行复原与拼接,供来往得行人凭吊、思考。
有个诗人说:像河流一样回望。
回望敦煌,从不同的视角,牵连那些远去的岁月,我们将看到:洞窟、神龛、佛像、壁画、雕塑、生锈的箭镞、坍塌的古墓、斑驳的陶器、枯索憔悴的道士、僧侣、外国探险家、中原士卒和贵胄、美术家和画工,还有朝拜佛窟的香客、寻求浪漫的情侣,出卖青春的风尘女子……
那么多的景观,那么多的人事,渺渺,茫茫。仿佛沙子,被风吹聚起来,笼罩如血残阳,成为遗世独立的风景,接下去又慢慢散失、飘落,无影无踪。每一个朝代都凸显壮观与繁华,后来渐趋暗淡,在时间的长河里沉寂,等待下次苏醒,再次展现博大恢弘。冥冥中,好像有一双手托举着岁月的沙漏,在敦煌的那个月牙泉边,筛选历史的影像,使过往的一切都倒影于清澈的水中,幻影幻现。
我只有一个人。在敦煌浩茫、寥廓的背景里,孤寂得像一棵树。一棵树置身沙漠,那是宿命,一个人也如此。党河谷地,只有白杨树,还有零星的胡杨,根植干燥的河床,生命却活泼旺盛,一律挑着令人心醉的绿色叶子,将枝头指向敦煌。游人不会注意一棵树,他们从那些廉价的景点上归来,就匆匆前往热闹的街市,或购物拍照,或游荡闲逛,或挤进豪华的酒店大快朵颐,或隐身某个娱乐场所体验刺激。21世纪的敦煌,俨然成了丝绸之路上的煌煌都市,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地方令每个唯物主义者灵魂出窍,神驰心往。
跟一棵胡杨照面。
那是一种仔细的审视和解读。我发现那棵胡杨已经苍老,树皮皴裂,露出褐色的纹理,大概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霜侵蚀与雷电烧烤,一半主干已经枯朽,伤痕斑斑。据传,胡杨活着千年死,死去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朽,如果将它一生的年代连续相加,那么这树起码也活过了三千年。年轮一圈圈缠绕,难以计数。年轮便是胡杨的记忆,从内心延伸至灵魂,铭刻人世沧桑。我想,一棵胡杨,可能通向敦煌神殿,永恒地追忆那个古城的前世风烟,但它不说话,以沉默的方式喻示敦煌的今生来世。
敦煌很远,远在时光尽头。
与我而言,第一次知道敦煌,源于一部电影。那部影片,根据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拍摄而成。由于年代久远,所记只是一些片段:沙漠戈壁、如血残阳、杂沓的马蹄声、战火熊熊的古城、惊天动地的爱情……《敦煌》的主人公赵行德身上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他放弃在宋朝科举、做官的既定前途,凭一时的兴趣到河西的沙漠里流浪,探寻自己所不了解的文化,见到美好而珍贵的事物将被毁灭便拼命去拯救,回鹘公主给了他爱情,是他想要拯救的一个人,但是最后还是被毁掉了,然后敦煌的文化又吸引了他,但是敦煌也将要被毁灭,于是他又拼命的拯救敦煌的文化典籍,在血与火中走向永生。
有时候,穿越或抵达一个地方,总伴随着早年的缅想,所谓梦牵魂绕,其实也是一种缘分,包括受某一类影像的感染,某几段文字的牵引。从看过井上靖的《敦煌》算起,我对那个古城的憧憬,业已等待了数十年光景。这中间,时常在恍惚的梦境中于敦煌相逢,却依然是模糊的瀚海、空旷的戈壁,还有朝圣的人流,飞来飞去,像黑色的蝶影……
这一回,终于走近了敦煌。
想象中,那可能是河西走廊西段唯一留存的古代城池,有绿洲环绕,流水潺湲,美若江南。然而事实是,在酒泉以西,古城一座连着一座:锁阳城、石包城、大方盘城、古塞城、六工城、肖家城、寿昌城……城垣兀立,墙壁倾圮,寒鸦万点,到处散落着残砖断瓦、陶片箭镞、朽木碎屑,间或还有人头兽骨的残片,在阳光下闪着骇人的白光。那些坍塌的古城就这样默然无语,独对着萧萧西风,与敦煌遥相呼应。
敦煌不是圣城,没有神庙和祭坛,甚至连香火也早已消散于历史的天空。跟其它宗教场合相比,缺少那种信徒喧嚷的迷狂情景,也不见柏香袅绕、梵呗缈缈的神秘气氛。世上的宗教建筑大多巍峨恢弘、端庄肃穆,藉此来宣示精神力量,震撼凡俗心灵。有些还将屋脊穹窿不断向上提升,宛若神灵手势,将朝拜者的目光引向天国。而敦煌的建筑却开凿在砂岩之上,那是一种洞窟,有门无窗,远离雕梁画栋,因为简陋,因为拙朴,才成了神祗的居所。佛陀和观音耐得住寂寞与冷清,他们住在高高的绝壁上,俯瞰芸芸众生。
仰视,莫高窟就在头顶。
少雨,无水,干燥的崖壁呈现一片灰褐。从地质纪年上推测,敦煌砂岩大概形成于中生界侏罗时期。夐古邈邈,让人无法猜测藏身于此的一只三叶虫和古莲子的前世今生,而那些萍踪浪迹的远古生命,即使它们依赖有限的想象,也抵达不了我们生存的光阴开端。不过,那层叠的砂岩似乎有着永恒坚守的胸怀气度,永不颓靡,没有垮塌和断裂,从扭曲变形的折痕里,凸显着被沧桑岁月磨砺后的坚韧、决绝。也许正是看中了这点,才使后人敢于运用斧凿,在其上开辟出一排排陈设信仰和精神的石窟。砂岩包裹着莫高窟,深藏在黑暗中,阴冷、荒寂,无始无终。我想,那里本应该有灯,是心灯,不是油灯或点灯。那盏灯就放在洞穴的冥灵深处,于幽幽的时光里点亮,梦幻般的晕光,映现着另一个世界:钴蓝绛红的色彩、飘逸灵动的线条、慈祥睿智的面容,还有千年莲、菩提树、金刚杵、药叉剑……
玛雅古城、马丘比丘古城、印加古城、吴哥古城、迦太基古城、庞培古城、佩特拉古城……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上,那么多古城或坍塌倾圮,或被风雨剥蚀,或让黄沙白草湮没,只剩下断壁残垣、西风流云、荒草古藤。
唯有敦煌留存了下来,文化和历史渊源不断,一直向前喷涌、流淌。
大漠边陲,上无飞鸟,下无鼠兔,更无色彩与声音。渥洼池里的水泊着天光云影,昭示永恒的美丽和寂寞。
我想,这里一定有过兵家争夺的险要,王权必夺的繁华。
时光后退两千多年,那时的汉朝,武帝扩张军备,经略西域,在辽阔的河西走廊设置四郡,于是,一条长长的路出现了。这条路来自中原的长安和洛阳,从这里通过玉门关和阳关,分作南北两道,直入古称西域的新疆,沿着人烟绝迹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边缘平行西行,越过葱岭,穿过中亚诸国、西亚的安息和两河流域,直抵地中海南岸的埃及和北岸的希腊罗马。这条路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最繁华的、贯通东西方世界的大道——丝绸之路。
从那时起,驼队、马帮、胡商、出使中原的官宦、头巾遮面的僧侣沙门、盗墓贼和探险家、行吟诗人与歌姬,就在丝绸之路上往来行走,川流不息。中原的铁器、瓷器、茶叶、打井技术、农耕手法传到了西域,而西域的胡麻、胡萝卜、胡饼、胡乐、胡舞相继进入了中原。
而在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旅与使团中,夹杂着笃信佛教的信徒,无形中又把公元前五世纪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播进来。
公元一世纪左右,敦煌其实还是一个繁华的都市,商客云集,胡乐震天,客栈与酒肆,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笙歌琵琶、胡姬翩翩,日夜不尽喧嚣与骚动……
直到纪元366年,有个叫乐僔的和尚途经敦煌,据说,当他驻足眺望之时,三危山前突然闪出金色的光芒,宛若万千佛像,若隐若现。乐僔坚信那是佛祖的降临的吉兆,预示圣灵再现,于是独自登临到对面的鸣沙山,在那里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这之后,便有了第1个,第2个……第700个。
我曾在乐僔行走的地方逗留,想象或盼望那一缕佛光从三危山顶升起,照亮我肉体和心灵的暗夜,但我什么也未看到,目光所及,是灰黄的沙碛、崖壁,是深蓝空洞的天穹。站在鸣沙山的阴影里,我感觉到自己就是沾满尘灰的树叶,苍黄、憔悴,无力飞跃到那一片精神净土。
莫高窟的洞窟大多安装着厚重坚实的铁门。现代管理者的说法是,防盗,防风,减少游人的践踏破坏,理由凿凿。关了门,上了锁,一切安然,让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默然独对黑暗,延长文物的存在寿命,同时也隔断了探究、思考、审美的目光。盘桓于那些铁将军把门的洞窟前面,我总是不由得会想起斯坦因、伯希和、王元箓、张大千、常书鸿……他们,那些或高大或卑微的人物,能够在遥远的某个年代,进入幽暗的石窟,长时间在壁画与经卷佛像间留恋往返,那该是多么的幸运。
我跟着导游,穿过一个当代代人修建的牌坊门楼,径直踏上了悬在石壁的栈道。这里的栈道设计简陋、粗糙,人经过时吱呀作响,提心吊胆。尽管如此,游人还是前拥后搡,把照相机镜头对准崖壁间的洞窟,拍摄一些无关宏旨的照片。叽喳呼叫,一片喧嚣。应该说,越是接近宗教艺术世界,越要心怀虔诚敬畏,但这里却正好相反。两千年的历史掠过云烟掠过山头,留下辽阔深邃的精神辉光,但无法普照人世的每个灵魂,使他们仰起脸,安静下来。
208号、209号、311号、322号、405号……洞窟门楣上的号牌,按照朝代顺序编排,标示其身份和地位。没有命名,每组数字代码,都隐含着时光的走过的足迹,仿佛王朝的年历,一页页翻开:汉、魏、三国、两晋、北魏、隋、唐、辽、宋、元、明、清……
早年读历史,时时被魏晋文化熏陶感染。此行目的之一,就是能够亲临敦煌莫高窟,看看其中的壁画,包括那些风神俊朗、略含忧郁的秀骨清像。我见过《敦煌画册》上的一帧北魏菩萨画像,肤色白晰,体形清瘦文弱褒衣博带,姿态伸展舒长,衣裙飞扬,充满飘逸豪迈的艺术张力,那种风韵气质,令人神往。然而不巧的是,那几个时代的洞窟没有开放,望望紧闭的大门,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暗淡、怅惘。
下午。银箔似的斜阳从山巅上落下来,铺满了人行栈道。风很大,吹过砂岩的罅隙,仿佛有谁在演奏陶埙,呜咽之声四起。朝山下看去,那里的沙丘依旧平静,若酣睡的骆驼,静卧于空茫瀚海。
导游把我们带进了230号石窟。
很宽敞的一个洞子,有陈年沙土腥涩的气息。
借着淡淡的天光,我看见了窟顶的壁画藻井:钴蓝的颜色象征天空的浩渺、深远,云朵则呈现卷草和忍冬花纹,流动、飘逸,好像刚刚从遥远的天国飘来,周围是飞天女神,她们长裙舞动,裾带飘摇,这厢在播撒花朵,那厢在反弹琵琶,还有乐伎舞女,蝴蝶般翩跹起舞……
石窟四壁画满了《阿弥陀佛经变》的故事。
画上碧波荡漾,莲花盛开。阿弥陀佛趺坐在中央莲台上,双手作出正在说法的手势,观音与菩萨侍立两旁。背后是经幢凌云,梵宫耸峙,花树成荫,祥云缭绕。神佛诸生,水榭回廊,讲台精舍,珍禽异鸟,拥绕出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所有的地面都铺着金银、琉璃、琥珀、珍珠、玻璃、玛瑙七种宝物;整个天空一碧万顷。众天神驾彩云而至,洒落漫天鲜花以示供养。各种乐器高悬空中,无人弹奏,凭空自鸣。宝池前雕阑玉砌的栏杆紧紧围绕歌台,乐伎们且歌且舞,其乐融融。
我终于明白了:这里是唐朝的天国。
羌笛、筚篥、鼙鼓、琵琶、月琴、箜篌、胡腾舞、胡旋舞、霓裳羽衣舞……胡乐、胡舞、胡风、胡俗,人间的欢乐折射于天国,天国的美景诱惑着人世。只有在大唐,只有在盛世,才会有天人相和、人神共乐的场景。大唐是音乐的朝代。朝野上下都是乐迷。朝廷日日举办音乐会或歌舞会,帝后王侯皆善乐舞。唐人对外来文化,只要喜欢便放手拿来,大包大揽。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这些来自西域胡天的音乐,经唐人修改加工,成了抒发天朝情怀的载体、工具和符号。
梦回唐朝。
可惜一切都远去了,如风如云。
留下的只有那冰凉黑暗的石窟,画匠笔下的佛陀世界,还有那寂寞的飞天,缥缈的神女。
我知道,敦煌还在继续,但迟早有一天,它也会成为无边岁月中的一个倒影,苍茫、孤独、决绝……
祭天者语
午后或黄昏。
仿佛是预设的两个渐次靠近的时空片段:无风无雨,山河岑寂,一脉河水叙述着孤独寂寞,从我脚下流过,打碎了我恍惚的梦境……
一个人在荒原上行走。
没有背景。或者说,因为人的渺小,使背景显得空阔、苍茫乃至虚幻。
走走、停停,再走走,再停停。有时候,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慢慢地抽吸、回味,让目光随着烟圈飘向远方,氤氲出一种地老天荒的忧伤。
我的前面就是祁连山。
阳光斜散,从光线的切面处,可以望见那里的塔松、云朵和石崖,偶尔闪过岩羊和鹰鹫的影子,匆急如风,恍若鬼魅。还有那些残雪,那些古老的云岫,被一种淡淡的蓝光笼罩,幽邃、空旷、神秘。
一座古城的废墟横亘在我的面前。
那只是一个瞬间,我发现有两只荒漠的雪狐躲在坍塌的城墙的阴影里,朝我张望,眼神慌乱惊悚,然后迅疾逃去,像两朵火苗,在荒野的草丛中消隐、熄灭。它们的背后只留下了一串串零乱的爪印,宛若凋落的梅花。
它们是古城的幽灵么?
再抬眼,废墟周围已是空空荡荡。
随处散落着岁月遗弃的物件:陶片、残砖、牛头骨、马蹄铁、生满绿锈的箭镞、花纹奇异的瓦当、鸽子和老鼠的尸骸……
最重要的祭祀场地还在。一个石祭坛,灰白的石头相互勾连,错落有致,搭建成两米高的建筑。石头上苔藓斑驳,地衣苍苍,从罅隙间长出的芨芨草挑着暗黄的穗子,也有叫不出名字的野花,艳丽却不轻佻,于阳光下独立苍茫。
历史上说,这一处高原古城曾经是匈奴单于的王城,后来匈奴败北,又相继居住过吐蕃人、鞑靼人、突厥人、回鹘人。
他们都远去了。渐行渐远的背影里,飘落着时间的尘埃和雪片,一切被掩埋和覆盖,只留下石头祭坛。天似穹庐,高高在上,而石头静卧于地下,等待灵性注入内心,然后复活,给我们再现历史记忆,或苍凉、沉重,或斑斓、诡异。
从废墟的墙头那边飞来一只蝴蝶,黑翅,米黄斑纹,触角极长,硕大。在我故乡,人们把这种蝴蝶称作“鬼钻墙”,因为它们飞行诡秘、隐蔽,所以很少被人发现,又说那蝶会给人带来厄运,是神煞之类的东西。不过,我查过有关资料,知道它们叫枯叶蛱蝶,外形极其美丽,但从破蛹化蝶,一生不过百日,命若琴弦,遇风即断。
黑色蛱蝶绕着那个旋舞,翅膀上的金点光灿炫目。
我突然有了幻觉:那不是神秘的巫师亡灵么?
在遥远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每年要进行多次祭祀活动,无论是祭祖、祭神,还是祭天、祭山,都须有巫师参与,那些人被称为萨满。
萨满是人与神的中介,他们可以代表人的意愿,面对上天,呼唤神灵下凡,帮助人解灾禳祸,也可以直通冥冥世界,让神灵附体于人。
上大学那年,偶尔去某城博物馆,在光线幽暗的角落,我见到了一幅古画,其上绘制着祭神的场景:萨满黑衣玄裤,头戴面具,手握宝剑,屈膝,仰脸,做出腾挪跳跃的姿势。画面上还有树木,似乎受萨满舞动的冷袖清风吹拂,以致枝干低垂,落叶飘摇。而围绕萨满的身前身后,则是褐色的云朵和纷扬的雨丝。整个绘画主题表现的是萨满祈雨仪式,氛围惊天泣神,肃穆而悲美。
我从未亲历过祭祀天地的大型场面,更无缘目睹萨满的真实面容。只记得青年时代,为了写诗,找寻一份荒寒苍凉的灵感,曾与几个文学青年去了祁连山深处。那里的山岗是石灰岩地貌,白雪覆盖乱石,丛莽之间有一个石台,上面零散地撒落着人骨、毛发、血滴,还有衣服的碎片、鸟雀的粪便、鹰隼的羽毛。有人断言,那地方应为藏民的天葬场。那一次,在天葬台的雪地上,我们遇到了一个红衣喇嘛,他静坐于那里,两手合胸,喃喃地诵念着超度亡灵的经书。
多年以后,留存在我记忆中的依旧是那红衣喇嘛的身影,以及他们身后的背景:雪山、白云、幽深的峡谷、空旷的山坡……《萨格尔王传》上说,经师是佛国世界绿度母的使者,他们带着神的旨意,在逝者的身边洒下花朵,然后引领亡灵走进雪山。当神鹰啄食完最后一块尸骸,神与亡灵就可并行远去,走过雪山的每一条小溪,每一个叶子,每一朵白云……
不过,超度亡灵的喇嘛并非是远古的萨满。
读史料,知道“萨满”一词也可音译为“珊蛮”“嚓玛”等。该词源自通古斯语与北美印第安语原词含有:智者、晓彻、探究、等意,后逐渐演变为萨满教巫师即跳神之人的专称,也被理解为这些氏族中萨满之神的代理人和化身。在匈奴时代,萨满在政治、军事上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凡战争或其他处于犹豫状态的事件,最后要取决于萨满。萨满必须具备许多常识或知识,能够观察事物的发展,预测未来,敢预言吉凶。
我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荒漠古城。
残阳渐渐消沉,雪山上升起一瓣菊花状的弦月,淡蓝的天光、还有晚风和迷离的沙尘,开始笼罩那个破败、萧瑟的城垣。乌鸦成群,站立于倾圮、垮塌的墙头,与我对望,眼瞳里弥散着刻骨的迷惘和忧伤。淡淡的星月下,那个石头修筑的祭坛,荒草摇曳,野花凄迷,没有鸟影与人迹,兀自沉入冰冷的黄昏。
如同被时光埋葬的繁华和喧嚣,那些曾经统治了古城的首领、贵胄、士卒、乐女,以及他们的琵琶箜篌、急管繁弦,还有权利、阴谋、欲望、梦幻,全都成了岁月的灰烬,深埋于古城的地下。
二十一世纪初叶,有当地农民在古城的墙基边挖开一个豁口,试图找寻前人藏下的宝物,但费尽心思,只挖出一具枯朽的人体骨架。据说那个尸骨是女性,刚出土时,肉身完好无损,长发覆面,腰际上挂一面铜镜,背面镂刻七星北斗、云彩仙鸟,不过女尸遇风即散,除骨殖之外,其余瞬间化为泥土尘埃。
有考古人员推断,那个女性尸骨应为匈奴时代的萨满。
古城废墟,默然无语。
而我,面对那个被荒草野花覆盖的祭坛,大脑沟回中渐渐闪出一组画面:深蓝的天穹下,古城的谯楼女墙、斗角飞檐轮廓蜿蜒,柔美如画,羌笛鼙鼓突然响起,此时,萨满款款登上祭坛,她的面具狰狞可怖,铜镜发着幽光,腰身像蛇一样扭来扭去,将神秘的宝剑指向星空,而祭坛下,一大群身着狼皮的匈奴匍匐在地,聆听着从她口中吐出的祷语……
我想,那应该是匈奴部族在河西走廊的荒原上举行的最后一次祭天仪式,之后他们就逃离了这座美丽的山城,骑马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戈壁和大漠深处。
那个妖冶秀美的萨满究竟在祭坛上说了什么,是谶语,还是神谕?抑或是天谴的密令?数千年后,没有谁能破解其中的谜团。
只留下一座废弃的古城。
古城先是被风雨慢慢侵蚀,一点一片地剥落,直到地基塌陷,墙体崩落,成为狐狸和寒鸦的家园。
民间传说,萨满女巫能够通天达人,她可以卜测个体生命的吉凶祸福,也可以推演一个名族、一座城池的繁华盛景和落幕结局。在每次祭天的时候,她可以获得上天的某种暗示,那种言辞和咒语,独成体系,犹如埋入古墓的青铜、古陶,那些只有在黑暗中生成的锈斑、图案,以及那些恍惚的水波纹路,它的所指与象征,永远无人参破玄机。
但历史的吊诡是,不管萨满如何神奇,如何诡秘,最终也难逃时间的惩罚,她们最后也会相继死去,剩下一堆朽骨,安睡于荒原的西风流云之下,默默地守候着古城的最后一抹夕阳。
也许,祭天者语,唯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