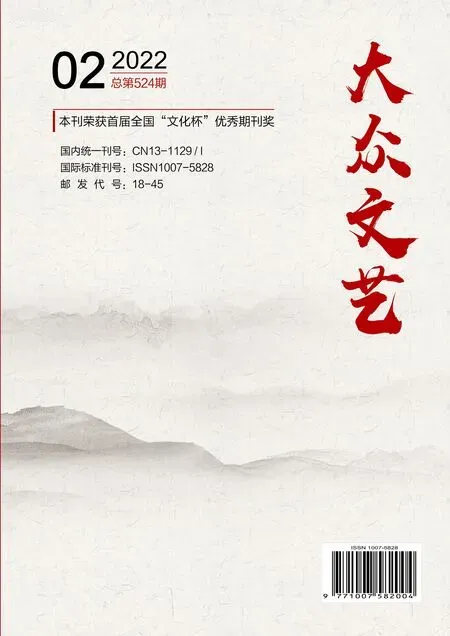何处回家路
——《风雅颂》中知识分子精神家园幻灭原因之探究
董雅珺 陈 茂 (广西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何处回家路
——《风雅颂》中知识分子精神家园幻灭原因之探究
董雅珺 陈 茂 (广西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风雅颂》是一部描写当代知识分子境遇题材的小说。故事内容主要描写以杨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当今商品经济社会中所遭遇的“排挤”与“边缘化”遭遇,被放逐与自我放逐让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家园消失殆尽。文章将从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自身软弱性两方面来分析其精神家园幻灭的原因,荒诞故事背后揭示的现实意义指引人们去关注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现实,表达了挽救文化价值的迫切性以及在后乌托邦时代建设新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望。
精神家园;知识分子;乌托邦
《风雅颂》是一部在荒诞与现实撞击下产生的小说,它血淋淋的揭露了象牙塔中种种丑恶的现象,将人们关注的视线聚焦在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身上。“知识分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但“知识分子”一词(inteligentsia)是19世纪在俄国出现,是指那些带有十分突出的反传统的批判精神的知识者。进入20世纪,知识分子的功能和价值变得更加模糊,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上出现了严重的“失位”,他们常常陷入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境,焦虑、失落、分裂的灵魂往往无处皈依,在徘徊中自我反省和质疑,在绝望中寻求救赎和坚守,小说主人公杨科就是这样一个苦苦追寻通往精神家园道路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危机共振”下的生存焦虑
中国的知识界在90年代出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分化现象,并且这种分化呈现出愈来愈严重的情绪倾向。在人文知识分子被逐出社会文化中心之后,进一步导致了“人文精神”丧失的一系列怪现象:人类价值的迷失,生存的虚无感不断制造出各类问题。终于,“启蒙”走向了“反启蒙”,使社会文化、文化、知识出现了“危机共振”的现象。这种危机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如王岳川在《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所言:“90年代以来,不少知识分子面对知识知识分子的危机,文化的迅速贬值,教育的滑坡和疲弱,知识者个体角色的尴尬失落和羸弱迷惘,希冀寻找一个“退而结网”的学术本位道路。但当语言被调侃话语和商品话语之手紧握之时,知识分子已经丧失读者和听众了。”1
小说主人公杨科即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体验着现实带来的的生存焦虑。首先,妻子赵茹萍的出轨行为给他的情感上造成了第一次打击。赵茹萍不学无术肚里空空,不惜剽窃甚至出卖自己以获得升迁,她此举说明了,现代社会关于爱情的道德理性,在功利的现实面前软弱无力。赵茹萍和李广智的道德理性在欲望、权利面前完全沦丧,只是不顾一切的追求物质、肉体上的享乐。杨科看见妻子和情人偷情的场景,尴尬万分却觉得错在自己,强烈的挫败感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他用知识分子的外衣包裹着自己可怜的尊严,此时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已面临崩溃。之后他的内心世界无时无刻不在翻腾着李副校长和他妻子媾和的场景,但却无力反抗。强权不仅剥夺了权力话语,更剥夺了一知识分子做男人的尊严,因而使这位研究诗经精神性存在根源的知识分子彻底崩溃了。
其次,象牙塔圣洁的消失殆尽给杨科带来第二次打击。当今社会,经济对文化的价值取的影响产生了偏移,从而导致文化精神的内在失和和断裂。人文知识的分子的价值已经不再是当代社会文化的中心,整个知识范式发生的变化使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视界发生错位,在物质诱惑面前,知识分子如何坚持自己的信仰,成了一道难题。杨科有这样的遭遇:“在国家的GDP上涨到百分之八时,我发表论文易如反掌,稿费单隔三差五地寄到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到GDP上涨到百分之十时,我发表的论文却是只有铅字而没有稿费了。到了GDP上涨到百分之十二那一年,再发表论文,不光不给稿费,编辑部和出版社还会倒打一耙,反过来向我所要发表和出版的经费了。”从杨科的困惑中,我们就能看出当今知识分子正面临着文化贬值的危机,且苦苦挣扎在全力与金钱中,夹缝求生存。清燕大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副高校整体堕落的荒诞图景:学校里是非混乱、价值颠倒,人性极端麻木和虚伪,完全失去了大学应有的品格。杨科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不带保留的奉献给这个他爱着的大学,却因自己的不谙世事被这个大学遗弃,他在清燕大学的失败是一个鲜明的讽刺,揭示了曾经纯净的象牙塔消失殆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权利与金钱的压迫中被摧毁。
最后,故乡的面目全非给了杨科最后一击。杨科一系列离奇的遭遇加速了他回家的脚步,故乡耙耧山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那里有日夜思念他的姑娘—玲珍。在刚回到耙耧山时,杨科的确是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尊严,在故乡人眼里杨科是京城归来的无所不能的教授,“天堂街”的小姐们也十分尊敬他。耙耧山的田园风光在今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乡村伦理中至关重要的贞洁观已经被经济实利彻底摧毁。杨科自觉肩负起重任对妓女进行改造。他试图通过情感关怀和经济支援使这些女孩回到她们原本朴素安宁的生活,但结果却是她们都已沉溺其中不愿自拔。当一群赤身裸体的少女围着杨科听课时,这一场景极大限度地讽喻了知识分子心中的精神迷梦。杨科在“天堂街”的拯救失败表明心中的故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村民得知杨科曾流连“天堂街”后,就开始对他进行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迫害,势要将杨科永远逐出前寺村。玲珍的自杀身亡使他的精神家园空空一片,他把自己的精力全放在玲珍的女儿小敏身上。他在小敏那里仿佛又感觉到了知识的希望、爱情的希望和生活的希望。可随着小敏与李木匠成婚,杨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他杀了李木匠,开始一路逃亡。耙耧山这个将杨科最初的生命旅程紧紧联系在一起土壤,集中了他的许多记忆,当他在皇城受到挫折之后,本能的想要回到这里,奢求在这能找到一些精神上的庇护,却再次被伤的体无完肤。原来的房子和家具早被村民瓜分一空,故园的淳朴之风似乎也被世俗瓦解,故乡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那个模样。
二、自我边缘化的放逐
在这样一个时代,“其中许多人学会了语言游戏和语言调侃,以自我贬损和玩世不恭来嘲弄精神价值和生存意义,在学术上处于退守姿态,在精神上处于漂流状态。另有一些人为了追求实惠而学会了取巧,放弃精神信仰和历史意识。”2但是杨科不愿意做这两种人,他深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身上所担负的重任,然而不仅是社会的发展将他排挤到边缘的地位,使他成为了一个丧失了自我话语发言的人,更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性而令他走上了一条自我放逐的路。从古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在社会的大舞台上。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形成“士”这个阶层以后,以后几千年的历史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寻求积极入世的道路,从而成为王权统治阶层的依附者。但是知识分子应该“不隶属于任何阶级”,应该葆有自由思想的权利,这样才能担当起自己的使命。正是这样的冲突与矛盾,让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当如今的商品经济的浪潮中感到痛苦与迷茫。
杨科同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一样,作为一种符号存在,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和典型性。他头顶知识分子的光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重塑精神家园。可他内心却空虚焦虑,感情、事业、人际关系一无所成,充满了无力感,他精神家园幻灭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自身性格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杨科性格上的妥协性。杨科是一个本雅明所提出的波西米亚式“文人”形象,“这类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定,与其说取决于他们的活动,不如说时常取决于偶然事件”3。当下知识分子在面对强权压迫时性格中的软弱性常常会突显出来,挣扎在这种环境下知识分子更多体验到一种无力感以及集体的漂浮感,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外界的偶然事件往往替他们做出了选择,这是时代下的典型性格。在看到妻子出轨的场面时,因软弱让他跪在了妻子和情人的面前;又因意外卷入抵抗沙尘暴的运动而被学校领导送去精神病院;当看见自己的花费了五年完成的专著《风雅之颂》被妻子窃走时,他选择了放弃为自己正名的反抗。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杨科不断地妥协,这不仅助涨了赵茹萍和李广智嚣张的气焰,也把自己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在强权面前,杨科低下了知识分子高昂的头颅,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其次,因为杨科的逃避态度,这种态度成了他行为的最好解释,然而这种逃避又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普遍行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经受着物质的压抑和权利的压迫,他们大多选择逃避。他们幻想渴望与流浪汉一样享有自由,但这是一种失去生存空间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物质对精神的压迫,使人成了物的奴仆,人与人的关系变异为物与物的关系,最终都成了卢卡奇所言“物化”的人,这是当今社会疯狂追求经济利益的恶果。虽然“物化”没有使杨科丢失信仰,他拒绝成为妻子那样被“物化”的人,然而强权对精神的“强奸”却是他无法逃避的。杨科的感情遭遇背叛,事业停滞不前,于是逃避到他的学术天地中去。他耗费了五年精力完成的专著却得不到出版,皇城里的一切好像都容不下他,于是他再次出逃,逃回故乡耙耧山。当故乡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时,他又逃避到了天堂街小姐们的温柔乡。杨科的心灵无所依靠,他性格中有着懦弱的劣根性,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杨科,由于他的逃避,造成了他既不容于现实,也找不回过去的现状。他犹如孤魂野鬼般飘零于世俗之外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他精神家园的幻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具有必然性的。
三、后乌托邦时代的理想
杨科这一路都在走,他的脚印一步步地踩在了正在变革的社会现实,踩得又狠又准。当今社会传统理性精神和理想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导致了人们精神文化上的无奈与迷惘,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无力的漂浮感。在这样一个理性、传统、文化都被自然与肉体削平,人类行为中丛林法则彰显,欲望成为人们不由自主的道德选择的社会,再提“乌托邦”,恐怕无异于白日做梦。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杨科这一路的“逃”,也是对“乌托邦”理想的苦苦追寻,他对信仰的追寻也是对精神家园的奋力守护。“退却和寻找时常交错,杨科退回故乡耙耧山前寺村,同时是寻找灵魂的避风港;杨科退到天堂街,同时是寻找天堂街里这些女人带给他的人的尊重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杨科从现实的生活退到虚幻的“诗经古城”,同时是寻找真正能让精神栖息的乌托邦。因此,杨科的退却之路同时就是找寻回家之路,也是知识分子在困境下的精神突围和自我超越之路。”4当“乌托邦”的浪漫与激情被逐渐消解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虚无意识语境下的“后乌托邦时代”,但是“乌托邦作为人类一种人类永恒的超越精神,才开始显示出它的拯救世俗的精神力量,并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5正如柏拉图设计的理想的社会模式,尽管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但它却应该比现实更加真实可信,它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一个变异的社会让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异,正常的变得不正常,而不正常却变得顺理成章。在寻找中不放弃希望,幻灭意味着重生,这恐怕是杨科这个人物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注释:
1.2.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德]本雅明.张旭东、魏文生 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上海:三联书店,1989.
4.权雅宁.退到无路可退—由《风雅颂》看知识分子的精神苦旅[J]名作欣赏,2012(3).
5.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评《湘鄂渝黔边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