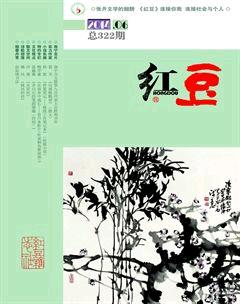秦似先生二三事(外一篇)
冯志奇,1968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南宁晚报》社、广西接力出版社工作,南宁市第五、第六届作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散文研究会副会长。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女性书画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梦魂的旋流》 《独坐书斋》及论著《新闻写作与散文》等。曾获广西首届“铜鼓奖”优秀编辑奖、广西第三届“铜鼓奖”创作奖、南宁市首届“五象工程文艺奖”。南宁市首届“德艺双馨”文艺家。
过去我在中学时读过秦似的《咏古莲》,印象比较深,很佩服他的才华,也为广西有这样的一位文学大家而感到自豪。他当时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咏古莲》,写的是报纸登载我国某地发现深藏于地下两千年前的古代莲子,发掘出来后植入泥土中,居然可以发芽成长。秦似有感于古莲生命力的强大而作。另一首是《吊屈原》,诗中既哀悼屈原的才气横溢和生不逢时,又歌颂了今天新社会的幸福生活,两首诗当时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可是不久,秦似的上述作品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说他“自比屈原”,“借古讽今,发泄他对新社会的不满,向党猖狂进攻”。后来,秦似被认为是文艺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凡是广西文艺界的批判运动,秦似被批必然首当其冲。
秦似早在抗日战争时,在桂林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任《野草》月刊主编。后任香港《文汇报》副刊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西省戏曲改革委员会主任、广西省文联副主席、广西省文化局副局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是中国文联委员、广西语文学会会长。“文革”前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后来调广西大学中文系任主任,并担任广西政协副主席直至病逝。他父亲王力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我也很喜欢其代表作之一的《汉语诗律学》,在“文革”停课时经常反复阅读。
我在广西师大中文系就读时与秦老没有什么接触,真正与秦老认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我调回南宁市,在南宁晚报社担任文艺副刊编辑工作,经常与一些作家名流接触,于是有机会认识了秦似先生。一次,我想约他写稿,但又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于是亲自到他家里去找他面谈。因为是和名人打交道,又听说他这个人有点架子,于是我便煞费苦心地想了许多见面时应该讲的客气话,想着如何小心翼翼地应对他。岂知见了面之后,没说上两句话,他便三下五除二直截了当地说:
“我明白你的来意了,说吧,要我写什么样的稿。”
我没想到他那么快人快语,一下子单刀直入,不用我开口就答应给我们写稿。于是我大喜过望,马上说:“我们想请你给我们写一组专栏的连载稿,是针砭时弊,发人深省的,好吗?”
“好!过两天你来拿稿吧!”他停了一下,又说,“不,我女儿上班离你那儿近,我叫她送给你就行了。”
啊!真没想到,不用费口舌,这次组稿就那么轻松地完成任务了。
第二天,我才上班,没想到秦似的女儿小陈就把稿子送过来了。一行题目先跳入眼帘——《未是小康居随笔》。当时的社会流行“进入小康”的提法,这“未是小康居”便有着浓浓的杂文味道了,意思是自己还未能进入小康,便会有许多不是小康的话题。果然,秦老后来不但每天按时给我们送稿,而且稿子总是切中时弊的话题,读者很喜欢看。文章一直写了30多篇,刊登后在文坛和社会上引发了较大的反响,给当时我们的晚报增色不少。
1984年,“西南剧展四十周年纪念会”在桂林召开,许多当年在抗战时期到过桂林的文艺界名人都汇聚桂林,回忆当年在桂林文化城的岁月。记得当时参会的有许多名人:欧阳山尊、金素秋、白淑湘、于是之、田海男夫妇、尹羲……我已记不得那么多了,而秦老自然是其中之一。在桂林“西南剧展四十周年纪念会”中,我见到了不少当时文艺界名流,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也是在那时,这些与会的艺术界名流也谈起过去在桂林的秦似,使我比较了解了秦老在桂林主编《野草》月刊的过去。我在会中的空隙也曾去探访过他,但来找他的昔日朋友太多了,我便知趣地让开了。在会中他还有点小插曲:由于他上了点年纪,嗜睡,在开会时总忍不住要打瞌睡。每每在发言者侃侃而谈之际,一不小心就会听到一阵酣声传来,那我们不用看就知道是秦教授正在入梦乡了。于是这件趣事成为我们在会议中的笑谈,但却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崇敬之心。
秦似在过去一直被批判,基本上没有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以后,他调到广西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还担任了广西政协副主席,好日子刚开始,却不幸患上了癌症,在他父亲王力病故后不久,即溘然长逝。
1986年,秦老病重住院。7月9日,我到医院看他时,他已不能言语,只朝我看了看,摇摇手表示致意。谁知第二天,便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心里感到很难受。他才华横溢,一世英名,却多是在被批判、被迫害中度过,中国知识分子的下场,像他这样遭遇的也的确不少!
秦似先生不论是作为作家,或诗人,或教师,他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钦佩、敬重的人物,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纪念。
与粤剧导演陈酉名的忘年交
与广东粤剧院陈酉名导演的相识有点戏剧性。想当年我刚刚10岁的时候,因为对粤剧有着浓厚的兴趣,曾经和姐姐一起到来南宁演出的广东粤剧团去报考,想将来成为一名粤剧演员。来考我们的人是广东粤剧团的导演陈酉名。结果是姐姐考上了,我却因为年龄太小而没被录取。后来姐姐也因为父亲极力反对而没有去成广东粤剧团,于是我们之间就没什么联系了,只是姐姐还和他通了一段时间的信,直到她上大学,于是姐姐常提起他。
想不到20多年后的1981年,广东粤剧院(前身是广东粤剧团)组团到南宁演出,我当时是《南宁晚报》的文艺副刊部编辑,正好到剧院来采访演女主角的广东粤剧院演员曹秀琴。采访完毕,曹秀琴送我出来,正好碰上陈导演夫妇迎面走来。于是曹秀琴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陈导演。当时我一听说是“陈导演”,就意识到:“一定是他!”
于是我很坚信,马上对他说:“您是陈酉名导演吧?”
他见我是个异地的陌生人竟叫出他的名字,感到很奇怪:“你怎么认识我?”
我笑了:“陈导演,您还记得冯志珩两姐妹吗?”我提起姐姐的名字,因为我知道姐姐当年虽然没去成广东粤剧团,却和陈酉名导演通信了好些年,他一定会记得姐姐的。
果然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哦,冯志珩,当然记得!你是……”
“我是妹妹冯志琪呀!”
“呵呵,对了,是那两姐妹!你是妹妹啊?我想起了,你那时才那么点高呢!是吗?”他作了个手势,“是了,我当年没有收留你,你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吧?”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意外的相逢,我们都格外高兴。我趁剧团还在南宁逗留几天的时间,把在广西农学院工作的姐姐找来,与陈导演夫妇相聚。故人一见,分外亲热,谈起当年,话题不少,感慨万千。
陈导演说:“幸亏当年你们没来粤剧团来,不然,哪怕你们成名,后来就是挨批斗的对象,白白浪费青春;如果不成名,跑一辈子龙套也没什么意思。可如今你们两姐妹都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都是知识分子了,那多好呀!”是的,想起来,我们也的确庆幸当年没去成广东粤剧团,不然的话,就像陈导演所说的那样,结局就很惨的了!
记得我当年曾经最喜欢唱的粤曲是红线女的经典唱曲《昭君出塞》和粤剧《搜书院》《关汉卿》里的插曲,还有罗品超、郎筠玉的《平贵别窑》等。过去我的祖母最爱听《平贵别窑》了,每每我唱时,她总是意犹未尽地叫我再唱一次,总要听过瘾为止。没想到当年扮演薛平贵的罗品超这次也来参加演出,陈导演还特意请罗品超先生来与我见面。我意想不到当年一直很敬仰的罗品超先生,听了他多年的《平贵别窑》,如今他居然笑声朗朗、英姿飒爽地站在我的眼前,我更佩服他已过古稀之年还在舞台演出,而且演的就是当年的经典节目《平贵别窑》!那天我们的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还在一起拍了照片留念。
自从南宁一见,想不到这回轮到我与陈导演通信联系了,而且有不少来往。他到南宁来肯定会找我,我到广州也肯定会去广东粤剧院探望他。这一联系,直到1998年他去世,长达将近20年时间。这是我们的不解之缘,也是我与粤剧的不解之缘吧!
想不到陈导演是一个极其热情、健谈的人,为人是特别地好,而且精力充沛,与他通信,每每是他的信比我的长十倍八倍。他是长辈,又已年过古稀,他十多年给我的信,叠起来少说也有两尺高了。这些年来,他到过南宁几次,我也到过广州几次,他每次来都会来看我,我到广州,也肯定会去探望他。有一次,他们夫妇还热情邀请我到他们家去住了两天,很热情地接待我。两老都已过了70高龄,每天还下厨为我弄吃的,煲靓汤给我喝(广东人最爱喝汤)!
我更没想到的是,与陈导演有这么多的共同爱好,如对粤剧、诗、书、画方面,都有许多可以沟通的话题。在他给我写每一封长长上千言甚至于数千言的信里,总是有滋有味地诉说艺术上的经历和看法。他的看法往往很精到,也常常引起我的共鸣,使我得到很大的收益和启发。由于接触的人有限,我对戏剧的爱好是从来没碰到什么知音的,没想到老天这样眷顾我,让我际遇陈导演之后的20多年后再次与他相逢,并一直通信。
他不但知识渊博,才思敏捷,能诗、能画、能说,他旺盛的精力,他对生活的热爱程度是惊人的!已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却还活跃在广东、港澳粤剧界,给一些剧团排戏,参加许多戏剧活动,并常常给我寄他参加活动的照片、资料。对于我来说,粤剧已在我的人生中渐渐消失了,但陈导演却乐此不彼地对我叙述粤剧界的近况,叙述他参加过广西抗战时期的“南宁战工团”的历史,不但让我懂得许多戏剧、历史方面的知识,也唤起我爱好粤曲的许多美好回忆。他的与人好善、待人热情、乐于助人的品德,在与他相交的10多年时间里,一直像一盏明灯,照耀着我,温暖着我的心田。
后来,他很有感触地对我说:“我们是忘年之交,我长你足足30多岁,但没想到我们竟这样投缘,真是相见恨晚啊!我们这么志趣相投,与你的交往使我感觉很好,真是难得!”他说话时那么自得,样子感到很满足。是的,能有这样的好师长、好朋友,也真是三生有幸!我小时很喜欢唱粤曲,能遇上这样的粤剧大家,也算是奇缘了!
我与陈导演合作过一幅作品,他画了一幅菊花,寄来给我提字。可惜我这人不会作古诗,也懒动脑筋,想来想去提不出好句,只写了几个落款字。其实,论起与陈导演的交往与友情,在他的画作上提字应该更慎重、更讲究一些的,如今想起来也真后悔。
在南宁相见时他已过古稀之年,到他去世时,已是93岁高龄了。虽然我们年龄相差较大,但我们是很难得的忘年之交。看着他留下的厚厚的一摞信,他的音容笑貌似还在眼前。我也觉得永远欠着陈酉名导演一笔无法偿还的债,为此还是感到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