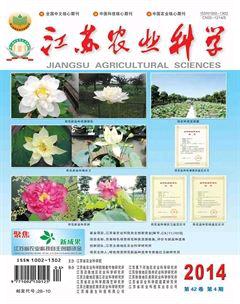科企合作模式与品种权保护利用方式
詹存钰等
摘要:分析了目前我国种子行业商业化育种的主力军仍是科研单位、企业通过与科研单位品种权交易获得种子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科企共建平台、协议约定、整体入注、兼并重组的合作模式及知识权保护利用方式。
关键词:科企合作;品种权;保护利用方式
中图分类号: F3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4-0428-03
收稿日期:2013-12-13
作者简介:詹存钰(1965—),女,江苏仪征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管理。Tel:(0514)87302275;E-mail:cyzhan@126.com。
通信作者:苏建坤(1963—),男,江苏靖江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管理。Tel:(0514)87302325;E-mail:yzsujk@163.com。2011年国务院出台“种业新政”后,种子企业纷纷与科研单位开展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也不断发生,种子公司的数量减少了20%以上,从原先的8 700多家减少到了7 000多家。2012年底,我国又出台了《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进一步明确“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从事农作物种业基础性公益研究,引导和积极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促进种子企业逐步成为商业化育种的主体”。鉴于目前我国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99%的种子企业没有研发能力,同时育种机构固步自封,育种力量各自为政,2/3的科研资源被浪费。科研人才不懂市场、商业人才不懂技术、国企人才思维模式固化、民企人才缺乏远见等是短期难以改变的现状[1]。种业新政后,大企业没有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小企业找不到突围的方向和抓手,科研单位没有能力仅凭自己的科研成果和人才优势来托起整个种子产业的发展;加上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建立,科研与市场严重脱节,体制上的弊端和产业的初级形态制约了种子产业的升级和发展等,导致我国整个种业界难以与跨国种企进行抗衡。因此,如何合理配置7 000家企业的产业资源和近千家科研单位的技术资源,这是整个种子行业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种业企业与科研单位、种业企业间如何进行合作,合作方式有哪些,合作各方的知识产权如何处理,是伴随着行业发展的另一个问题。
1我国种子行业的发展现状
1.1商业化育种的主力军仍是科研单位
1.1.1品种创新单位仍以科研单位和高校为主以江苏为例,目前全省从事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品种选育的单位共有70余个,形成了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为龙头,10个地市级农业科学研究所为主,武进、常熟等县级农业科学研究所与中江、大华等种业企业为补充的品种创新体系。其中,2000—2012年全省水稻、小麦审定的新品种中科研单位育成的均约占75%,玉米占44%以上,而企业通过审定的三大作物品种数平均不足20%。科研单位中又以地市级农业科学研究所育成的品种数占比大,其中水稻占595%,小麦占65.5%,玉米占643%。地市级农业科学研究所是江苏省育种的主力军,也是目前商业化育种中最活跃、最有优势的群体[2]。同样,2000—2012年全国科研院所通过国审的品种数量为1 391个,占比达68.5%(表1)。2012年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仍以科研院所为主。
1.1.2品种权拥有单位仍以科研单位为主从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网站上获悉,1999—2013年(截至2013年7月31日)各机构品种权拥有量中,国内科研单位拥有的品种权申请量为4 919件,占比达44.6%;品种权授权量为 2 113 件,占比达52.6%;申请量与授权量的占比均最高。
1.2企业与科研单位间的品种权交易情况
1.2.1企业获取品种权的常见方式
1.2.1.2品种权实施许可独占许可是目前我国政策规定中以“技术转让方式”可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的唯一条件,也是企业向科研单位或高校购得品种经营权的最普遍方式。如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在2004—2010年的58件品种权交易中,独占许可方式的量占总交易量的70.69%[4]。
1.2.1.3品种权作价入股品种权作价入股特别适用于科研院所与种子企业的合作。科研院所利用自己的品种权,经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与入股企业通过合约达成交易,在企业实收资本中占有一定的份额,成为企业的股东,然后按股分红。但以品种权向企业投资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以品种权投资的比例限制问题。品种权隶属于知识产权,也是一种财权,可以作价入资企业。品种权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可以作为投资的资产。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知识产权在公司注册资本中所占的比例。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中第27条“关于货币出资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30%”的规定,说明知识产权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可以达到70%。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知识产权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太高,容易造成注册资本虚假的现象。所以,企业在设立时要注意依注册企业的不同类型来确定知识产权在注册资本中的适宜比例。二是以品种权投资的权属变更与审核管理问题。知识产权不属于不动产,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动产[5],品种权也一样。以品种权进行投资牵涉到权属的变更与审核管理,这是品种权投资中一定要注意的法律问题。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规定,品种权可以转让,也可以实施许可。品种权转让行为涉及到品种权主体的变更,当转让双方自愿买卖、品种权人赠予或因企业兼并重组等原因发生品种权转移时,双方经书面合同约定,并报审批机关批准同意,受让方才能成为该品种的权利人,享有品种权赋予的相关权利,而原品种权人则失去品种权持有人的资格。品种权实施许可则不需要进行权属的变更,也不需要行政审批,由买卖双方自行约定[6]。三是以品种权投资的风险防范问题。品种权投资的风险来自于市场与评估作价上。因为品种不同于工业产品,其实际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品种的适宜种植区域有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品种容易受环境、气候、地域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再加上品种容易老化被更新替代等,这些因素造成品种权投资的风险性。同时,因为品种的特殊性,品种权在评估作价上更多的时候依赖于个人的经验,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1.2.2品种权交易价格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建立法定的品种权价值评估机构、评价体系及品种权转让的相关规定,新品种的价值无法估定,品种权转让价格只能约定俗成。当前我国种业市场品种权转让价格行情为:小麦按100万~200万元/个或0.20~0.30元/kg来收取品种权益费;国家审定杂交水稻品种500万元/个左右(高者达1 500万元/个),省级审品种(1个省审定)200万元/个左右,而父本在杂交水稻品种转让中所占比例为30%~40%,或按0.60元/kg收取品种权益费。但近2年,种子企业对品种的炒作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部分还未通过国审的品种转让价已高达1 000万元以上。
1.3企业担当商业化育种的主力军还任重道远
我国种业进入市场化时间较短,现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企业育种研发能力不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形成。
1.3.1企业的研发能力与实力欠缺多年来,我国的科研体制造成了以品种创新为主的研发资金一直依赖于国家投入,企业得到的扶持力度很小。企业在申请国家资金时处于不利地位,造成大多数种子企业不愿投资育种研发,企业纷纷以合作共享等方式加入购买品种的行列,导致企业研发能力不强。李军民等发现,现阶段农作物育种研究有“3个80%”现象,即80%以上的种质资源和育种人员集中在科研和教学单位,80%以上的农作物品种来源于科研和教学单位选育,80%以上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应用技术研究即商业化育种研究中[7]。
据调查,江苏省从事农作物育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约300多名,75%的专家集中在科研院所与高校,其中54.5%的人员拥有研究生学历,而企业只有21%的专家,其中只有295%的人员拥有研究生学历。全省145名从事稻麦玉育种的专家以45~53岁的为主,占57.4%;其次是40~43岁的,占22.0%。而企业的育种专家年龄集中在45岁左右、65岁以上2个层次。
鉴于企业是利益拥趸者,在现行体制下对品种培育这样一件难以立竿见影的事情,企业既不想投入资金进行研发,也没有研发队伍与育种资源,于是众多的种子企业要么与科研单位合作,要么从科研单位购买品种,要么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品种。所以,企业担当商业化育种大军还欠缺实力。
1.3.2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据学者统计,我国种业每年全行业技术创新投入资金约为25亿元,约占产业市场总数的4%。2011年,我国91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仅为4%,前10位种子企业研发投入共计才5亿元,仅占销售收入的5.5%。
2科企合作模式及知识权保护利用方式
“种业新政”已经明确,到“十二五”末,科研院所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基本实现脱钩。由于目前科研机构仍占育种创新能力的主导地位,国内种子企业竞争能力弱。在此背景下,建立科研机构与企业互补性技术创新联盟,共同开发利用育种科技资源,是科研机构逐步脱离商业化育种,推进企业主导整个种子产业的必经过渡阶段。在科企合作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利用方式将是推进整个合作的关键所在。
2.1共建平台
鉴于我国种子科研涉及的遗传材料、人才和投入等科技创新资源,约80%集中在科研机构。因此,“N(企业)+ 1(科研单位)”将是近一个阶段内科企合作的常规模式。种子企业与公益性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协同创建种质资源鉴定与创新平台、生物技术育种研发与应用平台、品种联合测试平台等,通过共担投入、共享成果,推进种业技术创新。
2011年,国家在推出“种业新政”的同时,同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即在5年内,科研单位将被按照公益、非公益进行分类。分类后,公益性涉农科研机构将承担种业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而与品种培育等相关的商业化研发则向种子企业转移。同时,国家还启动了“十二五”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等系列重大专项,以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为代表的生物育种产业发展,以及常规作物育种和无性繁殖材料选育等是未来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发展方向。国内有雄厚基础研究实力的公益性科研机构在专注于基因等生物资源性材料的研究,利用分子育种技术来开展常规育种和基因筛选的同时,注重以专利或商标的方式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在此背景下,科研机构还应结合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适时分析掌握国外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专利状况,增强科研育种项目方向与产业紧密度,培育具有局域特色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权利集群[8]。
共建的平台中将涉及多层次知识产权主体,各层次主体间的合作有利于推动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保护与综合利用,从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2.2协议约定
对于我国庞大数量的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偏向于杂交育种和生物技术育种的应用,具备较强的应用性研究能力,有丰硕的育种资源与良好的育种基础。应发挥相应优势,专注于中间材料的培育,如玉米、水稻不育系的培育等,这些材料可以通过专利、品种权、技术秘密来加以保护。
在商业化育种进程中,种子企业与这一类的科研单位之间,既可以通过签署具体品种的委托育种协议,由企业提供育种经费,科研单位进行品种选育,双方约定共享育成品种收益;也可以通过购买或合作取得相应品种的市场开发经营权利,然后通过配组加工进行品种生产,并推广应用。
2.3整体入注
长期以来的体制造成我国许多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都有自办的种子公司,“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是这类企业的常规现象。这类企业依赖于自身的科研单位与科研成果,生意也做得顺风顺水,小有成就。鉴于种业新政以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于2015年底前要完成事企分开、商业化育种剥离。因此,对这类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不妨转变观点,突破体制,破除原先的框架,使科研单位凤凰涅槃,彻底改制转身成为企业的研发部门,走企业化育种之路。
科研单位原先拥有的知识产权,经评估后与其他资产、人员一并进入企业,因为有长期积累的科研基础及技术、人才、销售网络等优势,并主动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合,构建种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品种大面积生产后续利用开辟了稳定通道。同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治理公司,理顺成果转化途径,不仅注重科技创新,更要重视成果应用与生产上的服务指导,及时反馈市场信息,走国际化大公司发展之路[9]。
2.4兼并重组
对于没有研发能力的小型种子企业,因为在地域上具有优势地位,可以加盟大公司,专做大公司的销售公司,成为销售网络中的一员。对于有研发能力的小型种子企业,可以携品种进入大型种子企业,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品种权益的分成方式与比例来共同收益;也可以接受大型种子企业的资本注入,成为其分公司或子公司。
参考文献:
[1]刘石. 2013年种业展望与猜想[EB/OL]. (2013-01-31)[2013-09-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3c6ad90102e4hc.html.
[2]许学宏. 江苏农作物品种创新现状与机制改革路径[J]. 江苏农村经济,2013(8):65-67.
[3]李军民,唐浩,宋维平.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中的制约因素及改进建议[J]. 种子世界,2012(12):8-9.
[4]张初贤,吴魁,顾巍巍,等. 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探索与思考——基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7年的实践[J]. 江苏农业科学,2011,39(3):593-595.
[5]孙春伟. 以知识产权向企业投资的问题与对策[J]. 科技管理研究,2012,32(20):190-193.
[6]詹存钰,叶浩. 植物新品种权权利运作模式探析[J]. 农业科技管理,2013,32(3):42-45.
[7]李军民,宋维平,吴家全. 构建种业科技成果托管平台提高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率[J]. 农业科技管理,2013,32(4):59-62.
[8]杜琼. 公益类科研机构农业知识产权战略与种业科技竞争力提升[J]. 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12(3):19-22.
[9]詹存钰,叶浩. 种业新政下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的出路[J]. 中国种业,2012(12):9-10.
1.2.2品种权交易价格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建立法定的品种权价值评估机构、评价体系及品种权转让的相关规定,新品种的价值无法估定,品种权转让价格只能约定俗成。当前我国种业市场品种权转让价格行情为:小麦按100万~200万元/个或0.20~0.30元/kg来收取品种权益费;国家审定杂交水稻品种500万元/个左右(高者达1 500万元/个),省级审品种(1个省审定)200万元/个左右,而父本在杂交水稻品种转让中所占比例为30%~40%,或按0.60元/kg收取品种权益费。但近2年,种子企业对品种的炒作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部分还未通过国审的品种转让价已高达1 000万元以上。
1.3企业担当商业化育种的主力军还任重道远
我国种业进入市场化时间较短,现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企业育种研发能力不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形成。
1.3.1企业的研发能力与实力欠缺多年来,我国的科研体制造成了以品种创新为主的研发资金一直依赖于国家投入,企业得到的扶持力度很小。企业在申请国家资金时处于不利地位,造成大多数种子企业不愿投资育种研发,企业纷纷以合作共享等方式加入购买品种的行列,导致企业研发能力不强。李军民等发现,现阶段农作物育种研究有“3个80%”现象,即80%以上的种质资源和育种人员集中在科研和教学单位,80%以上的农作物品种来源于科研和教学单位选育,80%以上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应用技术研究即商业化育种研究中[7]。
据调查,江苏省从事农作物育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约300多名,75%的专家集中在科研院所与高校,其中54.5%的人员拥有研究生学历,而企业只有21%的专家,其中只有295%的人员拥有研究生学历。全省145名从事稻麦玉育种的专家以45~53岁的为主,占57.4%;其次是40~43岁的,占22.0%。而企业的育种专家年龄集中在45岁左右、65岁以上2个层次。
鉴于企业是利益拥趸者,在现行体制下对品种培育这样一件难以立竿见影的事情,企业既不想投入资金进行研发,也没有研发队伍与育种资源,于是众多的种子企业要么与科研单位合作,要么从科研单位购买品种,要么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品种。所以,企业担当商业化育种大军还欠缺实力。
1.3.2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据学者统计,我国种业每年全行业技术创新投入资金约为25亿元,约占产业市场总数的4%。2011年,我国91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仅为4%,前10位种子企业研发投入共计才5亿元,仅占销售收入的5.5%。
2科企合作模式及知识权保护利用方式
“种业新政”已经明确,到“十二五”末,科研院所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基本实现脱钩。由于目前科研机构仍占育种创新能力的主导地位,国内种子企业竞争能力弱。在此背景下,建立科研机构与企业互补性技术创新联盟,共同开发利用育种科技资源,是科研机构逐步脱离商业化育种,推进企业主导整个种子产业的必经过渡阶段。在科企合作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利用方式将是推进整个合作的关键所在。
2.1共建平台
鉴于我国种子科研涉及的遗传材料、人才和投入等科技创新资源,约80%集中在科研机构。因此,“N(企业)+ 1(科研单位)”将是近一个阶段内科企合作的常规模式。种子企业与公益性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协同创建种质资源鉴定与创新平台、生物技术育种研发与应用平台、品种联合测试平台等,通过共担投入、共享成果,推进种业技术创新。
2011年,国家在推出“种业新政”的同时,同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即在5年内,科研单位将被按照公益、非公益进行分类。分类后,公益性涉农科研机构将承担种业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而与品种培育等相关的商业化研发则向种子企业转移。同时,国家还启动了“十二五”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等系列重大专项,以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为代表的生物育种产业发展,以及常规作物育种和无性繁殖材料选育等是未来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发展方向。国内有雄厚基础研究实力的公益性科研机构在专注于基因等生物资源性材料的研究,利用分子育种技术来开展常规育种和基因筛选的同时,注重以专利或商标的方式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在此背景下,科研机构还应结合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适时分析掌握国外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专利状况,增强科研育种项目方向与产业紧密度,培育具有局域特色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权利集群[8]。
共建的平台中将涉及多层次知识产权主体,各层次主体间的合作有利于推动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保护与综合利用,从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2.2协议约定
对于我国庞大数量的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偏向于杂交育种和生物技术育种的应用,具备较强的应用性研究能力,有丰硕的育种资源与良好的育种基础。应发挥相应优势,专注于中间材料的培育,如玉米、水稻不育系的培育等,这些材料可以通过专利、品种权、技术秘密来加以保护。
在商业化育种进程中,种子企业与这一类的科研单位之间,既可以通过签署具体品种的委托育种协议,由企业提供育种经费,科研单位进行品种选育,双方约定共享育成品种收益;也可以通过购买或合作取得相应品种的市场开发经营权利,然后通过配组加工进行品种生产,并推广应用。
2.3整体入注
长期以来的体制造成我国许多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都有自办的种子公司,“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是这类企业的常规现象。这类企业依赖于自身的科研单位与科研成果,生意也做得顺风顺水,小有成就。鉴于种业新政以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于2015年底前要完成事企分开、商业化育种剥离。因此,对这类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不妨转变观点,突破体制,破除原先的框架,使科研单位凤凰涅槃,彻底改制转身成为企业的研发部门,走企业化育种之路。
科研单位原先拥有的知识产权,经评估后与其他资产、人员一并进入企业,因为有长期积累的科研基础及技术、人才、销售网络等优势,并主动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合,构建种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品种大面积生产后续利用开辟了稳定通道。同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治理公司,理顺成果转化途径,不仅注重科技创新,更要重视成果应用与生产上的服务指导,及时反馈市场信息,走国际化大公司发展之路[9]。
2.4兼并重组
对于没有研发能力的小型种子企业,因为在地域上具有优势地位,可以加盟大公司,专做大公司的销售公司,成为销售网络中的一员。对于有研发能力的小型种子企业,可以携品种进入大型种子企业,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品种权益的分成方式与比例来共同收益;也可以接受大型种子企业的资本注入,成为其分公司或子公司。
参考文献:
[1]刘石. 2013年种业展望与猜想[EB/OL]. (2013-01-31)[2013-09-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3c6ad90102e4hc.html.
[2]许学宏. 江苏农作物品种创新现状与机制改革路径[J]. 江苏农村经济,2013(8):65-67.
[3]李军民,唐浩,宋维平.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中的制约因素及改进建议[J]. 种子世界,2012(12):8-9.
[4]张初贤,吴魁,顾巍巍,等. 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探索与思考——基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7年的实践[J]. 江苏农业科学,2011,39(3):593-595.
[5]孙春伟. 以知识产权向企业投资的问题与对策[J]. 科技管理研究,2012,32(20):190-193.
[6]詹存钰,叶浩. 植物新品种权权利运作模式探析[J]. 农业科技管理,2013,32(3):42-45.
[7]李军民,宋维平,吴家全. 构建种业科技成果托管平台提高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率[J]. 农业科技管理,2013,32(4):59-62.
[8]杜琼. 公益类科研机构农业知识产权战略与种业科技竞争力提升[J]. 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12(3):19-22.
[9]詹存钰,叶浩. 种业新政下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的出路[J]. 中国种业,2012(12):9-10.
1.2.2品种权交易价格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建立法定的品种权价值评估机构、评价体系及品种权转让的相关规定,新品种的价值无法估定,品种权转让价格只能约定俗成。当前我国种业市场品种权转让价格行情为:小麦按100万~200万元/个或0.20~0.30元/kg来收取品种权益费;国家审定杂交水稻品种500万元/个左右(高者达1 500万元/个),省级审品种(1个省审定)200万元/个左右,而父本在杂交水稻品种转让中所占比例为30%~40%,或按0.60元/kg收取品种权益费。但近2年,种子企业对品种的炒作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部分还未通过国审的品种转让价已高达1 000万元以上。
1.3企业担当商业化育种的主力军还任重道远
我国种业进入市场化时间较短,现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企业育种研发能力不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形成。
1.3.1企业的研发能力与实力欠缺多年来,我国的科研体制造成了以品种创新为主的研发资金一直依赖于国家投入,企业得到的扶持力度很小。企业在申请国家资金时处于不利地位,造成大多数种子企业不愿投资育种研发,企业纷纷以合作共享等方式加入购买品种的行列,导致企业研发能力不强。李军民等发现,现阶段农作物育种研究有“3个80%”现象,即80%以上的种质资源和育种人员集中在科研和教学单位,80%以上的农作物品种来源于科研和教学单位选育,80%以上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应用技术研究即商业化育种研究中[7]。
据调查,江苏省从事农作物育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约300多名,75%的专家集中在科研院所与高校,其中54.5%的人员拥有研究生学历,而企业只有21%的专家,其中只有295%的人员拥有研究生学历。全省145名从事稻麦玉育种的专家以45~53岁的为主,占57.4%;其次是40~43岁的,占22.0%。而企业的育种专家年龄集中在45岁左右、65岁以上2个层次。
鉴于企业是利益拥趸者,在现行体制下对品种培育这样一件难以立竿见影的事情,企业既不想投入资金进行研发,也没有研发队伍与育种资源,于是众多的种子企业要么与科研单位合作,要么从科研单位购买品种,要么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品种。所以,企业担当商业化育种大军还欠缺实力。
1.3.2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据学者统计,我国种业每年全行业技术创新投入资金约为25亿元,约占产业市场总数的4%。2011年,我国91家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仅为4%,前10位种子企业研发投入共计才5亿元,仅占销售收入的5.5%。
2科企合作模式及知识权保护利用方式
“种业新政”已经明确,到“十二五”末,科研院所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基本实现脱钩。由于目前科研机构仍占育种创新能力的主导地位,国内种子企业竞争能力弱。在此背景下,建立科研机构与企业互补性技术创新联盟,共同开发利用育种科技资源,是科研机构逐步脱离商业化育种,推进企业主导整个种子产业的必经过渡阶段。在科企合作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利用方式将是推进整个合作的关键所在。
2.1共建平台
鉴于我国种子科研涉及的遗传材料、人才和投入等科技创新资源,约80%集中在科研机构。因此,“N(企业)+ 1(科研单位)”将是近一个阶段内科企合作的常规模式。种子企业与公益性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协同创建种质资源鉴定与创新平台、生物技术育种研发与应用平台、品种联合测试平台等,通过共担投入、共享成果,推进种业技术创新。
2011年,国家在推出“种业新政”的同时,同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即在5年内,科研单位将被按照公益、非公益进行分类。分类后,公益性涉农科研机构将承担种业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而与品种培育等相关的商业化研发则向种子企业转移。同时,国家还启动了“十二五”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等系列重大专项,以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为代表的生物育种产业发展,以及常规作物育种和无性繁殖材料选育等是未来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发展方向。国内有雄厚基础研究实力的公益性科研机构在专注于基因等生物资源性材料的研究,利用分子育种技术来开展常规育种和基因筛选的同时,注重以专利或商标的方式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在此背景下,科研机构还应结合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适时分析掌握国外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专利状况,增强科研育种项目方向与产业紧密度,培育具有局域特色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权利集群[8]。
共建的平台中将涉及多层次知识产权主体,各层次主体间的合作有利于推动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保护与综合利用,从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2.2协议约定
对于我国庞大数量的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偏向于杂交育种和生物技术育种的应用,具备较强的应用性研究能力,有丰硕的育种资源与良好的育种基础。应发挥相应优势,专注于中间材料的培育,如玉米、水稻不育系的培育等,这些材料可以通过专利、品种权、技术秘密来加以保护。
在商业化育种进程中,种子企业与这一类的科研单位之间,既可以通过签署具体品种的委托育种协议,由企业提供育种经费,科研单位进行品种选育,双方约定共享育成品种收益;也可以通过购买或合作取得相应品种的市场开发经营权利,然后通过配组加工进行品种生产,并推广应用。
2.3整体入注
长期以来的体制造成我国许多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都有自办的种子公司,“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是这类企业的常规现象。这类企业依赖于自身的科研单位与科研成果,生意也做得顺风顺水,小有成就。鉴于种业新政以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于2015年底前要完成事企分开、商业化育种剥离。因此,对这类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不妨转变观点,突破体制,破除原先的框架,使科研单位凤凰涅槃,彻底改制转身成为企业的研发部门,走企业化育种之路。
科研单位原先拥有的知识产权,经评估后与其他资产、人员一并进入企业,因为有长期积累的科研基础及技术、人才、销售网络等优势,并主动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合,构建种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品种大面积生产后续利用开辟了稳定通道。同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治理公司,理顺成果转化途径,不仅注重科技创新,更要重视成果应用与生产上的服务指导,及时反馈市场信息,走国际化大公司发展之路[9]。
2.4兼并重组
对于没有研发能力的小型种子企业,因为在地域上具有优势地位,可以加盟大公司,专做大公司的销售公司,成为销售网络中的一员。对于有研发能力的小型种子企业,可以携品种进入大型种子企业,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品种权益的分成方式与比例来共同收益;也可以接受大型种子企业的资本注入,成为其分公司或子公司。
参考文献:
[1]刘石. 2013年种业展望与猜想[EB/OL]. (2013-01-31)[2013-09-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3c6ad90102e4hc.html.
[2]许学宏. 江苏农作物品种创新现状与机制改革路径[J]. 江苏农村经济,2013(8):65-67.
[3]李军民,唐浩,宋维平.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中的制约因素及改进建议[J]. 种子世界,2012(12):8-9.
[4]张初贤,吴魁,顾巍巍,等. 植物品种权交易实施的探索与思考——基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7年的实践[J]. 江苏农业科学,2011,39(3):593-595.
[5]孙春伟. 以知识产权向企业投资的问题与对策[J]. 科技管理研究,2012,32(20):190-193.
[6]詹存钰,叶浩. 植物新品种权权利运作模式探析[J]. 农业科技管理,2013,32(3):42-45.
[7]李军民,宋维平,吴家全. 构建种业科技成果托管平台提高种业科技成果转化率[J]. 农业科技管理,2013,32(4):59-62.
[8]杜琼. 公益类科研机构农业知识产权战略与种业科技竞争力提升[J]. 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12(3):19-22.
[9]詹存钰,叶浩. 种业新政下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的出路[J]. 中国种业,2012(12):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