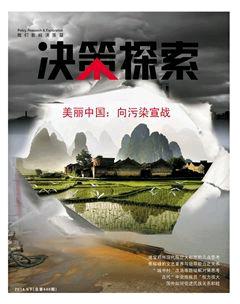大学该为女性就业公平做什么
王可
人们通常认为,像从哈佛这样的“名门”跨出来的佼佼者,会从母校的品牌认同度、准入高薪行业和知名雇主的便利性,以及“私人定制”式的求职与职业咨询中受益匪浅。倘若教育真像人们所宣称的,是“促进公平的利器”,那么,接受同样的精英教育的人士之间便不应该存在差异:不管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如何,生源地在哪,由什么样的文化哺育长大,性别如何,一旦你戴着学位帽迈出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高校的大门,便都能在就业市场上获得同样的“结局”,对吗?
《哈佛深红报》对已签约的大四学生的一项非正式调查显示,2013届哈佛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始年薪约为6万美元,显著高于美国同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起始年薪——45327美元。这个笼统的调查数据容易让人忽视一个问题:在444位被调查者中,56%为女性,但女性在最高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却小得多。
在年薪最高(即高于11万美元)的本科毕业生中,有3/4为男性;下一收入梯次(即9万~11万美元)里,则有约2/3为男性。从事金融业的哈佛男性本科毕业生年薪超过11万美元的可能性,几乎是女性本科毕业生的4倍,年薪在9万~11万美元的可能性是女性本科毕业生的3倍。在工程和技术业领域,79%的男性以及仅仅44%的女性年薪高于9万美元。
当然,这个调查是由哈佛校报而非专业测评机构发起,且其职业部分的样本量只有444个——只占应届生总数的1/4。但鉴于参与该调查的多数是女性,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不知道有多少研究已经揭示,在美国大多数行业里,女性的收入显著低于做同样工作的男性;虽然女性本科毕业生的数量多于男性本科毕业生,本科以上学历的女性数量更是远胜同等学历的男性。
即便是那些有更多女性在毕业时倾向就业的行业,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一半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都是男人;仅18%的医院首席执行官是女人;根据妇女传媒中心发布的《2013美国传媒业妇女状况报告》,在印刷、数码、广播和其他媒体中,女性持续并且显著地在领导职位及权力上落后于男性。那些被如今精英大学男性毕业生所偏爱的行业(咨询、金融、技术),其中领导岗位上存在的性别鸿沟更加让人“伤不起”。彭博社评选的50位全球金融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里,只有5位是女性。美国顶尖的10家管理咨询公司中,没有一位女性总裁。至于科技公司,咱们都没必要去数了,你懂的。
为什么在高等教育的最顶层,女性的毕业后起始薪资仍然低于男性?
调查表明,男性选择工作时,并不一定要符合他们个人的兴趣,而是要能赚更多钱、更具声望。反之,更多女性也许会抓住当下,立即追求她们心中所想。这样的假设合理吗?是否男人身负供养家庭的社会期望,因而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之前,先得建设“小金库”?是否女人在收入稳定性上所遭遇的社会压力比男人小,因此会被她们喜欢但薪酬较低的行业所吸引?是否女人会被平衡未来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的潜在压力牵制,因此选择了那些有着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和更小压力的行业,譬如教育?这便是被雪莉·桑德伯格(Facebook首席运营官,哈佛大学毕业生)描述为“甚至在选择加入之前便已选择退出”的一种现象——换言之,一个女人还没开始一展职业宏图,她就已经被未来事业与家庭的角力带来的挑战吓退了。
如你所见,哪怕是哈佛,女性也面临双重的挑战:行业选择的性别差异,以及行业内的性别歧视。看来,教育真不是我们以为的,是促进公平的“伟大均衡器”。一个教育机构是否应当致力于防止在职场中产生性别不平等?或者,还是把这个问题留待雇主解决更好?
在笔者看来,为不同性别的人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大学和雇主双方发挥重要作用。雇主有能力和力量去制定职场上支持女性的规则与框架,尤其是当她们建立家庭时。不过,有权力制定这些框架的人,需要好好学习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生理的和社会的。这就是教育机构能发挥重大影响的地方了。在大学,要鼓励女性将更多行业纳入考虑范围。她们应得到更多来自校方的支持,并且被鼓励互为“后援团”去追求事业机会。男性则应接受关于女性在职场中所面临的重重挑战的教育,以便他们某天身居高位后,能够更好地理解并努力解决那些困难。应该让他们意识到,“妇女能顶半边天”。
假使我们将教育看作投资,那么,在哈佛接受教育的4年里要花费23万美元以上(不包括助学金),学校收钱时可没管你是男是女。如果女性的职业“钱”景因性别歧视注定走低,对学生总体中占到更大比例的这个群体来说,投资的回报便不那么合算了。
于大学而言,花力气去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因为一所大学若将为青年步入社会、成为有责任和有生产力的公民作准备,以及把为世界未来培养领袖作为目标的话,为社会半数人口确保一个公平的未来就是非常关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