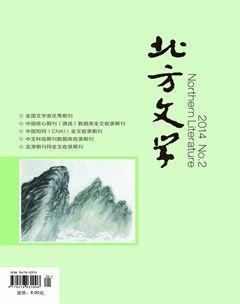丹•布朗小说中伦理困境研究
摘 要:丹•布朗典型的创作模式是将严肃文学主题寓于通俗文学形式之中。布朗以后现代伦理环境为其创作的背景板,将两类通俗文学元素融入其中,着力描绘当下人们的伦理困境。在处理科幻元素时,他模糊善与恶的界限,将善始未能善终的科技伦理困境呈现出来;而在重构历史元素时,他则将信仰与真理联系在一起,认为小写的复数真理引发当下人们两难的信仰困境。开放式结尾表明,布朗意在刺激读者在享受阅读狂欢之余,反思自身的伦理境况。
关键词:后现代伦理;丹•布朗小说;科技;信仰
美国文学史上,“严肃文学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家常常互相学习,彼此借鉴”[1]。坡、吐温及福克纳等一大批经典文学大师都曾有意识地采用通俗文学的表现方法来增强作品的叙事力度,以达到预期的美学效果。在当下多元文化时代,这种创作倾向更是受到众多作家推崇,丹•布朗便是其中之一。他灵活整合多种后现代创作手法,糅合科幻、悬疑、惊悚等通俗小说元素,又自觉地将“一些关乎人类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2]融入创作之中,从而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纵观其十多年的创作生涯,科幻小说与历史小说这两种通俗文学形式深受布朗青睐。迄今为止,布朗六部作品中就有五部直接探讨科技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而历史元素的重构则经常穿插其中,并在其成名作《达•芬奇密码》中大放光彩。这两类通俗文学形式分别对应后现代伦理环境下的两种困境——科技与信仰的困境。布朗将严肃的伦理主题融入通俗形式之中,意在使读者在享受阅读狂欢之余,能自觉反思自身的伦理处境,进而寻得一种适合自己的后现代伦理生活方式。
一、布朗的后现代伦理情怀与文学想象
隐形权力和阴谋的挖掘与揭露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代名词,但他想要传达的远不止如此。《失落的秘符》开篇之中,布朗就借“自己的影子”兰登之口直抒胸臆:“丑闻并非我的意图所在”[3]。与同时代的畅销书作家J.K.罗琳、斯蒂芬•金的作品相比,布朗的文化悬疑小说更侧重于“关心着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生活现状”[4]。由于“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5],那么,对后工业时代人们伦理境况的考量自然成为他所要表达的“意图”之一。可以说,在其每部小说惊险刺激的冒险经历背后,都暗涌着布朗对当下伦理问题,尤其是后现代伦理困境的反思。
在布朗的小说中,我们找不到一种“建立在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原则上的伦理和审美体系”[6],这种消解二元对立的创作手法正是后现代伦理学家所提倡的。齐格蒙特•鲍曼曾言,后现代伦理学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摒弃现代的道德关怀,而是“拒绝从事道德问题研究的传统的现代方法”[7]。现代典型的思维方式就是二元对立的,其特点在于将一切事物置于对立与冲突之中。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这种继承与发展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认识方式遭到了人们质疑。在伦理学方面,人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现象都可以用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去理解。由于道德现象“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8],它就不能简单地以正确或不正确,及真或假等二元对立的方式去认知。二元对立模式的消解意味着人们的道德行为不能再定位为善与恶、真与假等两极中的一个,而只能属于这种两极中间的灰色地带。这样,伦理学意义上看,后现代时期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道德模糊的时代。人们在这种模糊的伦理环境下,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同时也被抛进一个不确定的困惑状态之中。
布朗将当下人们自由与困惑并置的伦理境遇融入小说之中,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受其家庭环境长期熏陶而成。他的父亲是名获得美国总统奖的数学教授,母亲则是位深爱宗教音乐的艺术家,“其他人看来水火不容的两大学科——科学与宗教,在他家中和谐共处,甚至彼此依赖、相互共生”[9]。独特的家庭背景使布朗从小就对二元对立的认知方式有了新的看法。在谈到《天使与魔鬼》的创作动机时,布朗说到:“在许多方面我都将科学和宗教视为同一事物……他们就像是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10]。他这种旨在破除二元对立结构的创作理念,也贯穿于其他几部小说之中。依据整合通俗文学元素的侧重点不同,可将布朗的小说粗略分为两类——指涉未来的科幻小说与以史寓今的历史小说,分别消解善与恶、真与假的恒定性,从而将当下人们在科技使用和信仰上的伦理困境展示出来。
二、科技伦理困境:善与恶边界的消融
20世纪下半叶以降,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法比拟的影响,使人类面临着与以往时代不同的伦理处境。科技发明的本意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但在使用过程中却意外地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威尔斯、赫胥黎及冯内古特等当代作家都将科技的双重影响引入小说创作之中,“关注科技发展对传统道德的冲击以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的伦理命题,思考科技原则与道德原则的关系,试图解决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11]。尽管同样借助科幻小说形式并本着相似的人文关怀,但布朗的创作显然不同于先辈作家的尝试。在其五部涉及科技发明的作品中,布朗未将科技置于善与恶对弈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将涉及科技应用的伦理冲突设定为善与善的对峙。
这种对峙在《数字城堡》尤为突出。小说中,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使用万能解密机都有其善的初衷。万能解密机的发明解决了国安局在网络时代的工作困境,使原本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破解的邮件,在几分钟之内就能破解。它提升了国安局的工作效率,有效地帮助美国政府挫败几十起恐怖袭击活动。因而,万能解密机的发明与使用有其善的初衷——维护国家和个人安全,尽管它的使用也侵害了不少电脑用户的合法权利。面对国安局在虚拟世界的霸权行为,全球电脑用户自发成立电新会,旨在“支持在线言论自由,让人们了解生活在电子世界里的现实问题及危险因素”[12]。“飞鱼”丑闻曝光后,电新会认为国安局“在所有算法里都安上了后门”[13],以便让其可以自由翻阅每一封电子邮件。他们更称国安局为“自希特勒以来对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14],并开始监视其一举一动,企图阻止国安局在网络世界里肆意横行。他们反对“政府机构的奥威尔窃听能力”[15]也是源于维护个人隐私权的善意初衷。因而,这场关于是否使用万能解密机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善与善的对峙。从处女作《数字城堡》到新作《炼狱》,这种善与善的冲突大量存在于布朗小说之中,且可视为其特色之一。《骗局》中的政治谎言与个人诚信问题、《天使与魔鬼》中科技与宗教之争,及《地狱》中的杀人与救人问题,这些看似对立的伦理元素的背后都潜藏着善与善的对峙。矛盾的双方在对科技的使用上都有着善的初衷,但在后现代伦理环境下,这种善却很难被实现。
后现代伦理发轫于对现代伦理宏大叙事合法性的质疑中。因而,质疑成了人们后现代伦理境况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对任何宣布为绝对可靠的东西都表示怀疑”[16]。布朗明显觉察到此种怀疑基调,并将之置于文学想象之中。兰登系列小说的主角——罗伯特•兰登,布朗称为“自己的影子”,其身上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敢于质疑一切文化、宗教和历史上的权威观点。《数字城堡》中的质疑不仅存在于国家对个人追求自由权利的质疑,也体现在个人对国家权威话语的质疑。这种双重质疑不仅让各自的善意在执行中受阻,更使得善的另一面——恶被展现出来。在万能解密机的使用权限上,国安局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以副局长为首,认为国安局可以随意使用万能解密机;另一种则以远诚友加为主,认为使用万能解密机必须受限。两种声音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国安局以维护国家及个人安全为己任,但在其执法过程中,采取一种精英分子的立场。他们蔑视大众,甚至怀疑大众是否有能力甄别善恶好坏的能力。国安局首席密码破译员苏珊就认为:“政府有权收集对人民构成威胁的信息”[17],必要时完全应该“可以随时随地对任何人进行监视”[18]。她这样认为的理由是“网络里有很多好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掺杂其中。必须要有人接近所有东西,分辨好坏。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19]。苏珊以大众的监管人自居,而副局长则将大众推到国家的对立面,认为“我们面对过我从未想过会像我们发起挑战的敌人。我说的是我们自己的公民”[20]。究其原因,他总结道:“他们失去了信仰。他们变得多疑起来”,认为“公众需要有人监视他们”[21],并且“将他们从无知中拯救出来是我们的责任”[22]。这种精英分子立场就使副局长等人在处理国家和大众的关系时,将自己视为英雄而将大众视为无知的大多数,并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并有益于国家和人民。正是这种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让国安局的善意初衷在实际运作中受阻,最终以失败告终。
endprint
相较于精英分子立场,远诚友加的亲民立场则体现了个人对国家权威话语的质疑。作为万能解密机的设计者之一,友加赞同国安局有这样一台可以破解任何邮件或程序的机器,但反对国安局“可以阅读任何人的邮件然后再人不知鬼不觉地将之封上了事”[23]。与苏珊不同,他对副局长那套“为了国家安全”的权威说辞持质疑态度,称“这种做法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24]。友加的质疑和其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二战中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受害者,友加深知,不论有多么高尚的出发点,科技的使用必须有一定的管制,否则结果将不堪设想。因而,他极力反对国安局无限制地使用万能解密机。他的那句“谁来监视这些监视者”是对权威不信任的最佳阐释。正因如此,他决心发明“数字城堡”程序,迫使国安局承认万能解密机的存在,最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种对技术与权力相结合的焦虑在布朗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个人质疑乃至反抗权力机构善意的重要缘由之一。《地狱》中,支持使用生化药品的西恩纳就直接道出了这种焦虑,她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于科学发明有着重大影响的技术总是被当权者当做武器使用”[25]。
《数字城堡》中,由监视带来的自由与安全之争“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个技术问题”[26],但无论国家还是个人或民间组织都只将它视为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因此,冲突解决的主要途径是依靠技术革新,即以一方先进技术压倒另一方相对落伍的技术。当大众得知国安局可以拦截他们的邮件时,公钥加密法被发明。随后,国安局的“飞鱼”计划应运而生。在其被揭发后,万能解密机诞生了。为了对付它,友加发明了“数字城堡”。最后,国安局打算收编“数字城堡”。以此发展下去,这场冲突将演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此消彼长的技术竞赛,最后只会陷入技术决定论,这可能导致两种极端后果——网络世界将成为一个全景式监狱或无政府主义王国。无论这场冲突以哪种结果收尾,都背离了科技发明的善的初衷,给整个人类带来有害无益的影响。
有别于阿西莫夫和克拉克等经典科幻小说家天马行空的幻想,布朗小说中的科幻元素更具当下性。在现有科技稍加发挥想象的基础上,他有意模糊善与恶之间界线,将人类在道德上善恶并存的状态通过伦理冲突呈现出来。此种冲突起源于善,但在相互质疑中濒临破产,甚至有滑向恶的可能。
三、信仰的两难:“真”的多样化追求
当下人们的信仰问题是布朗小说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传统意义上,“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宗教事件”[27],因此,西方社会信仰危机大多表现为对上帝信仰的衰退或缺失。然而,布朗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科技信仰,在其本质上可以视为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他曾多次在小说中表明这一观点:“信仰是普遍的……随意的……有的人向耶稣祈祷,有的人去麦加朝圣,有的人去进行亚原子层的粒子研究。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在寻找真理”[28]。在宏大叙事遭到消解的后现代社会里,“各种场合下存在的复数小写真理取代唯一大写真理”[29],这种特殊情境造就了布朗小说中特殊的信仰危机。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到:“我们每天都在为谁的上帝是真的而彼此争斗”,因而,他认为,当下信仰危机不在于缺乏信仰,而在于有太多的真理衍生出太多彼此倾轧的信仰。在成名作《达•芬奇密码》中,他就颠覆了官方宗教历史中关于耶稣的记载,借助“神圣女性”之说再现当下由于质疑官方真理而导致的信仰危机。
小说中,布朗对耶稣生平历史的改写主要体现在雷•提彬爵士的话语之中。提彬是英国皇家历史学家,倾尽一生致力于发掘圣杯的真相。他认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历史的本质是一家之言”[30],因而,他敢于质疑乃至否定官方历史。尽管他的理念中有许多与官方相左,但有三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关于《圣经》的,据他考察,它只不过是“人创造出来……历经了无数次的翻译和增补修订。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本确定的《圣经》”[31]。他认为今天的《圣经》是根据康斯坦丁大帝的意志编纂而成的,因为康斯坦丁想借助基督教力量加强自己的统治,甚至他本人也在晚年时皈依基督教。第二个是关于耶稣的身份问题。提彬觉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由官方提出的,这一说法在尼西亚会议上被投票通过”。康斯坦丁将耶稣神化的目的在于,作为神而非凡人存在的耶稣能够扩大教会的势力,进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他必须要销毁之前关于耶稣是凡人的一切记载,同时还要重新编纂一本将耶稣奉为神明的《圣经》,而那些依旧遵循先前记载的信徒则被视为异教徒,遭到清洗。最终,康斯坦丁版的《圣经》成为唯一合法真实的关于耶稣生平的记录。在前两个质疑的基础上,提彬得出与官方历史分歧最大的结论:根据耶稣的遗愿,抹大拉才是基督教合法的领导者。既然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他就有可能娶妻生子。在被认为是最早的基督教文献——《科普特文古卷》中,提彬发现抹大拉就是耶稣的妻子。那么,耶稣传位给她也在情理之中。不同于官方历史将其身份定位妓女,抹大拉是一位极有权势之人,因为提彬相信她是王室之后,这就更增加了耶稣遗愿的真实性。提彬的言论给现实世界造成巨大的波澜,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宗教历史学家叶尔曼就在其著作中称:“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必须建立在可考证的资料之上”[32],为此他斥责小说中提彬的观点,认为那些所谓的史实资料纯属无稽之谈。布朗对历史元素的大胆重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评断历史真假,而是为了在对历史真相的解读中引出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的信仰困境。
在各种真相面前,苏菲进退维谷。“神圣女性”概念的再挖掘激起了“一连串与当下社会状态和我们自身反应相关的希望与焦虑”[33],这种“希望”与“焦虑”并存的状态就是她首先要面临的道德选择。郇山隐修会保存了大量康斯坦丁《圣经》之前记载耶稣真实生活的文献,而苏菲则是唯一拥有发掘这些文献钥匙的人。如果这些文献被找到的话,“希望”与“焦虑”将同时发生。一方面,还原耶稣真实历史,进而重塑抹大拉的女神地位,人们就有机会在撇开男性家长制权威的条件下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另一面,那也会使全世界基督徒陷入信仰危机。提彬就曾明确告诉苏菲,如果那些文献被发现的话,“梵蒂冈将会面临两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信仰危机”[34]。苏菲感到困惑,因为她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其“赢得许多人的尊敬,也会招致许多人的嫉恨”[35]。为此,她陷入两难之地。她向兰登求助,急于知道兰登在其新书《失落的女神崇拜符号》中是否赞成批露那些文献。兰登的回答让她陷入了第二个困境。兰登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相信我们想象的真实,盲从我们无法证明的东西”[36]。在他眼中,宗教信仰方面的任何真相最终都是虚构的。有些人明白此点,知晓“这些故事传说都是隐喻性的”[37],而另一些人则固执地想要找到终极的真相。因而,选择哪种真相都是无意义的,因为这些虚构的真相是无法证明的。这样,苏菲就被抛进信仰的虚无之中,无论选择哪种真相都已不重要。小说的最后,这两种困境在苏菲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后被其淡忘,这样,布朗就将苏菲所受的信仰两难困境抛给了读者,让其在阅读之后反思解决方案。
“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38],布朗的文学想象正迎合了当下文学发展的这一走向,他借流行文学的形式书写严肃的文学主题。科幻元素与历史小说元素的加入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对其中伦理困境的思考。开放式结尾表明小说中善恶的冲突与真假的选择仍然存在。布朗之所以这样的结尾,意在刺激读者在享受阅读狂欢之余,能自觉反思自身的伦理境况,进而探寻一种属于自己的后现代伦理生活方式。参考文献:[1]陶洁. 美国的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N]. 文艺报,1988-09-17.[2]朱振武. 丹•布朗教给了我们什么[J]. 文学自由谈,2010(2):105.[3]丹•布朗.失落的秘符[M].朱振武、于是、文敏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6.[4]朱振武. 解密丹•布朗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39.[5]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J]. 外国文学研究,2010 (1): 14.[6]朱振武. 解码丹•布朗创作的空前成功[J]. 上海大学学报, 2005 (4): 44.[7] [8][16]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伦理学[M]. 张成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 13, 24.[9]Lisa Rogak. The Man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an Brown[M]. Kansas: Andrew McMeel Publishing, 2005. 12.[10]朱振武等. 丹•布朗们的居家密码[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 228-229.[11]聂珍钊等. 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35.[12] [13] [14] [15]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丹•布朗. 数字城堡[M]. 朱振武、赵永健、信艳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4, 118, 92, 24, 117, 117, 118, 118, 228, 93, 228, 32, 32.[25]Dan Brown. Inferno[M]. New York: Doubleday, 2013. 440.[26]Torin Monahan. Surveillance and Security: Technological Politics and Power in Everyday Lif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0.[27]万俊人. 信仰危机的现代根源及其文化解释[J]. 清华大学学报. 2001(1): 27.[28]丹•布朗. 天使与魔鬼[M]. 朱振武、王巧俐、信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5.[29]Philip Sampson. Faith and Modernity[M]. Oxford: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1994. 37.[30][31][34][35] [36] [37]丹•布朗. 达•芬奇密码[M]. 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34, 211, 244, 272, 320-321, 321.[32]Bart D. Ehrman. Truth and Fiction in The Da Vinci Cod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xxi.[33]Robert A. Davis. “The Works of the Female: Mary Magdalene and the Return of the Goddess”[C], The Da Vinci Code in the Academy, Bradley Bowers eds.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3.[38]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62.作者简介:束少军(1988-),男,汉族,安徽省合肥市人,上海大学2011级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