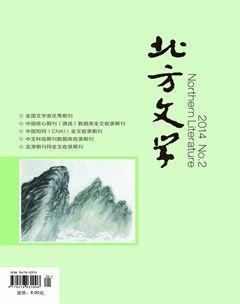王安忆与张爱玲的都市小说创作比较
摘 要:近年来评论界将王安忆视为张爱玲的传人,总是将其二者放在一起比较,但对于二者的相似与相异性,一直存在颇多争议之处。本文试图从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出发,探究其二者都市小说创作的异同。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长恨歌》
一九九五年,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出版了长篇小说《长恨歌》,在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认为王安忆此作直逼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更有人认为《长恨歌》是比张爱玲还张爱玲的小说。一时间,王安忆的名字被频频与“张爱玲”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本文从王安忆的《长恨歌》出发,在其背景环境的描写、人物与时空的关系、虚无与现实的叙事等三个方面作一比较,以期对这两位同样出色的女作家有更清楚的认识。
一、背景环境的描写
翻开《长恨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长达几万字的背景环境描写。“弄堂”、 “流言”、“闺阁”、“鸽子”以及紧随人物命运的“片场”,后来的“爱丽丝公寓”、“邬桥”,一个新的弄堂“平安里”。
这些背景环境描写把读者引入了作者营造的特殊气氛之中,犹如身临其境,引领读者视线,为其迅速走入王琦瑶的内心世界打下了基础。除此以外,和小说主体的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很多描写看似随意,却与后来的故事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是暗含在文本中数不清的伏笔之一。比如《鸽子》一节:“许多无头案,它们都是证人。它们都是证人。它们眼里,收进了多少秘密呢?”“当天空有鸽群惊飞而起,盘旋不去的时候,就是罪罚祸福发生的时候。”这些都和结尾一节《碧落黄泉》相互照应,使前面的描写不流于无谓的堆砌,而是形成镜子般的对照。
《长恨歌》的背景环境描写是王安忆对于张爱玲写作风格的一种承袭与超越。张爱玲最擅长的就是将叙述人、读者与故事的人物远远的拉开距离,将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成功剥离,从而形成一种旁观、张看的全知视角。作为对张氏风格的一种沿袭,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同样试图使用这种手法,只是不如张爱玲那样明显。“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物化的“制高点”,其实就是全知视角的象征。这和张爱玲的“在云端看厮杀”其实是相同的目的。《鸽子》中又写道“前边说的制高点,是我们人类能够企及和立足的呢?”这里“鸽子”同样成了一种“上帝视角”象征。作者通过“制高点”的过渡,力图将全知视角贯穿文本始终,有意无意地将笔下的鸽子变成了张爱玲在《沉香屑》中写的香,在《倾城之恋》中写的咿咿呀呀的胡琴,在《金锁记》中写的月亮,贯穿文本始终,充满了象征的色彩。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王安忆的这种叙事相对于张爱玲有所超越。张爱玲对上海特色的描述是零散的、往往贯穿于小说的细节之中,是为将读者引入人物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而渲染气氛,侧重于在深度上的展现。而王安忆对上海从宏观角度的整体描写,起到一种既能通过直观写实引领故事开场,又能表现出整部小说沧桑兴衰基调的作用,侧重于在广度上展现。从这一点看,王安忆的开篇描写更符合长篇小说叙事的要求,也体现了她超越了张爱玲略嫌狭窄的文化视野。
二、人物与时空的关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空间都有着一种被限定的拘束。她的小说一般来说,都有一个主要的活动空间,如果有变化也只是那么一次,然后又回归于那主要的活动空间。因此,她的小说的叙述空间是封闭的。而因为叙述空间的封闭性,张爱玲小说中的叙述时间也是静止的,凝滞在那里的。因此,几乎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小说叙述中,是不存在历史时间的,历史在她的叙述中是不存在的,而且时间因素由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有被空间化的倾向。
在这种封闭、静止的时空观中,产生了张爱玲笔下的那一部部都市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如流苏、曼桢、烟鹂、娇蕊等,皆形象鲜明,令人过目不忘,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张氏小说中,这两者却是各自存在、不甚相干的。上海之于张爱玲,就像鲁镇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仅是作为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现实背景而存在的。她笔下那些女子的悲欢离合,虽说是在上海这座城市里上演,但上海并不能够左右她们的人生,上海对于她们而言,只是一个偶然的落脚点,而换了别的地方,她们的故事也一样还要上演。可见,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物与时空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二者是各自独立存在的。
《长恨歌》把一个女人的一生与一个城市的历史交融在一起进行描写。小说从20世纪30-40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50年代“人民公社”的上海、60年代“文革”的上海,一直写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王安忆通过对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的书写再现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时代变化,在她的笔下,不同时期的上海对主人公的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长恨歌》当中,叙述时间是流动的,王安忆有意完成了人物与时间的融合。除此之外,她的叙述空间是开放的,与张爱玲的故事通常发生在一个封闭的房子或家族中相比,《长恨歌》显然具有开放性。故事不单单是在上海这一个地方发生,中间还穿插了邬桥这个地点,同样是在上海,根据王琦瑶人生的不同时期,王安忆为她安排了不同的居住场所,而正是由于居住场所的变更又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开放、流动的时空观恰恰与张爱玲那种封闭、静止的时空观相反。可见,在王安忆的笔下,是以人物来书写时空变化的。
三、虚无与现实的叙事
张爱玲曾经这样评价《红楼梦》:“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这段话同时也表明了张爱玲的小说观与人生观。
张爱玲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不管如何眷恋,过去的好时光都已经无法挽回。透过繁华的世相表面,张爱玲体验到孤独和寂寞的刻骨铭心。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更使她感受到个体的渺小与孤寂、生命的虚无与幻灭。最终促成了她悲观虚无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从而反映在她的都市小说叙事中。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同时,她又不由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狭隘。所以,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
而王安忆刚好相反,在她看来现实与虚无之间其实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她的叙事观是现实的,这一点在《长恨歌》中有着明显的体现。王琦瑶的一生完全是按照她自己的选择来过的,她是自我的,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而不必有所顾忌。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人物在作出选择时总是有重重顾忌,而且由于不敢直面现实,她们总是选择向生活妥协,将自己束缚起来。这一点无论是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还是《半生缘》中的顾曼桢身上都有所体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者看不到时代的影子,也没有具体鲜明的空间位置,所有的目光都只集中在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上,所以不免产生一种虚空感。王安忆则与此形成相反的对照,她不仅赋予了人物鲜明的时代特色,还敢于将人物最终走向死亡的血淋淋的过程描绘出来,这一点在张爱玲的笔下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所以王安忆比张爱玲现实的多,最起码她比张爱玲更多了一份勇气,即使前边是虚无的,她仍然要过去看看,直面现实而不是逃避。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将王安忆与张爱玲相提并论是不无道理的。她们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如果细细品读她们的作品便会发现她们终究是不同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没有两位作家会写出完全相同的作品。相信在未来,她们之间还有更多的异同之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3]高秀芹.都市的迁徙——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时空比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作者简介:侯佳俐(1992-),女,河南安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对外汉语专业2011级本科生。
endprint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