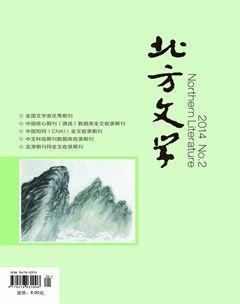三角结构与人文:论戏剧《雷雨》创作的无意识结构
摘 要: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认为,无意识有着与语言相似的结构,并且决定语言秩序的结构。戏剧《雷雨》中,贯穿着一种相似性的“无意识重复”的三角结构,其后隐匿的是作者的人文关怀。也正是这种重复,表征着曹禺《雷雨》创作背后被遮蔽的无意识结构。
关键词:话语;三角结构;无意识;人文
《雷雨》是曹禺先生的第一部话剧,从对该话剧的话语结构整体解读中,发现整部话剧存在一种重复的无意识的相似性三角结构,也正是这样无意识的相似性结构的存在,决定了戏剧《雷雨》的语言结构,同时表征着曹禺《雷雨》创作背后被遮蔽的无意识结构。
一、相似性三角结构的话语分析
《雷雨》中的人物关系主要分为2种关系:家庭伦理关系,阶级对立关系。亦可细分出主仆关系,夫妻(恋人)关系等。如下图:
父 母 子/女
鲁侍萍 鲁贵 四凤 互恋 单恋
鲁侍萍 周朴园 鲁大海(长) 兄弟
鲁侍萍 周朴园 周萍(次)
繁漪 周朴园 周冲
从上可以发现三组相似性的结构关系,第一组是周朴园、周萍和周冲之间构成的三角关系结构与鲁贵、四凤和鲁大海之间构成的三角关系结构 ,如下图所示:
周朴园 鲁贵
周萍周冲四凤 鲁大海
图1
周朴园,作为周家话语权的主宰者,要求其言行得到其他人绝对的遵从,周萍、周冲都不敢违其意行事。而鲁贵是鲁家中话语权的掌控者,虽在周家做仆人,但完全是作为第二个周朴园(在鲁家中)而存在。工运领袖大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但这种反抗在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面前,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组三角结构中,周鲁两家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无论从阶级地位还是经济实力比较,周家都完全压倒鲁家。何况,鲁贵及女儿四凤又在周家做仆人;工运代表大海也是在周朴园手下做事。所以,整体看来,鲁家是从属于周家的。而且,在这两个家庭构成的关系图间存在一种相似性的关系:封建权威的笼罩。这种相似性的关系的形成,正是曹禺在写作该剧过程中一种“无意识”的产物。而当时社会革命的条件和时机并不成熟,这样,两个三角结构中,年轻一辈仍是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发语权。于是,封建权威在两家的流动,决定了两组三角构架中不同的主体担任不同的角色。《雷雨》整个剧情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相似性的流动中推动着向前进。先是引出周家的故事,在逐渐道出周鲁鲁两家的复杂关系,最后两家因种种因缘、巧合,聚到一起,繁漪道出周萍与四凤之间的恋人关系,酿成悲剧。
再看一组相似性关系,由周朴园、繁漪和鲁侍萍之间的三角关系和四凤、周萍和周冲之间构成的三角关系组成,如下图所示:
周朴园 四凤
繁漪鲁侍萍 周萍 周冲
图2
从图中可见出一些相似性关系。其一,相似性的恋人关系。周朴园与繁漪、鲁侍萍(前妻)都是恋人关系,而且,在赶走侍萍之后,周朴园还一直保存着当年她在周家的家具摆设,对她恋恋不忘。右边四凤与周萍、周冲也是恋人关系,尽管周冲是单恋。其二,左边三角关系中的主体都是长辈,而右边的主体都为晚辈,左右两边都同时保持了一种完整的相似性关系。从剧情的发展来看,都是从左边的三角关系衍生至右边,逐步推进的。其三,从整个戏剧在一种压抑、郁热的环境中进行,戏剧的结尾是:左边图中繁漪、鲁侍萍都疯了,周朴园神智几近崩溃;右边图中,周萍自尽,四凤、周冲触电身亡。这样的结局,也存在着极度的相似性。可以看出,整个剧情都是在这种相似性的流动中向前发展的。同时,这种相似性结构关系的流动,在文本叙事中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重复。这种相似性结构的重复流动,由此也引起了文本中人物角色命运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另外一组相似性结构,由周家(周公馆)、繁家(繁漪)和鲁家之间的三角结构关系与大海、周萍和周冲之间三角结构关系组成。前一组关系中存在的是阶级对立,后一组关系中存在的则是兄弟关系。据此可进行“场景还原”。鲁家和繁漪属于受迫害的一方,她们的不幸来自周朴园的淫威,这三家之间一直存在有矛盾冲突。周萍和周冲两兄弟都爱上了四凤,由于周冲的天真和善良,他们更多是的深层的内心冲突而非表面的冲突。及至周萍当着侍萍打鲁大海的耳光,致使冲突炙热化,但仍属于兄弟间的冲突。如下图所示:
周家 鲁大海
繁家(繁漪)鲁家 周萍周冲
图3
由上三组图见出,戏剧是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行进的。不论是以上哪种冲突,都有一个特征:相似性。而且,这些冲突的流动造成文本中主体担任不同的角色。由此不难看出,《雷雨》中语言背后存在一种无意识重复在流动,它的流动构成了以上三组相似性话语结构,形成一种虚构的“符号秩序”,而这正是作者创作中一种无意识流露的结果。“因为说到底,无意识是隐藏在意识层背后的东西,只有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才具有一种内视语言的意义结构。”[1] 故此,潜藏于曹禺创作背后的无意识,伴随着一种语言的意义结构而现于笔端。诚如曹禺所言,“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 ”[2]而“绝非一个社会问题剧。”[3]那么这种无意识的重复流动是怎么形成的呢,本文将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二、雷雨:“一个纯粹的能指”的流动
“拉康认为,结构化的语言(the formal langugae)是先在的,对主体具有构造功能,因而决定主体。”[4]剧中“雷雨”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既可看作是当时社会背景的暗示,也可理解为黎明到来的前兆,或者一种“雷雨”式的性格。诚如学者所言:“和一切经典性作品一样,《雷雨》也是说不尽的: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开掘与阐释。”[5]其实“雷雨”象征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雷雨在文本中作为“一个纯粹的能指”而存在,它具有隐喻性性质。“‘隐喻是‘能指的替换,同‘凝缩一样具有相似性特点,即项目之间由于彼此相似而发生联系,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显示欲望的词语被另一个意义相近的词语取代,这另一个词语提供出了解无意识欲望(能指)的线索。”[6]正是基于“雷雨”此种隐喻性质,才指涉出文中话语结构中的无意识重复现象。
“雷雨”也可用剧中“郁热”,“躁动”,“抑郁”等语词来代替。这些词,在专制的环境下显示出一种欲望和力量。但于曹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憧憬。“《雷雨》对于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7]剧中“雷雨”这种“郁热”的气氛贯穿了全文,整个剧中的冲突都是在这种“郁热”环境下进行的。雷雨既渲染了氛围,又加剧了冲突。它既是旧式力量的余威,又是新生力量即将到来的象征。总之,不管主体(剧中人物)在不在场,它总是作为一种潜在的真实存在而存在着。即以一种“无意识的重复”流动,贯穿在这三组结构图中。
endprint
在这三组图中,无论主体在场与否,他们担任的角色和所表现出来的言行都受到这种“无意识重复”的支配。图1两边结构关系就受封建权威的支配,周朴园实亦是封建专制下的牺牲品。此时“郁热”则是封建专制占优势地位。及至四凤出走,“雷雨”的轰鸣则象征一股新生力量的即将到来。图2中右边的主体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受左边三角关系(长辈)的制约;图3中人物的结局基本都走向了毁灭。此时“雷雨”的描写,则加剧了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抗,覆灭与新生共存。“雷雨”贯穿在这三组关系中流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重复”流动现象。诚如学者所言:“在拉康看来,象征是被结构化、符号化为语言的‘现象的秩序。”[8]“雷雨”在文本中作为一种象征,“在这里,具有能指性质的象征性秩序或者说符号秩序是第一性的,它存在于主体之先。”[9]。因为“拉康是用象征指称一种话语结构”[10],而且这种话语结构的内在构成要素“像语言学中的能指一样起作用的,它建立起维护自身秩序的法规”[11]。在本文中表现为一种三角结构的话语机制。
三、人文精神的逆反表达:隐匿的人文
在这种相似性结构的重复中,由于能指(“雷雨”)的流动,造成了不同的三角结构关系。拉康认为,能指(语言)对于主体有着制约作用。在《雷雨》中,能指的流动决定小说中不同主体担任不同的角色。而能指受到抵制意指的阻隔,与所指间的纽带被切断,成为“漂浮的能指”,能指的流动在《雷雨》中形成一种“无意识的重复”。“在拉康看来,无意识有着与语言相似的结构,无意识是在语言的秩序中形成的,因此作为主体的象征的艺术,也必然具有由无意识决定的语言秩序的结构,也就是说,是无意识决定了这篇小说的语言结构。”[12]而文中相似性三角结构的重复流动,正是作者无意识语言结构的表征。
作为知识分子的曹禺,内心反抗着专制的压抑,同时也在探索着出路,并使之内化为情感,在剧中以一种无意识重复的方式流露出来。图1中呈现的是以家庭单位形成的三角结构,这种压抑来自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图2中呈现的则是封建家长制下扭曲的爱情关系,结局只能是走向虚无。图3中呈现阶级对立的关系中,兄弟之情亦受到扭曲。大海的出走是希望,更是作者的一种思考和探索。缺少话语权的弱者,受到的多是来自封建权威的话语暴力的侵袭、压制。如剧中繁漪被逼迫喝药的场景:四凤给她端药给她,她一度辩解没病。“谁说我要吃药”[13]“我不愿意和这种苦东西”[14]及至后来周朴园让她看克大夫的时候,繁漪的反抗更直接,连续三次强调:“我没有病!”[15]
显然,这些并不是曹禺最想表达的东西,作者是以戏剧这种形式来探索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并且深深同情处在压迫下的人们。在这种思考的背后,隐藏的是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曹禺并没有直接在文中把它表现出来,观众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话语暴力对人性的压制。而繁漪辩解自己没病的一连串的反抗话语,恰恰表征着曹禺的人文关怀。剧中人文精神正是借助反抗话语暴力的行为来表达的,反抗越烈,关怀愈深。而周朴园,则是话语暴力的行使者,他的话是一种单向度的话语表达。其假装关心话语后面隐藏的是语言暴力行为,而这种语言暴力的相似性在周、鲁两家都存在着。无疑,曹禺是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创作的,正因此,整个剧中充满着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令观者深受触动。诚如曹禺所言“并没有明显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16],“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动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17]
作者的人文关怀就隐匿在这一系列相似性三角结构的无意识重复中,“无意识集中在心理结构的上层(想象界、象征界),它不是生物的需要,而是某种文化化和社会化的东西。无意识并非是无序的或不可控制的,而是有序的,具有文化性质的话语结构。”[18]正是这种三角结构话语的重复流动,表征着曹禺《雷雨》创作背后被遮蔽的无意识结构。
参考文献:
[1][18]王岳川.拉康的无意识与语言理论[J].人文杂志. 1998-01:126、126.
[2][3]曹禺:《雷雨》的写作[J].杂文.1935-07(2).
[4]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488.
[5]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8.
[6][8][9][10][11][12]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485.486.486.486.486.488.
[7][16][17]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1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11、211、211.
[13][14][15]曹禺著.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2、52、82.
作者简介:田其德(1987-),男,湖南邵阳人,广西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批评。
endprint
在这三组图中,无论主体在场与否,他们担任的角色和所表现出来的言行都受到这种“无意识重复”的支配。图1两边结构关系就受封建权威的支配,周朴园实亦是封建专制下的牺牲品。此时“郁热”则是封建专制占优势地位。及至四凤出走,“雷雨”的轰鸣则象征一股新生力量的即将到来。图2中右边的主体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受左边三角关系(长辈)的制约;图3中人物的结局基本都走向了毁灭。此时“雷雨”的描写,则加剧了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抗,覆灭与新生共存。“雷雨”贯穿在这三组关系中流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重复”流动现象。诚如学者所言:“在拉康看来,象征是被结构化、符号化为语言的‘现象的秩序。”[8]“雷雨”在文本中作为一种象征,“在这里,具有能指性质的象征性秩序或者说符号秩序是第一性的,它存在于主体之先。”[9]。因为“拉康是用象征指称一种话语结构”[10],而且这种话语结构的内在构成要素“像语言学中的能指一样起作用的,它建立起维护自身秩序的法规”[11]。在本文中表现为一种三角结构的话语机制。
三、人文精神的逆反表达:隐匿的人文
在这种相似性结构的重复中,由于能指(“雷雨”)的流动,造成了不同的三角结构关系。拉康认为,能指(语言)对于主体有着制约作用。在《雷雨》中,能指的流动决定小说中不同主体担任不同的角色。而能指受到抵制意指的阻隔,与所指间的纽带被切断,成为“漂浮的能指”,能指的流动在《雷雨》中形成一种“无意识的重复”。“在拉康看来,无意识有着与语言相似的结构,无意识是在语言的秩序中形成的,因此作为主体的象征的艺术,也必然具有由无意识决定的语言秩序的结构,也就是说,是无意识决定了这篇小说的语言结构。”[12]而文中相似性三角结构的重复流动,正是作者无意识语言结构的表征。
作为知识分子的曹禺,内心反抗着专制的压抑,同时也在探索着出路,并使之内化为情感,在剧中以一种无意识重复的方式流露出来。图1中呈现的是以家庭单位形成的三角结构,这种压抑来自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图2中呈现的则是封建家长制下扭曲的爱情关系,结局只能是走向虚无。图3中呈现阶级对立的关系中,兄弟之情亦受到扭曲。大海的出走是希望,更是作者的一种思考和探索。缺少话语权的弱者,受到的多是来自封建权威的话语暴力的侵袭、压制。如剧中繁漪被逼迫喝药的场景:四凤给她端药给她,她一度辩解没病。“谁说我要吃药”[13]“我不愿意和这种苦东西”[14]及至后来周朴园让她看克大夫的时候,繁漪的反抗更直接,连续三次强调:“我没有病!”[15]
显然,这些并不是曹禺最想表达的东西,作者是以戏剧这种形式来探索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并且深深同情处在压迫下的人们。在这种思考的背后,隐藏的是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曹禺并没有直接在文中把它表现出来,观众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话语暴力对人性的压制。而繁漪辩解自己没病的一连串的反抗话语,恰恰表征着曹禺的人文关怀。剧中人文精神正是借助反抗话语暴力的行为来表达的,反抗越烈,关怀愈深。而周朴园,则是话语暴力的行使者,他的话是一种单向度的话语表达。其假装关心话语后面隐藏的是语言暴力行为,而这种语言暴力的相似性在周、鲁两家都存在着。无疑,曹禺是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创作的,正因此,整个剧中充满着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令观者深受触动。诚如曹禺所言“并没有明显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16],“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动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17]
作者的人文关怀就隐匿在这一系列相似性三角结构的无意识重复中,“无意识集中在心理结构的上层(想象界、象征界),它不是生物的需要,而是某种文化化和社会化的东西。无意识并非是无序的或不可控制的,而是有序的,具有文化性质的话语结构。”[18]正是这种三角结构话语的重复流动,表征着曹禺《雷雨》创作背后被遮蔽的无意识结构。
参考文献:
[1][18]王岳川.拉康的无意识与语言理论[J].人文杂志. 1998-01:126、126.
[2][3]曹禺:《雷雨》的写作[J].杂文.1935-07(2).
[4]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488.
[5]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8.
[6][8][9][10][11][12]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485.486.486.486.486.488.
[7][16][17]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1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11、211、211.
[13][14][15]曹禺著.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2、52、82.
作者简介:田其德(1987-),男,湖南邵阳人,广西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批评。
endprint
在这三组图中,无论主体在场与否,他们担任的角色和所表现出来的言行都受到这种“无意识重复”的支配。图1两边结构关系就受封建权威的支配,周朴园实亦是封建专制下的牺牲品。此时“郁热”则是封建专制占优势地位。及至四凤出走,“雷雨”的轰鸣则象征一股新生力量的即将到来。图2中右边的主体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受左边三角关系(长辈)的制约;图3中人物的结局基本都走向了毁灭。此时“雷雨”的描写,则加剧了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抗,覆灭与新生共存。“雷雨”贯穿在这三组关系中流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重复”流动现象。诚如学者所言:“在拉康看来,象征是被结构化、符号化为语言的‘现象的秩序。”[8]“雷雨”在文本中作为一种象征,“在这里,具有能指性质的象征性秩序或者说符号秩序是第一性的,它存在于主体之先。”[9]。因为“拉康是用象征指称一种话语结构”[10],而且这种话语结构的内在构成要素“像语言学中的能指一样起作用的,它建立起维护自身秩序的法规”[11]。在本文中表现为一种三角结构的话语机制。
三、人文精神的逆反表达:隐匿的人文
在这种相似性结构的重复中,由于能指(“雷雨”)的流动,造成了不同的三角结构关系。拉康认为,能指(语言)对于主体有着制约作用。在《雷雨》中,能指的流动决定小说中不同主体担任不同的角色。而能指受到抵制意指的阻隔,与所指间的纽带被切断,成为“漂浮的能指”,能指的流动在《雷雨》中形成一种“无意识的重复”。“在拉康看来,无意识有着与语言相似的结构,无意识是在语言的秩序中形成的,因此作为主体的象征的艺术,也必然具有由无意识决定的语言秩序的结构,也就是说,是无意识决定了这篇小说的语言结构。”[12]而文中相似性三角结构的重复流动,正是作者无意识语言结构的表征。
作为知识分子的曹禺,内心反抗着专制的压抑,同时也在探索着出路,并使之内化为情感,在剧中以一种无意识重复的方式流露出来。图1中呈现的是以家庭单位形成的三角结构,这种压抑来自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图2中呈现的则是封建家长制下扭曲的爱情关系,结局只能是走向虚无。图3中呈现阶级对立的关系中,兄弟之情亦受到扭曲。大海的出走是希望,更是作者的一种思考和探索。缺少话语权的弱者,受到的多是来自封建权威的话语暴力的侵袭、压制。如剧中繁漪被逼迫喝药的场景:四凤给她端药给她,她一度辩解没病。“谁说我要吃药”[13]“我不愿意和这种苦东西”[14]及至后来周朴园让她看克大夫的时候,繁漪的反抗更直接,连续三次强调:“我没有病!”[15]
显然,这些并不是曹禺最想表达的东西,作者是以戏剧这种形式来探索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并且深深同情处在压迫下的人们。在这种思考的背后,隐藏的是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曹禺并没有直接在文中把它表现出来,观众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话语暴力对人性的压制。而繁漪辩解自己没病的一连串的反抗话语,恰恰表征着曹禺的人文关怀。剧中人文精神正是借助反抗话语暴力的行为来表达的,反抗越烈,关怀愈深。而周朴园,则是话语暴力的行使者,他的话是一种单向度的话语表达。其假装关心话语后面隐藏的是语言暴力行为,而这种语言暴力的相似性在周、鲁两家都存在着。无疑,曹禺是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创作的,正因此,整个剧中充满着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令观者深受触动。诚如曹禺所言“并没有明显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16],“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动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17]
作者的人文关怀就隐匿在这一系列相似性三角结构的无意识重复中,“无意识集中在心理结构的上层(想象界、象征界),它不是生物的需要,而是某种文化化和社会化的东西。无意识并非是无序的或不可控制的,而是有序的,具有文化性质的话语结构。”[18]正是这种三角结构话语的重复流动,表征着曹禺《雷雨》创作背后被遮蔽的无意识结构。
参考文献:
[1][18]王岳川.拉康的无意识与语言理论[J].人文杂志. 1998-01:126、126.
[2][3]曹禺:《雷雨》的写作[J].杂文.1935-07(2).
[4]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488.
[5]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8.
[6][8][9][10][11][12]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485.486.486.486.486.488.
[7][16][17]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1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11、211、211.
[13][14][15]曹禺著.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2、52、82.
作者简介:田其德(1987-),男,湖南邵阳人,广西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批评。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