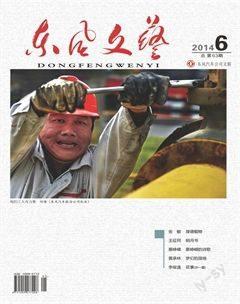风继续吹
瞿可丁
奶奶离开我很多年了。然而她那好像是总也唱不完的儿歌,这么多年却一直潜藏于我的心底。那好像是她老人家特意留给我的一笔“遗产”,或者是类似于“护身符”之类的“灵物”,通过它,奶奶默默地为我祝福。
奶奶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几岁,那是一个对一般城里的孩子来说还并不怎么懂事的年纪。而对于出身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农家并拥有四个弟妹的我来说,却已开始为大人们分担生活的艰难了。悲恸的同时,我清楚地知道,从此我再也见不着奶奶那永远慈祥的面容;再也吃不着奶奶做的腌菜;在我受委屈或被别的孩子欺负的时候,再也得不到奶奶那口口声声像是真的要替我出气的哄骗与安慰了;而最让我伤心的是,再也听不见奶奶的儿歌了!有好一阵子我都觉得精神恍惚,无依无靠。
儿时的情景记得最真。
记得在我四岁那年。一次我穿了一双脚尖上缀着一朵小红花的新布鞋(可能是那时候流行的款式)。由于小孩子的虚荣,便急不可耐地要在小伙伴们面前把两只脚踢来踢去显摆一番。后来干脆就在屋子门前练起了短跑比赛,似乎那双鞋能助我跑得更快。跑着跑着不好了,只觉得有个东西绊了一下,我便实打实地趴在了地上。凡是先着地的部位——脑门、鼻尖、手掌、膝盖都蹭破了皮,血迹斑斑;嘴也啃了许多沙土;脚趾更是蹴翻了皮。奶奶听到哇哇的哭声便拖着一双小脚颠来。问清了原委,只见她顺手拿过一把附近猪圈墙头的粪耙,照准那块绊我脚的石头就是几耙子。随后,我被奶奶牵进家,我边哭边诅咒那块石头。奶奶给我擦洗之后把我抱上膝头,拿给我一大把姑妈从汉口带来孝敬她的饼干。在又诅咒了一顿石头之后,奶奶给我轻声地唱起了儿歌。我忘记了疼痛,静静地听着: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提笆篓/笆篓破,捞菱角/菱角尖,杵上天……
不觉已是黄昏,大人们还没放工,奶奶便开始张罗做夜饭。等饭做好了,我们都吃完了,大人們还没回来。我便又闹着要奶奶教我唱儿歌。奶奶给闹得没法子,就把我搂在怀里,然后轻声地哼起:星斗哥哥,月亮嫂嫂/莫割我的伢儿的耳朵……渐渐地,我在奶奶的臂弯里睡着了。
多年以后,当我对音乐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时,我意识到,也许正是奶奶的儿歌在我心灵深处播下了第一粒音乐的种子。我无法忘怀奶奶那纯朴、清新,饱含着真挚的爱和浓郁的泥土芬芳的儿歌!奶奶的儿歌如温馨的乳汁伴我长大,浸透我成长的历程。虽然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往事,但一切都恍如昨天。奶奶去了,但她的儿歌犹在。就像是窗外这温馨的秋风,总是不经意间拂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