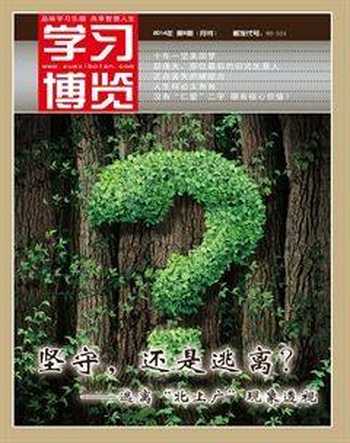人生何必太匆匆
元年春
“童话王子”王尔德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还是懒散生活的倡导者,曾说过“无所事事绝非易事”。藏书家爱德华•纽顿讲过一个故事:王尔德在一个乡村别墅过周末,借口工作需要离开其他宾客。晚上用餐时,女主人问他上午做了些什么,他说:“我在我的一首诗里加上了一个逗号。”夫人又惊喜又感兴趣地问起下午的工作是否使他同样筋疲力尽,王尔德厌烦地以手遮眉,道:“这个下午我又把逗号去掉了。”纽顿由此评论说:“他像艺术家对待色彩那样斟词酌句,反复推敲……但王尔德喜欢无所事事。”1882年,王尔德赴美国巡回演讲时,针对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在急着赶火车的情形感慨:“要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总为乘火车而担心,或是为返程票而烦恼,莎士比亚就不可能写出那几幕如此富有诗意、哀婉動人的戏了。”他说:“这种情形对诗歌和浪漫爱情是不利的。”
林语堂崇尚“自由和淡泊”以及“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在《生活的艺术》中,他感叹道,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在终日劳作,辛苦奔命,而其他动物都在跟着季节更替,享受悠然的时光,闲适的生活。他说:“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他把阅读分为两种:一种是公事上的必要,另一种则是奢侈的享受。第二种才给人带来“开朗的容颜,满胸的清气”,仿佛漫步林中,而不是走向市场。他试图把闲适的东方哲学介绍给当时忙碌的西方人,“希望千年后美国文化是这样的:大街上,人们不那么匆匆忙忙,而是放慢脚步,问候一个行人:你的祖母怎样?不坐汽车,而是坐着牛车,穿着拖鞋悠哉散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丰子恺在杭州做“寓公”。当时,故乡附近的海宁已经通了火车,老家石门湾也有了小火轮。坐火车和火轮回家,只需要两三个小时。但是,每次回家,他都选择花上两三天时间,乘坐慢悠悠橹声欸乃的木制航船。对此,直到晚年他还记忆犹新:“吃过早饭,把被褥用品送进船内,从容开船。凭空闲眺两岸景色,自得其乐。中午,船家送出酒饭来,傍晚到达塘栖,我就上岸去吃酒了。”第二天,如果兴致好,他会在塘栖游玩一天,赶上春末,还会“买些白沙枇杷,回到船里,分些给船娘,然后自吃”。次日,客船再沿运河,经过梁山坟一直摇到杭州横河桥上岸,然后坐上人力黄包车,拉到市中心的田家园寓所。在旅途中,他读书作文,还画了很多有名的漫画。有段时间,每次路过塘栖,船泊在小杂货店门口的运河里,从客船的小窗里看出去,总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孜孜不倦地在“打绵线”,他由此创作出名作《三娘娘》。
现代生活节奏实在太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兰•昆德拉忍不住将自己的一部作品直接命名为《慢》。他追问:“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在书中,“慢”是指没有汽车电话的18世纪,出门要靠笃笃悠悠的马车,消息要靠磨磨蹭蹭的信件。但到了“快”的20世纪,在机器革命了自然的世界里,生活被装置上发动机,开足了马力,于是我们开始了转瞬即逝的生活。他将之归结为一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
汤姆•霍奇金森可谓英国“闲人党”的首脑,创办了一本《闲人》杂志,还煞有介事地写出《优游度日:如何一天度过24小时》,按时间的顺序从24个方面介绍了如何过悠游的生活。他感叹“千古艰难唯起床”,还埋怨闹钟:“花自己的血汗钱买个设备,好让人生中的每一天尽可能不痛快地开始,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自己出卖时间的对象——雇主,这不是太可笑了嘛?”他认为爱迪生是闲散的大敌,因为后者认为睡眠没有产出,纯属浪费时间。霍奇金森言辞犀利,指责麦当劳、肯德基最符合法西斯主义者对食物功能的定义——给工人身体注入能量;星巴克不过是工作机器的F1赛车加油站,而那种长年累月泡在咖啡馆里打发闲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面对快餐式阅读,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托马斯•组柯克批判道:“在学校,阅读已经变成竞赛,孩子们掐着秒表读书,看谁一分钟里读的文字量最多。还有专家研究出让视线在书页上走Z字的快速扫描方式,教孩子们怎么用最短的时间读完一页书——照此办法,阅读有望提速4–5倍,远远超过火车提速。这些都在灌输一种观念,快即好。以这种错误观念对待阅读,还能有什么乐趣?”他提出“慢阅读”概念,主张细细阅读一本好书,反对一目十行,甚至在课堂里鼓励学生重拾大声诵读和背诵的老办法。然而,这些已经习惯快速浏览网页的年轻人,再次面对纸质读物时,竟然很难集中注意力。对此,组柯克说:“我想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一目十行中失去了多少。”
已入耄耋之年的金庸说:“我的性子很缓慢,不着急,做什么都是徐徐缓缓,最后也都做好了,乐观豁达养天年。”他说话慢吞吞的,让人以为他结巴;走路也是慢吞吞的,看起来像大象的脚步。他喜欢驾车,尤喜开跑车。但就算性能极佳的保时捷,他也只“跑”出每小时三十里的速度。曾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他回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金庸不尚奢华,羡慕“且自逍遥没人管”的生活,饮食简单清淡,七八分饱,衣着自然简朴。他说:“人要善于有张有弛。武打小说打一会儿,就要吃饭,谈情说爱,不能老是很紧张,要像《如歌的行板》韵律一样,有快有慢,这样对健康很有好处。”
——千年文脉焕新生塘栖古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