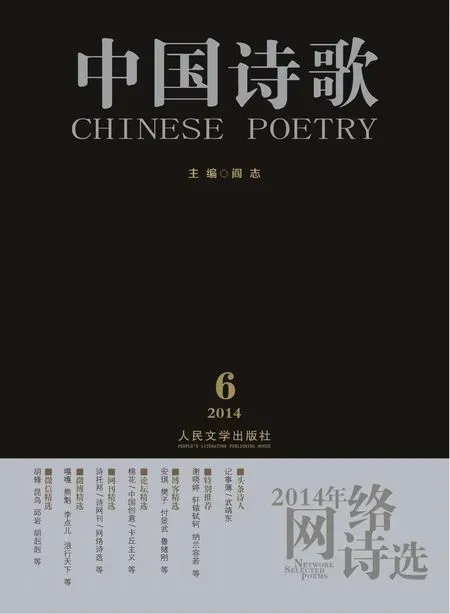新锐诗刊
新锐诗刊
听 雪〔外一首〕
王蕾
我看见古道湮没,长亭黯然
南山在琴声里,渐渐地白了头
一条承载往事的弦
愈加低缓
弦上,雪在飞
必须飞高一点
再高一点……如果错过了我的衣角
错过了,横逸的松柏、竹影
或某个词,就与梅花做小姐妹
如果琴还醒着
如果雪也一直不眠
请继续飞,让枝头上的小姐妹重新开一次
让我在崇高中,且现且隐
冬至书
我写这苍茫,写异地的冬天
写四明山一场雪
没有等到另一场雪便融化掉了
写我从伤感中抽身
一次次北望山梁
和那么多消失的脚印,纠缠不清
写吹进眼里的尘埃,遮住
黛色或蔚蓝
写夜更深,我在梦里买下一片浮云
签署自己的名字
写鸿雁,也许顺着惠济河、淮河的流向
从我的省份河南来
越飞越载不动
心上的家书
我写一九、二九、三九……
写被我抽短的光阴
在一天天见长
春天的渡口
湘妃
山峦离我很远,它静默于
覆满草叶的小径之后
那是锯齿类和蕨类植物的国度,饰以
露水和雾珠,草丛里飞出的鸟
扑棱着翅膀,兀自形单影只

湿漉漉的目光把晨曦压向枝梢
花骨朵从饱满逐渐走向丰盈,最后的绽开
汁液四溅,天边响起巨大的回声
这时我已经和你并肩走过黑夜的渡口
就 范〔外一首〕
黑骆驼
落日离开了,之后
惆怅,
翻过白色的栅栏
步态轻盈。没有迟疑。
跳将进来
轻松越过沉思的哨卡。
仿佛轻车熟路。
天空合上眼睑,提前去睡了。
暮鼓亦褪去
沉甸甸的衣衫
而他却不肯轻易就范
坚持就是在四周伏满黑暗的床上埋头大睡
挨至午夜
枕头们已经凌乱
床下一只,
怀中一只
还有一只
不知跑哪去了
慢慢地
辽阔的客厅
隐入模糊之域
床的四周
伏满黑暗
他想起一幅图:
“无论你做什么,
都可能是无限汪洋中的一滴水。”
他随手抓住一只枕头
像抓住一团云
铁铸的脸深深地埋了进去
蛰眠记〔外一首〕
白公智
该到蛰眠的时候了。既然
天地不仁,赐给尘世的光明
和温暖,越来越少,越来越冷。
刚刚栖落暮秋的枝头,霜
降于双翅,打湿了生活
飞翔的梦想。而充满张力的
双腿,腾跃于阡陌,田畴,
村院,却被寒露洒落的忧伤滑倒,
重摔一跤,怎么爬也爬不起来。
亲人们纷纷南飞,就连空阔的
天宇也留下道道离殇。而
青春泛黄,枯萎,像一枚枚落叶
飘飘荡荡。人间脸色灰暗,
留白似雪,枝头齐刷刷
举起来,指问偷摘果实的人——
既然天地不仁,我将率领
松鼠,刺猬,蜗牛,黑熊,青蛇……
率领我的臣民掘开大地,埋藏
我们的脉搏和代谢,埋藏
我们的贪欲和暴力,埋藏尘世
所有的奔跑,飞翔,和守望。
然后集体蛰眠。我知道,
也许这一睡,我们将永远沉睡。
也许,会觉醒在春天。
时光划过绿叶
时光划过绿叶,像一阵煦风
在轻轻抚摸。青春润泽,有绸缎柔曼
而高贵质地。灵魂沉睡。梦幻深处,
风吹过,若薄翅律动,绕树三匝——
树立不倒。这群路过的风,
忽冷忽热,像某些人心怀鬼胎,
暗中窥伺并偷走了时光。
绿叶红了脸,灰了心,飘飘悠悠,
拂袖而去——
时光总是在一些事或事物上,留下
记忆的疤痕。需要风,去慢慢抹平。
鸟鸣里跑出老虎
高作苦
河山无立锥,老虎去势急
宽阔的芭蕉叶面,老虎摇三摇
山河动,山势陡,飞鸟从峰顶冲向谷底
其间,有落山风,有跌破的旧时代
老虎转灰色,斑斓不值钱
鸟鸣空山静,一滴滴老虎
从树梢滴落,树顶之上
是行将远游的云彩
老虎即是空用岭南的一万亩杨桃
来换它一次奔跑,用一万次奔跑
来换密林深处,生锈的下一站
老虎发芽,行将被万象吞没
一只只脚印过了江,宽阔的芭蕉叶上了山
幼虎行将归来,天空走近些,再近些
这次看清了,昨夜暴雨,幼虎已被万象推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