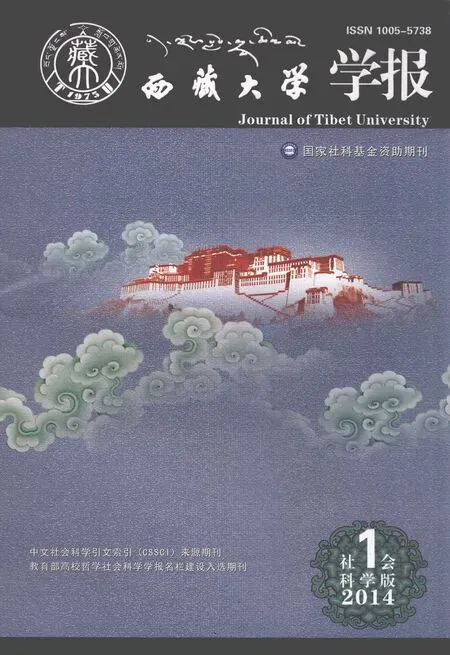西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的文化解读
朱和平胡名芙
(①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株洲 412007②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 江西南昌 330013)
由于历史久远、木质材料难以保存等原因,西藏地区家具的确切起源年代尚无定论,应是与这一地区有人类生活同步。目前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至迟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至5000年左右)就已出现家具,依据有二:其一,家具与人们的定居生活方式关系密切。相关考古资料显示,这一历史时期西藏先民早已告别原始的狩猎生活方式而步入了定居的生活方式,其生产工具较为发达,生活器具制作技艺多样且达到一定水平;其二,家具乃建筑的内部空间延伸,受建筑影响甚大。在房屋建筑方面,卡若文化时期一些木制建筑构件多有出现。
公元6世纪,西藏地区的先民经过数千年的征服与被征服、迁徙、发展、分化及融合,逐渐形成了数十个比较稳定的部落联盟。[1]此后到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特别是一些宫殿的营建促进了家具需求的增加。统一的吐蕃政权建立后,随着民族融合、佛教的传入、经济贸易的频繁,以及宫殿寺庙建筑的大量出现等,为西藏传统家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西藏传统家具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从遗留至今的一些建筑壁画中可窥一斑。吐蕃政权崩溃后近4个世纪,整个藏族文化进入一个缓慢发展时期,藏族传统家具的发展受到影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从元朝始,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社会生产力长足发展,建筑艺术发展日臻成熟,受其影响,西藏传统家具在装饰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征。
一、家具装饰艺术特征
(一)色彩明艳瑰丽
西藏传统家具同其他西藏艺术门类中的唐卡、面具、藏毯等一样,无不呈现出色彩炫丽的艺术效果。缘于地理、生活环境等,藏民族对自然之物固有原色极为推崇,在家具装饰中常保留自然原色,如天之蓝、草之绿、雪之白等。具体而言,西藏传统家具装饰喜好红、绿、蓝、黄、白及黑等色彩,并且常采用多种高纯度、高明度的色彩进行搭配使用,对比强烈,总体呈现色彩明艳、瑰丽的装饰特征,如龙纹藏箱(见图1),这件19世纪末期藏箱装饰的红色、绿色、蓝色等有着高饱和度,且形成了强烈的冷暖对比,此外长方形装饰带形成了高明度的色彩对比。

图1 龙纹藏箱
(二)多样材质融合
西藏气候西北严寒、东南温暖湿润。由于气候干燥和纬度高,可供家具制作的木材十分稀缺和珍贵,仅有少量的杉木、松木、柏木等软木,以及核桃木、樟木、楠木等珍稀硬木[3]。杉木因良好的加工性成为西藏传统家具制作材料的首选,但木质松软,容易腐败,所以在制作家具时,一方面,利用桐油进行表面防腐处理或施以彩绘处理,另一方面,利用不同材质加以装饰,如金属、宝石、兽皮和织锦等。其中金属主要是铜,有时也会使用金、银;宝石主要是松石、珊瑚等;兽皮则主要采用牛皮、虎皮、熊皮及豹皮等。上述主要装饰材质兼具实用功能和装饰,既起到了对家具某些易损部位的加固作用,又收到了审美的效果,其中尤以利用兽皮镶嵌装饰最为明显,这是藏族传统家具标志性的装饰符号。
色彩斑斓的彩料、光泽闪亮的金属、珍贵美丽的宝石和狂野奔放的兽皮,经过能工巧匠精心雕琢和合理搭配后,显得多而不乱、层次有序且独具匠心,同时也使得家具装饰在同一视觉平面内呈现多样化的视觉美感,或自然或亮丽,或浑朴或奢华,不同材质的质感、光泽、肌理得到了充分展现,使得藏族传统家具的装饰以多样化的审美形式共现共存于材质装饰之美中,极具地域性和民族性,如竹编包猴皮藏箱(见图2)。

图2 竹编包猴皮藏箱
(三)纹样寓意多元
寓意是装饰艺术应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纹样的一种形式语言。[4]西藏传统家具将装饰艺术中寓意这一表达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其装饰纹样寓意的多元性为最明显的特质之一。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沉淀而形成的寓意丰富、审美价值独特、文化内涵深刻的特征。从寓意的主题来看呈现多元化特征,大致可划分为崇拜文化主题纹样、宗教文化主题纹样和汉文化吉祥主题纹样。
对于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新唐书·吐蕃上》有如下记载:“多霆、电、风、雹,积雪,盛夏如中国春时,山谷常冰。”艰苦的自然环境激发了藏民族强烈的生存渴望,在长时间的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藏族人民一方面充分发掘和利用自然之物,另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了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如羊、牦牛等既是他们的生活之源,同时也成为其造物的文化因子及审美对象。
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所认为的“图腾是原始人存放灵魂的储蓄器”那样,在西藏本土文化中,崇拜对象可谓包罗万象,有动植物崇拜、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等,就家具装饰纹样寓意而言,动物崇拜的装饰纹样最为典型,其中尤以羊、牦牛、雪狮为最。在苯教流行时期,羊是作为图腾来崇拜的,正如《新唐书·吐蕃上》中所云:“其俗,重鬼右巫,视羝为大神”,藏族人民视羝为大神,认为只有羊才能伴随死者通过充满艰险的死人国到达天国,只有羊才能“遮避”死者的灵魂免遭鬼怪的侵扰。牦牛作为西藏高寒地区特有的动物之一,其性耐寒、耐劳等,有“高原之舟”之称。至今西藏不少地区的藏民仍将牦牛视作神物加以崇拜,把牦牛头骨、牛角作为灵物供奉,把牦牛尸体等当作镇魔驱邪的法物。雪狮在家具装饰中的形象为白如雪的身躯、或蓝或绿的鬃毛,在西藏艺术中被看作是保护神,是圣洁的化身,如彩绘动物纹藏柜(见图3)。

图3 彩绘动物纹藏柜
有关佛教信仰的装饰纹样在西藏传统家具装饰中占据比例最大,主要代表纹样有八瑞相、八瑞物、七政宝、卍字纹、莲花等,其中又以八瑞相使用最为广泛。吉祥结是团结、祥和的象征;妙莲寓意生于尘世,却不为世俗所染;宝伞能够消除众生的贪、嗔、痴、慢、疑之五毒;右旋海螺象征着和平安谧;金轮预示佛法如车轮辗转不停;金幢象征佛法的坚固不衰、战胜邪道、永远的蓬勃发展;宝瓶标志着聚满千万甘露、包罗善业智慧、满足众生愿望;金鱼则象征抛弃无明、智慧无限。[5]
佛教题材装饰纹样的大量使用反映出西藏人民生命观念的蜕变。他们希望通过“普世”的佛教对自身生命加以重视,而不再是让自然“神灵”充满其生命的血液。这代表了一种对人、对命、对世的全新的心境,彰显更为有效的心理、情感和精神的源动力,以此来满足自身多方位的需求。
西藏与中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广泛且深入,从松赞干布开始,便源源不断。文化的交流尽管是潜移默化的,但通过长时期的碰撞、撷纳,西藏的艺术领域逐步认同并再现了某些汉文化的内涵,反映在家具制作中是对汉文化中吉祥纹样的青睐,包括寓意吉祥的龙凤纹、寓意长寿的寿星、鹿、仙鹤、寿字纹,寓意生命繁衍的太极、葫芦以及寓意福气满满的蝙蝠纹、寓意富贵的牡丹纹等等,不一而足。
二、独特审美观产生的原因
上述西藏民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的艺术特征折射出与众不同的审美观,这种颇具民族性、地域性的艺术审美观可以说是藏民族内部“秘语”的外在表现。它们经过千百年的神秘传承,已渗透至民族集体意识的“原始心象”而凝固其中[6]。
一个民族抑或地域的整体审美观的形成与某些重要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7]。独特的自然环境、地域文化和相对封闭的宗教文化空间使得西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形成了独立的审美观念体系,极具地域性和民族性,它深刻地渗入西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集中地体现了雪域高原颇具脱俗意味的世界观、人生哲学和艺术情感等。
(一)就自然环境而言,西藏地处高海拔地区,海拔高度平均从4000米左右至5000米以上。那里气候高寒、空气稀薄洁净、尘埃和水汽含量少,大气透明度高、光照充足,且干湿季分明,温度年变化小日变化大。加上域内江河星罗棋布,冰峰雪岭、冰川冻土广布,使得自然形态五彩缤纷。静态的和变幻莫测的色彩一方面丰富了藏族先民的色彩感知,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对色彩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取向。事实上,红、黄、白、绿、蓝、黑色等彩色都与其明朗、多元色彩环境密切相关。[8]
(二)除多彩的自然环境,西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衍生出独特的艺术审美向度。正如康·格桑益希教授所指出:藏族的传统文化源自生根于藏族古代社会里的苯教文化。苯教是青藏高原史前文明中主要的土著宗教,于公元前5世纪由西藏西部地区古代象雄王子辛饶米沃且(一译辛饶米保)创建。苯教主张“泛神论”,认为自然万物皆有灵,天地、日月、星辰、山水、土石、花草等。这种对万物本体的崇拜既与藏民族对自然的变幻无常难以捉摸的感受有关,更与其对形态和色彩的模仿、运用有关。
在藏族古老的神灵观念中,他们认为白色是神的色彩,东方是白色,苯教认为太阳起于东方,故白色象征光明。[9]另外,天空的蓝色是神圣的、是威严的,为权利的象征,时下西藏僧侣服饰中的坎肩、僧裙、内边等往往采用蓝色。而对于红色的崇敬源于苯教的祭祀仪式,在早期的苯教祭祀仪式中,通常将祭神用的石墩染成红色,以示对神明的敬畏,这种红色涂色的装饰做法也逐渐应用于建筑艺术和家具装饰艺术。再者,苯教创世说中出现的三位“创世人”的色彩特征,长着青绿色头发的什巴桑波奔赤、满身黑光的门巴塞敦那波和青蓝色的曲坚本杰莫,更成为藏民族心目中的神圣色彩而顶礼膜拜!
(三)上述而外,西藏作为藏传佛教的圣地,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除了其精神生活以藏传佛教为宗旨和主旋律以外,其造物和生活方式也莫不围绕宗教信仰而展开,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其佛教信仰。正因如此,藏族传统家具装饰色彩极富藏传佛教寓意和象征性。
在藏传佛教的诸多佛经中,认为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包括在“息”、“增”、“怀”、“伏”这四种范畴之内,分别是温和、发展、权力以及凶狠,而传统西藏建筑中的涂饰用色和这四种范畴一一对应:“息”对应白色,代表温和;“增”对应黄色,代表发展;“怀”对应红色,代表权力;“伏”对应黑色,代表凶狠。[10]另外,藏传佛教常以不同色彩的佛、菩萨等具体形象来传达抽象的教义,其中以白色代表法界体性智,为毗户遮那佛;青色代表大圆镜智,为阿閦佛;金色代表平等性智,为宝生佛;红色代表妙观察智,为阿弥陀佛;绿色代表成所作智,为不空成就佛。另据《药师经》记载: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身色杏黄;观音菩萨身色白;普贤菩萨身色红;大势至菩萨身色绿;虚空藏菩萨身色蓝;地藏菩萨身色黄;除盖障菩萨身色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藏族传统家具中白色的使用最为广泛,占据传统色彩搭配近一半的比例,缘于白色既是圆满状态又是虚无状态,与藏传佛教中的“圆满”、“四大皆空”等教义完美契合。
(四)另外,西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独特的审美观还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对汉文化中吉祥纹样的吸纳,反映了趋利避害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希求,也折射出西藏人民对未来的理想图式,是他们在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持续斗争过程中强大意志力的有力表征,反映出藏民族对现实生活乐观主义的文化心性。同时,吉祥纹样也预示着西藏先民的生命观、生活观的转变,由以往敬神重巫、崇拜宗教的虚拟观念转向现实观念,并逐渐深入藏民族自身的思想、心理、情感及精神世界等,对现实生命、生活也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注释。
繁多的装饰纹样既有理性写实也有感性想象,既充满生活气息也有神秘的宗教色彩,其审美价值呈多元态势,蕴含朴素自然审美、现实的世俗审美和超现实的宗教审美等,具有强烈的视觉辨识度和精神震撼力,带有强烈的地域、民族固有色彩。这一显著的艺术特质是西藏本土文化、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等多元文化相互渗透、激荡、融汇而成的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西藏家具装饰艺术中这种相对稳定的、多元的意象符号系统和文化范式通过造物艺术活动有意识地、自觉地传承至今,它将持续影响到西藏家具未来的发展。
一言以蔽之,藏族传统家具艺术独特的审美观主要受到自然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影响,其审美特征具体表现为融合了以自然为审美主体的“物”性、以宗教为审美主体的“神”性和以世俗世界为审美主体的人性。其一,在人类认知能力相对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等受环境的影响甚大,人们的审美观在感知、模仿借鉴自然到崇拜、再认知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从而自然的“基因”被逐渐注入其中并延续至今。在西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中的色彩、材质、形象均带着明显的自然“天性”,热情、奔放、瑰丽!其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藏族艺术其实就是宗教艺术,西藏传统家具艺术亦是如此。宗教不仅决定着藏民族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价值观,同时也决定其主体审美观,呈现以“神性”为主的审美体系,古老、神秘、庄严甚至诡异。其三,由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西藏家具装饰艺术的审美还呈现一些世俗化的特征,其审美观表现出人性的一面,活泼、生动、亲和。
三、结论
在西藏家具装饰艺术中,自然和宗教是其最为重要的两个文化因子,独特的自然赋予西藏艺术存世于大美,反映出藏族传统家具艺术视万物有灵的艺术心理和崇拜自然的艺术观念,而占据西藏文化核心地位的宗教则赋予西藏艺术存世于大善,反映出其净化心性的艺术追求和关注生命的艺术使命。这种追求大美、大善的艺术精神可以说是藏民族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自由向往的深刻写照。
西藏传统家具艺术具有不重物质而重精神性的艺术气质。这种精神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艺术的主观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它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真实的“神性”,而这种“神性”是独特的西藏文化所赋予的,是人类内心世界通过体悟才能达到的“未来世界”。这种融合大美、大善的西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心理、文化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象,并充分体现了根植于雪域高原藏民族的文化向度和文明成就。
[1]陈庆英.西藏历史[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8.
[2]王孝丽.藏式家具文化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2:31.
[3]Chris Buckley.Tibetan furniture[M].London:Thames&Hudson,2006:2.
[4]李砚祖.装饰之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9.
[5]项江涛.藏族装饰图式及其审美情感模式[J].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7(1):86.
[6]高洁.藏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及风格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09:38.
[7]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71.
[8]余思慧.藏族色彩艺术的外延和内涵研究[J].装饰,2007(11):85.
[9]陈笑鸥.藏族的色彩审美和藏族文化[D].兰州:兰州大学,2007:17.
[10]罗飞,等.解读西藏传统色彩与建筑装饰艺术[J].重庆建筑,2012(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