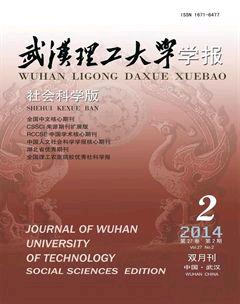重读经典 聚焦“形塑”
何博
摘要:通过考察1998年以来北美戏曲学界明清传奇研究的重要著述及论文,可以发现,在当前文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北美学者依然重视对中国明清传奇经典剧作的重读。他们在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质研究上立足于文本细读的前提下,利用文化诗学“自我形塑”理论,重点探讨文人剧作家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历史时期通过传奇创作来表达主体诉求,确立个体身份,完成自我形塑。
关键词:明清传奇;重读;文化诗学;身份;自我形塑
中图分类号:K207.8; I237.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2.003
从文学批评角度看,“重读”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过去的文本中不断发掘出未为人识的精神内涵。这种潜藏于文本表层之下的精神内涵,恰是使一部作品得以经典化的内在因素,同时其也会引发后世读者的共鸣,从而使得作品自身被一再重读。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英语学界的明清传奇研究呈现出一种新变之态,传奇的文本研究明显“降温”。尽管如此,“戏剧脚本是我们的价值观与过去的价值观间的一座桥梁。我们要欣赏与了解另一时代的种种,非得从其中找出至今仍具有意义的意念与态度不可,否则我们不会受到感动的”[1]。而且就明清传奇而论,无论是文人创作主体还是他们的意向读者群,都有将之作为案头文学来表达和建构自我真实存在的明显趋向。因此,综观新时期的北美明清传奇研究著述,以主题、文体、修辞、互文等文学命题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对象之一的成果仍占据很大比重。
自1998年以来,北美地区中国明清传奇研究专著成果不少,计有史恺悌(Catherine C.Swatek)的《场上〈牡丹亭〉——一部中国戏剧的400年生涯》(Peony Pavilion Onstage:Four Centuries in the Career of a Chinese Drama,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萧丽玲的《过去的永恒呈现:万历年间(1573—1619)戏剧文化中的插图、剧场和阅读》(The Eternal Present of the Past: Illustration, Theatre,and Reading in the Drama Culture of the Wanli Period,Leiden:Brill,2007),蔡九迪的《虚幻的女主角:17世纪中国文学的鬼魂和性别》(The Phantom Heroine: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吕立亭《个人、角色和思想:〈牡丹亭〉和 〈桃花扇〉中的身分》(Persons,Roles,and Minds:Identity in “Peony Pavilion” and “Peach Blossom”, 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2001),马茜的《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妇女:女主人公的剧作》(Wom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er:the Heroine s Play,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5),沈广仁的《中国明代文人戏剧(1368—1644)》(Elite Theatre in Ming China,1368—1644,New York:Routledge,2005),袁书菲(Sophie Vollp)的《世俗的舞台:十七世纪中国戏剧》(Worldly Stage:Theatric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周祖炎的《明末清初文学中的双性混同》(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而北美地区1998至2012年间的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有八篇以明清或晚明清初传奇为研究对象。除了上文提到的吕立亭的博士论文,余者分别为:何赖林的《文化转型与中国历史剧观念:两部清前期剧作的分析》(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inese Idea of a Historical Play:Two Early Ching Plays, 普林斯顿大学1999年),沈静的《传奇戏曲中文学的运用》(The Use of Literature in Chuanqi Drama,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2000年),善思(Dietrich Tschanz)的《清前期戏剧与剧作家吴伟业(1609-1672)》(Early Qing Drama and Dramatic Works of Wu Weiye(1609-1672),普林斯顿大学2002年),何予明的《生产空间:晚明时期的表演文本》(Productive Space: Performance Texts in the Late Ming,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3年),梅春的《“戏”:晚期中华帝国叙事中的表演性和戏剧性》(Playful Theatricals:Performativity and Theatrical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Narrative, 路易斯华盛顿大学2005年),林凌瀚的《情感的内在差异:晚期中华帝国戏剧和小说的外在性探讨》(Emotional Indifference:Exploring Exteri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Drama and Fiction,芝加哥大学2006年)及许桐的《进化的舞台:中国明清时期的戏剧与社会文化转型》(The Evolving Stage:Theater and Soc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2006年)。
在这十余年间,北美地区有关晚明清初传奇研究的期刊或会议论文产量也不少。《亚洲戏剧季刊》、《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等均有不少相关论文。此外,需要特别提及的还有三本论文集。分别是华玮、王瑷玲所编的《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8),华玮主编的《汤显祖与〈牡丹亭〉》(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以及王德威、商伟所编的《王朝的危机与文化更新:从晚明到晚清及其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5)。北美地区在戏曲研究领域卓有成果的学者,如宇文所安、伊维德、奚如谷、王德威、蔡九迪、史恺悌、魏爱莲、李惠仪、袁书菲等均有重要论文囊括在内。
深度阅读上述著作与论文,我们会看到北美戏曲学人对明清传奇的名家名作依然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在西方文学批评“经典论”的影响下,他们尤其热衷于探讨以下问题:晚明清初文人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充满“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的文学环境①这一时期的传奇作家如何在唐人传奇、元人杂剧乃至前代传奇剧作家的影响和压力下进行创新、出奇并力图让自己的作品跻身文学经典之列?他们又如何通过戏剧创作使自身成为经典作家,让后起的诗人奉为典范并对后世产生影响?而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身份(identity)”与“形塑(selffashioning\\selfshaping)”成为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
一、身份意识在明末清初文学领域的凸显
个体的身份问题一直以来是哲学思索的重要命题。一个人在确立其“人”的属性之后,是什么使其成为群体中独特的“那一个”?毋庸置疑,任何人的个体存在都是以人与人关系中的另一方为参照系的。这一理念渗透在中国儒家传统所建构的政治伦理道德体系之中,通过界定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儒家确立了皇权、父权以及夫权的至高无上性。问题是,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是否一旦确立就无可解除?换言之,在什么情况下,隶属关系中处于“从”的一方的个人具有反叛与抗争的合理性?
在上起《牡丹亭》(16世纪末)下至《桃花扇》(17世纪末)的百余年间,身份问题在文学领域凸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17世纪随着商业的繁荣与社会分工的急速细化,中国社会的经济发生剧变,贫富差距、阶级分化程度较之以往更甚。经济的变革对于人的社会文化身份起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比如,晚明社会收藏之风盛行于世,一个人可以用金钱购买到的、收藏在手的东西,代表着他的实力与品味,将其自己从原本低微的社会族群中区分开来。又如,晚明人情放荡,世风侈靡,服饰潮流变换迅速,服饰的功用除了反映人的财富、阶级和品味等之外,还能提供给人在日常生活中假扮的多种可能,借以模糊社会等级及身份差异。而清初对于服饰的“假扮”功能则采取了绝不容忍的政治立场,满清政府以铁的手腕要求男子必须剃发留辫并采取改良满族骑射之服的着装。一部分忠于亡明的汉人选择断头也不剃发,以留发和旧服来确保自己先朝遗民身份。显然,异族统治者深知人的形容服饰的重要性,透过它可以窥见臣民的内心。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对于选择了剃发易服的汉人而言,服饰装扮也许只是一种用以假扮的面具,无法改变他们内心对先朝故国的归属与依恋。吕立亭在《个人、角色与思想:〈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中就指出,明末清初人们对于传奇戏曲的热衷,原因之一是舞台上服装、布景和演员的假扮带来身份变换的可能性,契合了当时格外关注“身份确立”的社会心理②。
在哲学、文学与艺术领域,晚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讴歌人与人性。艺术家们通过书画与文学创作来表达人的本性、童心、真气,哲学家们从形而上的层面鼓吹超越正态的、世俗的、平庸的、乡愿的“真”与“奇”。在袁宏道那里,人有殊癖且终身不易就是真名士;在张岱那里,无癖无疵之人不可交,因为他们没有深情与真气;在李贽那里,人伦关系的基础与前提不是父子而是夫妻,彻底否定了儒家父系社会界说“人之为人”的参照系。凡此种种,都是对千百年以来中国儒家伦理框架对人的身份界定的反驳,更是对程朱理学所鼓吹的以圣人人格为完美人格修养目标的颠覆。满清入关征服中国之后,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与民主思想启蒙的进程上看,是历史的某种倒退。清初的大屠杀、文字狱以及封闭僵化的君主专制体制的强化扼杀了晚明思想界、科学界、艺术界的开放性与活力。江河易主、家国飘零中,汉族文人始终与异族统治者存在着思想感情上的隔阂,这种无法消融的隔阂带来的是他们身份界定的矛盾,对自我存在的真实性产生无法排解的迷惘与焦虑。换言之,对异族的“君”和“国”缺乏认同与归属感的文人,是否有理由采取反抗——无论是自杀殉国,武装抵抗还是拒绝效忠新朝抑或遁隐山林——以界定自我的身份?
二、北美学界对身份与自我形塑的关注
英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强调个性自由比较普遍,在这样的人文思想背景下,北美学人在明清传奇的研究中非常关注的一个词就是“身份”。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开始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觉醒与自我建构,同时社会各种力量对自我的制约与塑形亦发挥强大影响力。文学阐释中的“自我(self)”或者“身份(identity)”实际是历史合力的产物。或者,按照新历史主义学派(New Historicism)代表及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的提出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 1943—)的表述,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是在各种社会能量的碰撞与交流中不断展开的。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形塑理论始于“自我戏剧化”的研究。他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罗利爵士的研究表明,在宫廷权力争斗、与女王的情感关系以及追逐财富的过程中,罗利爵士利用书信、游记和诗歌等文本书写对自我加以戏剧化的张扬与肯定,塑造了自我的文化社会身份。用罗利本人的诗化语言来定义,生活就是一场情感剧,死亡带来的就是剧终的谢幕。格林布拉特对这一“戏剧化自我”的表述进行演绎,进而发展出“自我形塑”理论。他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从莫尔到莎士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中通过对莫尔、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作家的研究,全面展示了自我形塑理论的阐释功能。据此理论,在文本写作中,作家以虚构的人物、事件来演绎自我与他人的复杂关系,表现社会能量之合力对自我的规约以及个体以反抗、颠覆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并完成形塑的过程。换言之,像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剧作家并不是孤独的与世隔绝的天才,而是善于将流通于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文本中的“社会能量”凝聚于戏剧文本的审美客体,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各种利益、信仰、势力派别的复杂关系。作家通过对异己力量的反叛完成自我形塑,同时形成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剧本。这些文学剧本承载着各种社会能量在剧院舞台上上演,作为审美客体供观众消费,其所承载的社会能量又通过观众回流到历史的当下③。
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中,基于对莎士比亚等伟大作家的自我形塑的分析,格林布拉特首度提出“文化诗学”的概念,之后又在其他文章中加以演绎与完善。文化诗学首先将文学文本视为各种社会能量流通与交汇的场所,文学形成于社会历史语境,同时也参与构建社会历史,文学与历史因此是一种互文存在。这种观点使得我们能够“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2]。可以说,文化诗学概括了新历史主义这一正宗当代美国学术流派的研究实践与学术方法论,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如今已经成为北美学术界的一门显学。
三、“自我形塑”理论观照下的经典重读
如果以文化诗学的自我形塑理论来考察晚明清初的文学现象,从宏观上看,传奇的创作、文本呈现以及阅读阐释是一种具有整体综合性的人类文化行为,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内部多种社会能量复杂互动的过程。晚明社会印刷出版业的发达带来纸质文本的大量刊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个人意志得以极大张扬。社会边缘群体被压制的声音得以在文本中倾诉出来。明朝覆亡带来的民族创痛与历史虚无感,清初异族君臣之间难以消除的芥蒂与隔阂,晚明人文思想启蒙余绪与清初儒学复归正统之潮流的抗衡,凡此种种,莫不在传奇戏剧文本中碰撞上演,剧本成为晚明清初特定历史语境中压制与颠覆的张力场。统治上层的权威话语对异己实行同化与打压并举,边缘文人作家则在剧作中塑造反权威的角色,挑战、破环乃至颠覆社会权威与主流话语。不过,这种权力操控与文学颠覆之间往往又会试图达成妥协与平衡。我们因此看到传奇剧本既存在对权威话语权的内在反抗性,又时常表现出向以儒家正典为代表的体制性话语的靠拢。晚明清初时期的文人,如何在互相矛盾与冲突的重重“意义”中确定“身份”、塑造“自我”?又在多大程度上颠覆权威,在多大程度上妥协于主流?他们选择了传奇这一文学体裁作为自我戏剧化及自我形塑的手段。
近年来,在文化诗学的强势渗透下,北美的明清传奇文学研究格外关注剧作家在特定历史文化期的身份确立与自我形塑。他们或显或隐地运用文化诗学的“自我形塑”理论来重读传奇经典剧作,取得了一些颇有新意的创见。
例如,吕立亭在《个人、角色与思想:〈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一书中以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本传奇经典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探索“人何以为人”以及“人何以建构一己之身份”等古老哲学命题的不同方式。人类始终是自我和社会多重塑造的复合体,因此“身份”的概念足以成为跨文化比较研究最基本的主题。在中国这个父权社会内,自古以来人的身份皆以儒家传统伦理关系为参照系。而到了明末清初,社会流动性的显著加强使得个人的自主意识空前高涨,开始以人的感性生命精神特征来确认个体的人。作者以文化诗学为理论框架,从跨文化比较的高度来探讨中国文学对“身份建构”的表征手法与西方的异同[3]。
周祖炎在专著《晚明清初文学中的双性混同》中指出:晚明清初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性别的矛盾含混性(gender ambiguity)。这一现象是商业繁盛、财富剩余、教育扩张、印刷出版业的兴盛、个人意识增长、享乐主义盛行、主情思潮高涨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政治上官场腐败与朋党斗争日益加剧,动摇了儒家传统的父系等级结构。尽管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内心深处仍难以割舍儒家大丈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但无法改变的现实是其政治上的边缘化和精神上的疏离感,用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阴性化”(feminize)。这种社会性别属性上的含混性从本质上说就是对社会身份的把握不定。明末清初文学中的双性混同现象由此而生。具体说来,科举失意的儒生、离经叛道的文人异端、宦场沉浮的官员、与满清异族统治者隔阂难消的亡明遗民(或者具有遗民思想的人),因为其地位的边缘化而导致传统社会角色身份的异化。他们对那些具有双性混同人格特质的女性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在后者身上,男性文人仿佛看到了镜中的自我影像:后者如男性般坚毅不屈的气质(masculinity)与现实中作为女性被边缘化的地位似乎映照出作家本人双性混同的模糊身份。因之,在小说与戏曲中,文人作家心有戚戚,创造出双性混同的角色,或观照社会的非常态,或进行自我塑形[4]。
又如,在《魂旦: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一书中,蔡九迪高屋建瓴,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域来观照17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鬼魂的“形塑”问题。 此书的第四章集中探讨女性游魂如何在晚明清初的传奇创作中被表征与概念化,如何被移译为戏剧性的书面表述和演剧性的舞台表演,如何艺术地实现女性鬼魂在舞台上隐蔽性与能见度的统一,从而体现戏剧的价值观。如以自我形塑理论来考察,对女性亡灵的塑形无疑也是文人在主情观与政治专制、社会权威的激烈冲突中自身戏剧化的表达。此书《尾声》部分以《长生殿》的魂旦戏为个案,全面而深入地剖析了杨玉环的自我形塑。蔡九迪认为全剧后半部实际展示了杨玉环灵魂的自我救赎过程,反映她如何在沉沦中复归本真的“我”。女主角从“故吾失久”到“形神忽地重圆就”的转化,其实也就是在对异己的反抗中构建自我真实存在的过程。当然,此语境中的异己,更多的指向海德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常人之存在。而女主角救赎的成功(即自我形塑的完成)也恰是洪昇本人“情至”的理想诉求的文学表达,换言之,即为作家的自我造型[5]。
沈静的博士论文《传奇戏曲中文学的运用》运用互文理论(intertextuality),细读三组六部明清传奇戏曲作品,包括汤显祖《紫钗记》和梅鼎祚(1549—1615)的《玉合记》,吴炳(1595—1648)的《绿牡丹》和李渔(1611—1680)的《风筝误》,以及李渔的《比目鱼》和孔尚任 (1648—1718)的《桃花扇》,分析了明清传奇的内在互文性和剧作家作为创造性阐释主体的“重写”实践,以及传奇意象读者群的文学能力之于创造性阅读的重要性。论文第一编着重探讨眀传奇对唐传奇小说的重写,指出这种重写实际是传奇剧作家自我身份的建构;第二编着眼于传奇戏曲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考察剧作家如何运用中国诗学传统来建构剧中人物的主体性;第三编考察清初传奇戏曲中的“戏中戏”,探讨了传奇前文本如何在本文中得以“语境化”,而这一语境化过程又折射出戏剧如何参与建构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总体而论,作者认为传奇以其汪洋恣意、天马行空的虚构性成为精英文人自我表达(selfinterpretation)、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的语言。通过这种文学语言,个人意志自由与公共职能/政治使命之间的紧张对峙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融。汤显祖、梅鼎祚等对唐传奇的戏剧改写反映出精英文人在官僚强权政治对其个人与政治命运操控下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与张扬。汤、梅所代表的文化精英阶层“自我”形塑的力量既来自于各种外部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制与颠覆,也源于自身内在的政治理想、情感价值取向、心理诉求、文化知识结构的呼应与外向扩张。剧作家的“自我”或者“身份”最终在与异己和权威的冲突对立中完成塑造。在分析晚明吴炳的《绿牡丹》与清初李渔的《风筝误》时,沈静具体考察两部作品如何运用中国诗学传统的审美文化因子去完成剧中人的身份构建,这一构建过程实际体现了文人剧作家对把握“自我形塑”文学话语权的特殊自豪感[6]。
善思的博士论文《清前期戏剧与剧作家吴伟业(1609—1672)》选择清前期杰出的学者兼诗人吴伟业(1609—1672)的三部戏曲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包括杂剧《临春阁》(作于1645—1647年之间)、《通天台》(约作于1649年)和传奇《秣陵春》(出版于1653年)。作者认为吴伟业的传奇创作与诗文创作一样,聚焦于山河易主、朝代更迭的历史动荡期中个人所面临的选择困境,其文学创作实际上可以称之为作家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7]。
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牡丹亭〉在〈桃花扇〉中的回归》,通过细读《牡丹亭·闺塾》与《桃花扇·传歌》,剖析了学生学习儒家经典与歌妓/演员学习戏曲唱段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认为杜丽娘与李香君都学到了本不应该学到的东西:前者基于天然与本性,对“关雎”作出了与新儒家道学主义完全相悖的理解与阐释,被内化为自我的至情追求;后者一往情深,学习如何做一个痴情贞洁的浪漫女主角,而不仅仅是台上扮演一个浪漫女主角的“旦”。在汤显祖那里,幻象是和现实一样的真实,杜丽娘凭借意志力,借助杜宝及端坐父权社会宝座的皇帝,最终使幻象成为真实。而在孔尚任那里,李香君对杜丽娘的学习、模仿至多只能如真,最后在《牡丹亭》中帮助幻象成真的父权社会现实摧毁了她的梦想,她的学习是一种充满了局限性和悲剧反讽意味的学习。作者认为《桃花扇》从第一出戏开始,阶级问题或者社会身份问题就已经暴露在真与假、士大夫阶层与隶属社会末流的演员的倒置之中,剧作家以此提醒我们:梦想的实现是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李香君对《牡丹亭》内化的学习注定只能是一个被赋予了阶级色彩的梦想——学习与阶级身份紧密相连,她梦想由“学”达至另一个阶级身份所属的世界,最终这种自我形塑的努力遭遇悲剧性的破灭[8]。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史凯悌的《论两部冯小青戏曲对〈牡丹亭〉的拈借》,从刊印于1628年的《春波影》与《风流院》两出传奇与《牡丹亭》之间至关重要的互文关联性入手,认为二者是《牡丹亭》原文本(pretext)的后续文本(posttext)。两出戏的作者都颇具兴味地改变了汤显祖创造的在美学上偏离传统的超前女性形象,使之更符合传统的表达形态。同时作者认为二者均毫不掩饰地将剧作作为自我戏剧化的表达手段,明朝的衰落伴随政治与社会的剧烈动荡,文人以小说戏曲自况成为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并持续到18世纪,反映出他们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对乖舛命运和边缘身份的焦灼心态[9]。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以现代的、西化的方式来研究古老的、东方的对象,往往难以避免认识的误区与方法的隔膜。笔者以为,北美学者沉潜于传奇戏曲的文本本身,同时又在整体上运用了文化诗学的方法论,故而能将深入文本内部肌理的细读与驰骋文本之外的宏阔历史文化语境考察较好地结合起来。他们努力挖掘经典文本所蕴含的时代文化精神以及所折射的作家主体精神诉求,使得经典的重读历久弥新,其重读所获得的洞见以及不可避免产生的某些误读都对国内学者具有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中,海外戏曲学人依然能够坚守文学之为文学的本体特征,重视传奇经典的文本细读。他们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国内学者拨开宏大叙事的理论迷雾,通过文学性解读以达到对社会性的认识,从而避免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对文学性的异化。
注释:
① “影响的焦虑”由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首先提出,他认为所有作者都在前代作家的影响与压力下对其进行挑战并力图创新。参见布鲁姆的著作《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② 参见吕立亭的《个人、角色与思想:〈牡丹亭〉与〈桃花扇〉中的身份》一书的引言部分。
③参阅Greenblatt,J.Stephen.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此外,有关文化诗学的理论主张还可参阅陶水平的《文学 “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 ——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文,载于《江汉论坛》2007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布罗凯特.世界戏剧艺术欣赏——世界戏剧史[M].胡耀恒,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56.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外国文学所.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80.
[3]Lu,Tina.Persons,Roles,and Minds:Identity in Peony Pavilion and Peach Blossom Fan[M].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4]Zhou,Zuyan.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M].Honolun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5]Zeitlin,Judith T.The Phantom Heroine:Ghost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
[6]Shen, Jin. The Use of Literature in Chuanqi Drama[M].St.Louis: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0.
[7]Dietrich,Tschanz. Early Qing Drama and the Dramatic Works of Wu Weiye (1609—1672)[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2002.
[8]宇文所安.《牡丹亭》在《桃花扇》中的回归[M]∥华玮.汤显祖与《牡丹亭》.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5:497510.
[9]史凯悌.论两部冯小青戏曲对《牡丹亭》的拈借[M]∥华玮.汤显祖与《牡丹亭》.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5:537589.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A survey into the books,dissertations as well as papers on Ming and Qing Chuanqi studies by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since 1998 reveals that,despite a current “cultural shift” in literary studies,rereading the classic Chuanqi plays still remains a hot spot. Insisting on the tradition of close reading established by New Criticism,scholars in North America now apply in their studies the theory of self fashioning proposed by Cultural Poetics and hence,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how the literati playwrigh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resolved to assert themselves,establish their self identity and finally accomplish selffashioning.
Key words:Chuanqi Drama;rereading; cultural poetics;identity; selffashio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