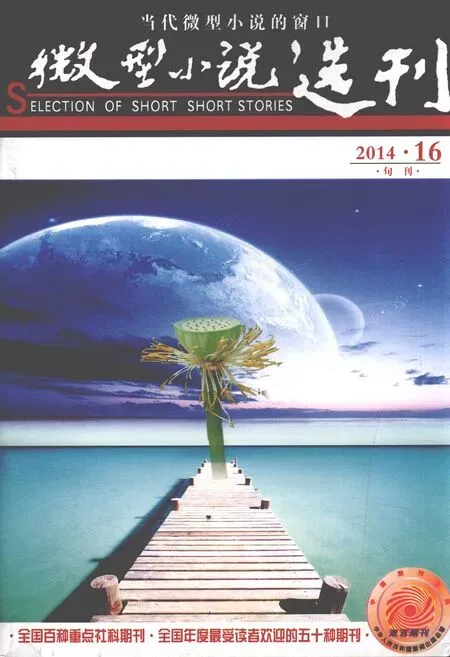掖庭木
□周月霞
掖庭木
□周月霞

当我被运进汉宫的时候,以为马上就可以见到她了。而我被工匠们砍了锯了刨了削了修了,一层层涂满桐油明漆置于掖庭院正堂屋顶的那一刻,我绝望了。
我和她曾是紧紧依傍的两棵树。我唤她槐儿,她唤我榆儿,我们共经四季轮回,守望着种下我们的赵姓人家世代繁衍,简单、快乐、幸福。
五十年前,一个雨天,有个俊朗少年避雨来到我们身边,惊赞她秀美的伞盖、腰身,把一对银指环套在槐儿的臂上。他走后,槐儿就像丢了魂似的,总是昂着美丽的脸望着远方发呆,不久,就慢慢枯死。
从此,我只能孤单地经过四季轮回重复着思念的煎熬,等待她的魂兮归来。
她转世做了赵家的女儿,据说,一落生就双手紧握不能伸开,却只要从窗外看到我就咯咯笑个不停。
我很满足了,只要她快乐幸福。直到那天,六十五岁的武帝在我的眼皮底下,就那么轻轻一捋,她十五年从没伸开的手就倏然展开,手心里竟是那个俊朗少年套于她臂上的银指环!我和她同时惊呼一声,她一头扑进武帝的怀抱,我知道我将彻底失去她了!我痛哭失声,满身碧绿的叶子一夜落尽。
她被武帝华盖彩车迎进皇宫,再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变成一根光滑的、面无表情的掖庭梁木时,却终于见到了她。
她的娥眉,她的粉腮,她水汪的眸,如瀑的乌发,依旧。
我激动得浑身发抖,低声轻唤:槐儿……
她轻扬玉腕,一袭白绫便绕住了我。她昂起梨花带雨的脸直愣愣地呆望着我,满眼茫然。我知道她早已忘却前世的一切,当然包括她的名字。
“槐儿!”我再次轻唤。
“告诉我,你怎么会来到掖庭局?重复许多女人无奈的、我极其憎恶却无可奈何的动作?”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一切。
她的纤纤玉指系紧白绫狠狠打了个结,我的脖子便被箍得喘不过气来。我呼吸急促,声嘶力竭地喊:槐儿,不要!快松开!还好,她好似听到我的祈求,开始哆嗦着解那个结。
窗外,是风呜咽吗?
门口的风铃在互相撞击发出声声犀利怪叫。寂静的院落里,跪满了鸦雀无声的太监和宫女。风吹动他们帽上的飘带在暗黑的夜色里愈发诡异阴森。
门被缓缓推开。
她抹掉脸上的泪,鸟儿一样飞奔过去。
“江充!大王怎么说,大王改变主意了吧?他只是玩笑吧?”江充慌张地往门口闪躲着身子。白绫的影子在烛光里闪动在他的脸上,狰狞恐怖。
“大王主意已定,不会更改的。娘娘,你就……”江充深深弓下身子抱拳作揖,抬眼看向我。
“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正在替他束发整衣,小心翼翼。因为我拔掉了他的白发吗?因为拔的时候弄疼了他?”她止不住抽泣,嘤嘤哭诉。
“大王要立弗陵为太子……这是汉宫的祖训:子立母死……大王一直用宽大的袍袖遮住脸,大王其实很不舍……”
江充直挺挺跪在了她的脚下。
她将头颅探进白绫,仰起脸凝视着我。
我闭上眼,跟着她一起战栗。
她喃喃自语:大王曾是那么疼惜我,那么宠爱我,竟也是那么狠心……她的泪一串串滑下来,落到我的脚下。
而我,却变成一根光滑的、面无表情的掖庭之木。年复一年的桐油明漆,虽让槐儿想不起来我原先的样子,但我却不能做弑杀她的凶手。
她腾空的一刹,我伸出手臂,用尽平生所有气力把她拦腰抱起,冲破掖庭正堂的屋瓦,飞天而去。
那晚,长安城狂风大作,黄沙漫天,人们的眼睛无法视物,掖庭院里中堂大殿轰然倒塌,整座后宫笼罩在一片烟霭里。
七十五岁的武帝摇晃着苍老的头颅,苍老的脸飞淌着浑浊的泪。六岁的弗陵挣脱开太监宫人,冲过来跪倒在他面前不住哭啼:母亲,母亲,我要母亲……
不久,武帝驾崩,传位弗陵为宣帝。宣帝废弃掖庭局,为其母修建陵园,却遍寻不到母亲的遗体,只好做衣冠冢。
多年后,陵园里无种无根地生了两株紧紧依傍的参天大树,一槐一榆。
(原载《山东文学》2014年第3期 边际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