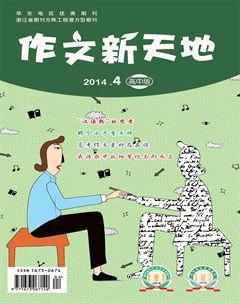我诗歌中的细节化与形而上
《胡不归》是我的第三部作品,诗歌创作生命中的第三张底片。两年,七十余首诗,写得不算快,但都是我和自己拥抱、抗争、打碎又和解的果实,是我内心悄悄爆发的、不为人知的战争与和平。
在写作的最初阶段,我对一些琐碎、日常的庸俗化描写保持着警惕之心。但我又希望,自己在寻找形而上的出口时,诗歌中会有丰富的生命细节、活泼的现场作为根基与铺垫。为了完成这个预设,我走过一些弯路,也曾经有人说我那时写的诗歌艰涩难懂。这或许是我在把握及物性与形而上时,错失了平衡点,在我最开始的诗歌创作中,我更倾向于表达“为什么,要去向哪里”,而冲淡了“是什么”。我想一步跨栏,直接到达终点。
那是危险的,从简单的经验出发急切地去追问形而上的意义。我曾以为那是对过度执着于琐碎、物化的文学风气的一种反抗,是对最高可能性的靠近。
所以当我开始着手写这部《胡不归》,我作了调整,返回到纷繁又有生命力的细节中,回到我失去山水梦的江南,回到我日渐成熟的母性情怀中,重新接受它们的照耀和捶打。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对语言一如既往的坚持。语言,是诗歌的本质。我沉醉于语言世界,并试图控制它。节奏的适切、用词的准确,我一遍遍地读,吹毛求疵地读,孜孜以求地寻找那最独特的一个,这大概可以称为戴着脚镣跳舞了。我相信,语言是一个活体。它有色有味,有节奏,有张力,会用自己的生命,铺垫出深度、广度以及一个不断扩张的空间。我固执地坚持,要写出好诗,一是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独创程度,一是文本揭示生命体验的深度和复杂性。
我用十年的时间把玩和训练语言,这十年,我从二十四岁变成了三十四岁,但最难的攀登还在后头,就是寻找文本在提示生命秘密中的力量。
我开始着手写这部《胡不归》是在2011年,我唤它为“胡不归”,源自于“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古老乡愁。我的意图是它不仅仅被注解成乡愁,而且被理解为反复呼唤的声音,它呼唤无数被追忆的过往、无法得到的完美与优雅以及注定要缺口的完满。是死对生的乡愁,遗忘对思恋的乡愁,凋零对绽放的乡愁,是一切的“我们回不去了”以及平静的追忆。我希望它从一开始就有这样广义的格调——它来自于烟火缭绕的现实,又暗暗发问——当时光流逝,我无法企及的,你为什么不回来?我希望这个发问既来自于现实悲喜,又是对灵魂的深度检阅。
在这部诗集里,我分了《死生集》《长相忆》《如梦令》《悲欣集》《寻江南》等篇章。第一辑是《死生集》,《银簪》这首诗其实讲的是一个故事,容纳的是我的个人经验,在村中开发山林时,父亲为太祖母迁坟,打开时,发现棺内除了一支簪子,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就把这只簪子当成她,落户到新坟。就是这个迁坟事件让我想要借此表现生命与美的关系,以及人在物面前的挫败感。
一百年前,她戴过它
一个陪嫁。在她的头顶
树绿过,花谢过
一只燕子和她一起
把一只巢的理想和苦涩
折叠在胸前……
此刻,棺内空空
骨肉消逝,衣袍化灰
只有这支银簪留下来
在一个角落
记住了她鬓角最美的位置
我平静地在想象中追忆,强化叙事性,追溯历史,极力追求细节化,从她的家园理想写到经历的战火,我运用细节连缀她的一生,并将这些都幻化成银簪上的花纹,我企图通过个性化的体验写出一个女性花开花落的普遍经验。《一本书上的两个名字》用对死亡的想象完成爱情的建构,这两个曾经相爱的名字在我细节化的陈述里变成两朵落花、两条小船,最后是两座青山上眺望对方的坟头——
是两座青山
第一页,略高处是我
翻过去,就是你
一个山头
高一点,越过密密麻麻的孤坟
看着另一座山头
这首诗虽然涉及了死亡,我却用尽了温暖的意象,并让它们拥有自身的运动和生命,为了表达我对爱情的理解,我选择的最后一个意象是死,并借此获得情感上的升华和诗歌结构上的高潮。但死的意象在这里不是绝望的符号,而是青山绿水间永远的眺望和想念。《黎明》这首诗写成于江南一个秋日的清晨五点,那时世界还处于沉睡之中,但在我耳旁清晰地响起了两种声音,一种是鸟的鸣叫,一种是丧乐的演奏。而我就处于这两种声音的对峙与融合之中。这样的诗歌很容易变成哲学思想的生硬解读。所以我很谨慎地把两种声音场景化,用细节质感的纹理,完成由听觉到视觉的转化——“每一天,都有一只鸟叫着……遗弃自己的名字,为相似的晨光/唱同样的歌//不远处,出丧的队伍/被长号和鼓声带领着/正牵引死者重温故土/亲人们发出准备好的哭泣/像沿路种植的银桂/一阵风过,就洒了一地”。
在另一个篇章《长相忆》的十五首诗歌中,我写作的基点是爱情。毫无疑问,它们是我相当珍视的一部分创作,来自于我的生活,与我同患难、共荣辱,成为我血液中最真实的那部分,并直达心脏。但是,爱情并不是我所要到达的唯一终点。它只是一个发端,那些试图通过爱展开的内容,比如个体命运、两性关系、现代人的孤独感、生命价值等,一直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在近作《每当我说起大海》中,我继续坚持着诗歌细节化与形而上的微妙运动,我写到别离——“你转身离去。一条鱼,游回海底/把灯熄灭,闭上双眼/我宛在海中央,变成独木之舟/顺水飘零,无人注意”,把两性关系铺叙成鱼和孤舟的画面,“我擅长波澜不惊,在所有无法抵达的地方/用文字与你重新相遇/一句句,上有惊涛拍岸,下有鱼翔浅底”,惊涛拍岸与鱼翔浅底是相忆与交融的细节;我写两性的隔阂——“若我纵身入海,也不过是变成一束水草/长在你游过的地方,容你短暂栖息/不会是另一条鱼。我的假想敌/对你唱:若你占海为王/我便有变幻迷离的身体”。我用一尾鱼的形象,构建与大海、水草、另一条鱼的关系,构建一个寓言化的两性世界的缩影,抒情主体“一束水草”塑造的是局外人的形象,那样的相思相恋所起的作用竟只是“容你短暂栖息”,现代人的间离与陌生感,我渴望表现的生存之痛,在语言的跳动中自然而然地流泻而出,整首诗就疼了起来。
在《如梦令》这个篇章中,我展示的是各种女性命运,有沉迷于泥塑的女雕塑家、半夜约会却不是因为爱情的女网友、一个正在哭泣却无人安慰的四十岁女人、一个患病的母亲。我是以小说的建构在完成这个篇章,我寻找着体现她们不同精神气质的细节,试图以形而上的视角回归日常生活领域,描写我所遭遇的各种女性的现实,描写她们的苦难,以及对于苦难的惊人的忍受能力。苦难是人类的生存本质。当我在用文本描写苦难时,这些小人物身上闪现的温情的光芒和人性的光彩,更加熠熠生辉。如果我这个微小的旁证,能作为时代的注脚,那么我与文字的联姻就达到了预期目的。
我觉得最好的写作就是左手拿着镜子,照见自己和别人,右手拿着刀,剖析人性和命运。我的写作,是一只蚂蚁为一群蚂蚁写的传记,是平等的生命的握手。
我希望自己的诗歌从自我出发,能因为精确的细节越来越具有扑向大地的深沉力量,我手中的语言,能因为我对精神高度的追求,变成一支箭,射到哪里,哪里就流血。
作家简介
钱利娜,1979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出版诗集《离开》《我的丝竹是疼痛》《胡不归》,获《人民文学》新人奖、浙江省优秀青年作品奖等,现就职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文联。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