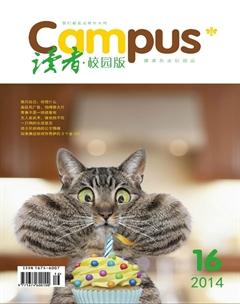给你讲个笑话,你别哭啊
囧叔
“嗨,给你讲个笑话,你别哭啊,就算不好笑也别哭。”
这是我妈在讲那个笑话之前的心理活动写照,我猜的。我妈年轻的时候没怎么读过书,不是文青,不那么细腻。很多凄惨的事情她都面不改色地当笑话讲了。这一点都不奇怪,有些人天生粗线条,总是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而不自知,其实他们是善良的。高中时我有个哥们儿,特别憨厚老实。毕业前我俩坐在马路牙子上喝黑加仑(其实是他毕业,我留级了),他说:“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接着他说:“昨天她来了。”他喜欢一个附近学校的女生,是个假小子,学校女子篮球队友谊赛的时候来过,他一眼就喜欢上了。他说:“我在楼道里遇见她,她来找我们校队的女生约暑假的比赛,我一咬牙,就鼓起勇气说:‘你放学能不能等我一下?结果那女孩一笑,说:‘好啊,我一会儿来找你。你在教室等着吧!”
“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一拍我后背,自顾自地憨憨笑起来。一阵“呵呵”后,他说:“结果,老子就在教室傻等。一会儿就听见楼道里哗啦一声巨响。老子一个箭步冲出门一看,楼道的卷帘门关了!然后老子就在教室过了一夜,哈哈哈……”
“这根本不是一个笑话。”我生气地说。一个18岁的男孩,就因为喜欢的女孩子随便说了一句,就在教室等了一个晚上。当时同样18岁的我觉得这事儿一点也不好笑。我都快哭了,但又没有哭的理由。不过现在想起来,这确实只是个笑话。谁的青春没有傻过呢?
当然,我妈讲的笑话比这个水平高多了,毕竟是有60年阅历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把那些惨绝人寰的事情当笑话讲。而且我看得出来,这样的人在这么做的时候,是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没什么。他们就算中了一枪,大概都能当笑话在临死前讲一遍。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高中同学来找我玩,就讲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嘿,”他见面先拥抱了我一下,跟熊一样有力,“给你瞧个新鲜的!”
他伸出右手,张开五指。小指的形状很奇怪:最后一个关节向一旁微微扭曲着,怎么也伸不直。看上去确实有点好笑,但又有些狰狞。
“怎么弄的?”
“打架弄的。”他说,“被人按在铁栅栏上拿桌子腿砸的。”
说完,他“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但是哥们儿后来把他们都干翻了。哥们儿当时还以为能演《新上海滩》了。”
笑话真冷。我很想说:“你这算残废了你知道吗?”这个朋友好久没有见面了,只是偶尔打个电话。不知道他的手指是不是一直都这样。他是为了女朋友打架的,而现在女朋友当然早就换人了。
我妈讲完笑话,我立即想到了这两个朋友。水平固然差得远,但性质差不多:他伤害了你,还一笑而过。他们不是故意要伤害你,而是神经比较大条。
我妈是在看《知青》的时候讲她的笑话的。电视里,一个返城知青坐大巴去探亲,把大衣忘在车上了,车上一位姑娘在长途车站苦等。
“你知道吗?”我妈拿出惯用的民间故事开头,她正在嚼提子干,“我插队的时候,你姥姥干过一件特别可笑的事儿。”
我妈是笑点特别低的那种人。她给你讲一个笑话,还没讲完呢,自己得先乐一会儿。“咯咯咯”乐完,她接着说:
“那年我正在内蒙古插队呢,你姥姥啊,有一天想我想得不行了,也不知怎么就干出那么件事儿来。”(笑)“她也没跟家里人说,就跑到长途汽车站去,先在那儿站了半天,不知道想干吗,然后突然开始见人就问:‘内蒙古的车来了吗?今天有没有内蒙古来的车呀?你们知道内蒙古的车什么时候来吗?你说你姥姥是不是精神不正常?”
讲完,她嚼着提子干,没事儿人一样轻松地笑着。
我当时特别想骂娘,可惜她就是我娘,不知道怎么骂。我看了看我爹,他一副已经30多年了习惯了的表情,淡定地嚼着花生米。我又看了看我妈,她用30多年养成的固定的频率嚼着提子干。
看着她的侧脸,我发现我好像有二十几年没仔细看过她了。她才60岁,竟然长出一个提子干形的老年斑来。我一下子就想起一个笑话。小时候我爸我妈两地分居,我跟我爸在保定上学,寒暑假回家,开学前回保定。有一次开学前,我爸带着我进火车站,我“哇”地哭了。“我要我妈!我要我妈!”我不停地喊,不让我妈走。我妈特抠门儿,从来不买站台票。她在栅栏外面,攥着栅栏,脸贴着铁棍,使劲喊着跟我说:“妈不走,妈一直在这儿呢,你放寒假回来,一下车妈就在这儿呢。”
哈哈哈哈哈!这个笑话好笑吗?我看着提子干形的老年斑默默地咬牙切齿。但我不忍心把这个笑话讲出来。
我妈看电视的姿态过于淡定,好像刚刚讲的是一件别人生命中不值一提的、有点可笑的小事儿。她好像一面墙,墙内风起云涌六十载,墙外风平浪静一瞬间。独有一枚提子干形的老年斑在那里,让我浮想联翩。那一瞬间我简直是弗吉尼亚·伍尔芙。
“你才精神不正常。”我默念着。我要哭了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