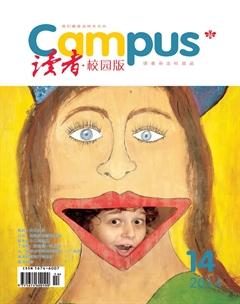童年的光晕
赵霞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读的村小来了一位年轻的代课女教师。印象中,这位老师并不真的代课,主要是代管。逢到哪个班的体育课排不出教师来上,她就会出现在这个班的教室里。但她并不是来代上体育课的。她的手边夹了一册连环画,用来给学生们读故事,以此实行代管的职责。那时全校其他4位老师上课多用方言,代课老师据说讲一口普通话,这在我们听来也颇为稀奇。
有关代课老师的传说很快在小校园里散播开来,尤其是夹在她手中的那本小人书,让总在渴盼故事而不得的我们感到了天大的新奇和迫不及待。那时,全校仅有的一柜故事书被锁在唯一的一个办公室里,一个礼拜才有一次开放阅读的机会。现在,原本井井有条的学习时间里,忽然多出了一个与故事有关的悬念和涟漪,我们的兴奋之情简直无法形容。终于盼到体育课的时间了,进来上课的却总不是代课老师,我们的盼望于是在一次次的失望中逐渐暗淡下去。
就在一个没有期待的下午,代课老师夹着一本连环画走进来,坐到了讲桌的后面。
我后来记不清代课老师长什么样,也忘记了她说的普通话,但我至今记得那天下午讲的是一个“密林剿匪”的故事。三年级的学生不懂什么叫“剿”,但明白“匪”必定是坏的。既有“密林”又有“坏蛋”,这一切勾起了我们对于故事的强烈好奇。耳听到少年主人公在黑暗里小心地拾级而上,“突然——”我们顿觉脖子上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原来,“他的手触到了一只脚”。
这只“脚”在我童年时代的想象世界里占据了长久的位置。我们家的那一架木楼梯,成为我无数个黄昏跋涉于其上,惴惴地想象和回味这段惊险情节的地方。我后来知道,这样的剿匪故事在那个时候多如牛毛且易于炮制,但在童年对于故事的渴望远不曾被填饱的年代,正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连环画故事,成为我记忆深处不曾熄灭过的与阅读有关的光亮片段之一。
另一个片段与一份儿童刊物有关。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外祖父为我订阅了上海的《少年文艺》杂志。此后每月刊物即将寄抵的那几天,对我来说往往伴随着过节般的企盼和愉悦。某一天放晚学归来,从进门的小桌上看到新印的一册《少年文艺》,恍惚觉得接下去的几个礼拜的时光都变得格外明亮和鲜艳起来。功课完成之后捧起书来,又想一气读完,又怕读得太快,透支了阅读的欢乐,常常是读到酣畅处狠狠心合上,第二日傍晚再接着读。等到一册读完,起初的几篇已经隔了些时日,重读起来又有了新的滋味。及至书桌上已积起若干册了,便可以把往期刊物中格外钟爱的篇目再拿来反刍充饥。这样反复着,一个月的时日很快便度完了,接着就又有了新的盼头。那时我小小的书架上排有这份刊物的那个角落的色彩和模样,迄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此后许多年间,每当我与钟爱的书籍相遇的时候,还恍惚闻到从这个角落里散发出来的那样一种芬芳而又美好的气味。
我后来常常想,在童年时代,这种对于阅读的光亮和气息的感受或许比阅读内容本身更为重要。它所培育起来的那份对阅读的珍惜和爱慕之情,比许多书籍的内容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内心深处对于阅读的态度;它所带来的那种因一件简单的物事而生的对于生活的幸福感受,也更久远地滋润着童年心灵的旷野。我说不出这种感受究竟从何而来,但是回想起来,如果童年时代对于阅读的饥渴可以得到随心所欲的满足,这样一份阅读的光亮感,或许早已随着经验的轻易重叠而消磨黯淡了。
或者,童年时期的阅读与吃的道理是一样的。“饱食”的状态总是难以激发起我们对于食物最深切的渴念和想象,更进一步说,食物本身的充盈也会削弱我们对它的热情。我想起少年的时候,一度迷恋武侠小说而不得,偶尔辗转借得一套,轮到自己手中,离限期已只剩一两日。这时不但白日里狂读,夜里也掌起灯来“用功”。后来进城做客,同样有此癖好的舅舅领我到租书摊前,许我随意挑拣,我才狂喜般获知世上竟还有如此丰足的书里刀光剑影。在舅舅家小住了几回,每回都是租一堆金庸或古龙所著的书“饱食而归”。但不知怎的,当我得以恣意索取这些书籍的时候,我看待它们的态度却越来越随意起来,早先的阅读热情迅速凋敝,对于这件事情以及与此相连的时光的珍爱之情也逐渐减淡。记得最后一次退还租书时,忽然感到一瞬间莫名的百无聊赖,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类似的书摊。
事实是,一种珍惜的情感总是与某种程度上的匮乏联系在一起。我们或许难以否认,正是故事的匮乏,使得许多童年时代的阅读保持着本雅明所说的那种“光晕”感,后者也成为童年生活光晕的一部分。今天,当源源不断的故事被市场轻易奉送到童年面前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许多孩子面对故事变得倦怠和不情愿起来;而这种倦怠和不情愿,也在消蚀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情。
阅读是如此,那么其他呢?
我有时候想,今天童年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或许都可以归因于“少”的匮乏。这个“少”并非指物质或精神上的剥夺,而是一种与“少”相连的珍贵、美好的童年生存感受。在一个物质和精神生活总体上空前富足的时代,儿童生活体验的幸福度却似乎在持续下降,这里面留待我们去探询的问题,也许不是如何急于制造和满足孩子更多的要求,而是如何使这种满足对童年来说,能够真正成为一种幸福。毫无疑问,近一个世纪社会生活的提升,带给童年的福利是任何过去的时代都难以比拟的,但这不妨碍我们追问,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谁能把童年的光晕还给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