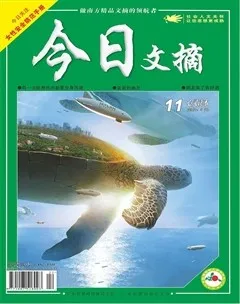流亡者
去年国庆,我回了一趟老家,参加博士生表姐的结婚典礼。表姐的婚礼摆了88桌,近一千人,我得以见到许多一百年没打过交道的亲戚。不用我喊出姨奶表舅的称呼,对方的热情已经扑面而来。“从上海回来啦?结婚了吗?有对象了吗?怎么还不结婚?在哪儿工作?”面对这种汹涌而来的关心和侵犯,我实在招架无能。
“她一天到晚还稀里糊涂的,赚钱能糊口就行了,我们也不指望她有什么出息。你家孩子怎么样?我听说去电力局上班了?电力系统好……”我妈瞪我一眼,轻松地就把话题引到了对方最得意的领域,我只需要在一旁听那位亲戚表扬她的儿子就好了。
百无聊赖地四处扫视,忽然对上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女孩的面孔有些熟悉,见我终于注意到她,弯了眼睛,狡黠地一笑。
是小宛。
我认识小宛是在2000年的夏天。那年,我的小学毕业典礼因为我和班主任糟糕的关系而格外尴尬。可我觉得错的不是我,我只是有些早熟,很早就能听懂那些女老师对孩子们的嘲讽:一边用施恩的态度让上自习的小孩给自己跑腿买零食,一边对着孩子撒欢一样奔走的背影讥笑;号召大家给班级捐款捐物,捐来的东西都被她拿回去自己用。却还能大义凛然地批评什么都没捐的同学,带领大家一起孤立唾弃……
这个样子的中年女性班主任,很多人都遇到过。大多数人都会在长大后宽容地感恩,说毕竟她教过自己,可我不会,13岁的我还没学会“想得开”这一快乐人生必杀技。针尖对麦芒,她说我偏激冷酷,我:说她虚伪贪婪。
那一年的战争当然是她赢了,她手里有兵,我身无分文,全班大部分站在她那一边。
我爸妈忙着赚钱,我找不到他们帮我,幸好班主任也找不到。我一腔愤懑无处发泄,暑假的时候,被舅舅带去山村里见远房亲戚。就这样认识了小宛。
小宛是亲戚家的女儿,比我小4岁,有着粗糙的皮肤,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和一头棕色的马尾辫。她瘦瘦小小的,躲在人群里不说话,只露出格外明亮的眼睛偷偷看我。带领我上山下水,并保证我这个城里来的缺心眼儿孩子的安全,是我舅舅交给小宛的任务。
小宛一开始有点瞧不起我,我怕蚂蚱,怕蛇,一脚踩进茂密的向日葵田里,只因为草棍扎了小腿一下。就恨不得哭爹喊娘。我跟她解释这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小宛一翻眼睛,说,呵,是吗?
我不管小宛听不听得懂,一直跟她絮叨我们班主任那点儿破事儿。小宛坐在树根上,双手托着小下巴,懵懵懂懂地听着,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也有老多不高兴的事儿。那能咋办呢?”
我傻眼了。是啊,我13岁,她9岁,我们能怎么办?
我再见到小宛时,已经是4年后。我考上了省里最好的高中,成绩也蛮好,却终于顶不住理科班的压力,在高一结束的暑假,决意去学文。虚荣心让我一遍遍地对别人解释,我理科成绩很好的,我只是喜欢文科,真的,不是因为我笨。
那时我已经去过不少风景名胜,小山村不再是我记忆中蒙着一层薄雾金光的圣地。我17岁,不再撒了欢地往山上跑,开始在意自己会不会晒黑。只喜欢赤脚站在冰凉的溪水里。一边驱赶蚊子一边发呆。小宛13岁,有点儿大姑娘的模样,依旧黑黑的,眉眼舒展开,眼睛愈发亮。
这一次我没有对小宛喋喋不休,换她来倾诉。13岁的小丫头还不懂有些话不能讲给外人听,在她心里我是个城里来的好心大姐姐,所以一切私藏的烦恼——哥哥嫂子奉子成婚,嫂子家里人短了两万块的嫁妆;小青姐18岁就嫁了人,可是半年没怀孕,男人喝多了就往死里打她,她却死活不离婚……
还有更多的,断断续续的,欲盖弥彰的,更加沉重的秘密。
我17岁她13岁,我们依旧不知道该怎么办。
黑压压的重点高中里前途未卜的渺茫,闭塞的小村子里18岁就结婚的笃定,我们俩,究竟谁比谁更好一些呢?
然而我那时读了太多的心灵鸡汤文,所以对于小宛的苦恼我大手一挥,不负责任地说,你好好学习,考到你们县或者市里的高中去,上大学。你千万不能18岁就嫁人,别让你妈拿你换嫁妆!你记住,像小青姐这样,一辈子就完了。
你看,我是多么轻易地就评价别人的人生“一辈子就完了”。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刻小宛看我的样子,仰着头,阳光从密密匝匝的松树林上空照下来,只留下零星的光点,其中两颗,就在她眼里。
她点头,说,嗯,我不会这样的,我会离开。
然而人生导师的豪情壮志却被我的好友兜头浇灭。她说:“如果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呢?如果她存了这份心却根本考不上大学呢?到时她的小姐妹都开开心心嫁人了,过成什么样也都满足。她呢?”
我惶恐了很久,恨不得让我舅舅带句话,让小宛还是别学习了,小青姐有小青姐的幸福。
小宛的确不是读书的料。但是她很聪明,聪明在审时度势,人情世故,举止得体上,却没聪明在数学公式和英语词组上。初中毕业,小宛哪里都没考上,和家里闹了一场,奔向了省城,在一家度假村里做了服务员。
在我都快忘记她时,小宛又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仍然在人群中,眼睛仍然明亮如初。
我拉着她的手,却不知道说什么,眼前的姑娘穿着米色的风衣,长发披肩,依旧是小时候秀气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上眼的一瞬间,突然觉得不需要说什么了。
小宛已经在度假村做到了大堂经理,180个下属,娘子军的头目,并通过函授课程修完了酒店管理的学位,即将跳槽到我市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如此励志的故事,若是仅仅如此,倒也没什么。更有姿色的姑娘,早就通过嫁人的方式做了五星级酒店的老板娘,有什么稀奇。让我感动的是小宛的状态。她赚了不少钱,却没背恶俗的logo大包,一身都很得体,文文静静安安稳稳的。只是聊了几句,就让人从心底感受到一种说不清的力量和安定。
“安定什么,”小宛苦笑,“我爸妈现在都不肯认我了。”
哥哥和嫂子第二胎终于偷偷摸摸生了个儿子,赌博却把家底败光了。想把儿子送去镇上读书。顺便混个城镇户口,朝小宛开口就是十万。小宛拒绝了。
当初纵容她二十几岁还不结婚就是觉得她能赚钱,现在发现赚的钱都进不了自家的口袋,立刻就破口大骂,有家难回。
那一刻在我脑海中出现的一个词语是:异乡人。我和小宛从小境遇就不同,最终却都做了流浪者。
前几天有个新闻引人关注。一对情侣去饭店吃饭,邻桌的流氓冲女生吹口哨调戏,男生拉女生快步离开,女生却说男生这样做不够爷们儿,并率先冲去找流氓理论——男生在混战中被流氓一刀捅死,临死前问女生,现在我够爷们儿了吗?
大家都在声讨那个作死的女友,我却忽然想通了一件事,那是属于26岁的我,到目前为止所开悟到的“怎么办”。
如果我是那个男生,自然也会逞英雄,不过从此之后,会致力于有朝一日能带着女友到没有流氓的、高级一点的餐厅吃饭。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们随机出生,随机获得不同的资源与背景,然而人生就是一次再选择的过程,不安于此的,只能出走。
你是一匹野马,所以你要去草原。我和小宛都脱离了自己的环境,却还没能够找到归属地。在这漫长的一路上,幸而还有勇气,就这样出走,出走去做一个流亡者。
(司马冬荐自《萌芽》)
责编:小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