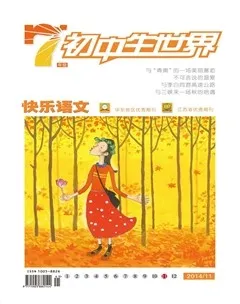三峡(节选)
当我真的坐船经过白帝城的时候,船上的广播员正在吟诵着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口气激动地介绍几句,又放出了《白帝托孤》的乐曲。猛地,山水、历史、童年的幻想、生命的潜藏,全都涌成一团,把人震傻。
《白帝托孤》是京剧,说的是战败的刘备退到白帝城郁闷而死,把儿子和政事全都托付给诸葛亮。抑扬有致的声腔飘浮在回旋的江面上,撞在湿漉漉的山岩间,悲愤而苍凉。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在李白的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他们知道,长江行途的最险处无疑是三峡,但更知道,那里又是最湍急的诗的河床。他们的船太小,不能不时行时歇,一到白帝城,便振一振精神,准备着一次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只能请那些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诗人在三峡的小木船上,刚刚告别白帝城。
鉴赏空间
本文并无太多写景之处,主要写白帝城,还有与之联系紧密的诗句、诗人和故事。作者以三峡游踪为线,编织着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凸显三峡的文化含义。在作者心中,三峡几乎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见证者,它不仅代表传统意义上的山水风景,更蕴含着浓烈的文化气息,是作者心中无可替代的圣地。作者以“李白的时代”的诗人为例,道出了诗人与山水的亲密关系——真正的诗人,是驾一叶扁舟行进于湍急澎湃的江水上,把酒临风,沉着而激动地吟出心中精神与感动的人,就像李白在白帝城悄然登舟,当时无专用,却被传记千年。三峡,是真正的诗歌的摇篮,有《早发白帝城》为证,有李白为证,而那些驰骋一时的战将与战事,则随滔滔江水滚滚东去。
[读有所思]
读后请你谈谈,本文中三峡的文化景观引起了作者哪些方面的思考。
(选自《中国当代文学》,刘景荣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