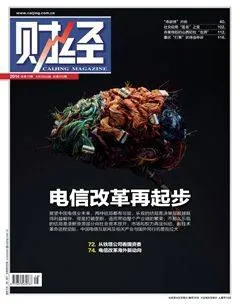预算修法长跑
在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权力得到有效约束无疑最为重要。以法律而论,被称为“经济宪法”的预算法就是这样一部约束政府“钱袋子”的重要法律。但也正因此,中国的预算法修法,在人大与公众监督、预算透明、支出公开、地方能否自主发债等诸多环节,仍正经历着不小的博弈与阵痛。
时隔将近两年之后,2014年4月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在二审稿的基础上,此次三审稿修改了十个方面的内容,涉及法律条款将近30条。三审稿对于预算法的立法目的、预算公开、地方债务管理等方面内容,都做了调整。
有业内人士认为,三审稿相比二审稿有很大进步。但由于争议仍然较多,在诸如是否赋予人大修改和调整预算的权力,央行究竟是“经理”还是“代理”国库,公众如何参与预算,地方债风险管理等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之路仍然相当漫长。三审稿最终未能通过。
自此,从2011年12月首次审议至今,预算法这部重要的“经济宪法”修订,业已成为旷日持久的修法“马拉松”。毋庸置疑,现行预算法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修订具有很强的紧迫性。然而与此同时,修法也面临很多不同的意见,一时间难以权衡。修法紧迫性和各方意见的统一,两者一时难以兼顾,立法机构必须从中作出一个选择。
从实际来看,天平正向搁置争议尽快出台法律的一方倾斜。
重申立法宗旨
预算法三审稿,仍然是修法过程中的一个博弈呈现。只不过这一次修法的主体有所变化,呈现出来的修订内容也因此多有变化。
自1995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现行预算法。201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2012年6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相比一审,二审稿在多个方面出现了倒退。审议后二审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短短一个月时间,竟然收到33万条修改意见。
不同于前两次审议由财政部牵头起草,三审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完成。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了三审稿内容。
李飞指出,三审稿吸收了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吸收了二审稿公开征集的意见,以及预算法修订过程中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人大代表们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意见。
但预算法三审,显然是一次匆忙的矫正。按照全国人大此前的考虑,如果预算法中有些问题不能获得突破就先不审议。而人大内部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如果一部法律的修订超过两年没有再行审议,往往就要另起炉灶进行大改,但三审稿匆匆上会,显示出现行预算法很难适应现实、亟须有可替代的法律进行规范的迫切性。
另外,此次三审之前预算工委或财政部也没有像以往那样,专门召开专家咨询会征询意见。这从侧面说明,三审稿并非较为成熟的,吸收过各方面意见的审议稿,它的审议只是在走一个过渡性程序。而且,三审过后也没有像二审后那样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此前曾参与预算法修订,他对《财经》记者表示,预算法的修订,横向上是对全国人大、国务院和财政部三者的权力进行配置,纵向则包括调整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全国人大频繁在多个部门征询过意见,各方分歧很大。
施正文认为,在二审稿的基础上,三审稿有一定的进步,但有些可以做出突破的方面并没有形成突破,有些方面相对于二审稿还出现了倒退,与整个社会对预算法修改的期待,以及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目标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开宗明义,在立法宗旨方面,三审稿将预算法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对此施正文表示,从立法宗旨来看,目前的预算法是管理法,规定政府如何收钱花钱,修订后预算法就成为人大控制政府的控权法。三审稿在立法宗旨上指明预算改革的方向,只是以下的具体条文还达不到控权法的标准。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表示,预算法的定位必须首先认清,它应该是约束和引导政府管理好公款的法律,在中国没有第二部法律能够代替预算法发挥这样的作用,而三审稿的立法宗旨中还包括“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说法,显然此次修法并未全部到位。
王雍君说,政府公共资金的收取、分配和使用的规模,在最近20年急剧增长,如何有效地引导政府花好纳税人的钱,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中国政府成为富政府之后,预算法应该履行好守护纳税人钱袋子的使命,因此它必须是一部充满法治理念的法律,法治表现在财政上,就是政府拿钱和花钱,必须获得明确的授权,在授权基础上,应该实行严格的问责。
王雍君说,预算法必须是一部财务授权的法律,财务授权就是授予政府拿钱、分钱、花钱的权力,所以预算法的基础非常明确,就是未经代表纳税人的立法机关的明确授权,政府不能拿钱和花钱。这就是法治授权,遵循这个法理,预算法修订才算成功。
人大代表纳税人授予行政部门以合法的财政的权威,行政部门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其中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那就是它可能滥用这项权力。为对权力进行制约,就要以责任制约权力。问责还需要得到财政透明的保障,当责任很脆弱的时候,透明就变得无比重要。如果透明度不能得到保障,就要有救济的办法,那就是预见性。如果预见性也不能保证,那就要参与,在预算过程中发展各种参与机制,让公民通过预算程序表达自己的声音,政府作出适当的回应。
“授权、责任、透明、预见、参与”,王雍君认为这是预算法修订的重要任务,从目前的三审稿来看,这些方面还存在盲点和漏洞。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认为,不管是千条规矩还是万条规矩,预算法最根本的一条,应该是政府的钱必须按照社会公众的意愿来花。“家庭理财如果脱离了主人的愿望,这种理财一定是糟糕的,同样政府理财如果不符合社会公众的意愿,也会出现很多问题。”蒋洪说。
如何公开透明
预算公开是预算法修法宗旨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但在预算如何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上,有关部门与修法主体的杯葛仍然未了。
在预算公开方面,三审稿删去了预算公开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决定的条款,规定了应该公开的内容,还明确了公开时间,政府预算、预算调整、决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其报表,部门预算、决算及其报表,应当在批准或者批复后20日内公开。
对此一改动,施正文认为预算公开方面三审稿比二审稿有一些进步,但还有较大的修改空间。三审稿立法主旨中强调的公开透明,应该体现在政府预算活动的各个环节,而草案规定的只是将预算的结果公开,而且还是概括性的公开,预算编制的过程人大和公众都不能参与,这仍然不是真正的公开透明。
这也使得20天的时间规定显得意义不大。其实公众要求的不只是时间的快慢,即使5天后公开,而公开的只是公众并未参与意见的结果,也没有实质性意义。即便是结果公开,也应该更为细化,比如重大项目资金需要公开,公开到项这一级。预算公开的真实性也应该加以保障,审计部门要对预算进行审计,并公开审计结果。
要做到公开透明,政府的收支分类必须进行调整。不管分为多少层级,其分类应该以问题为导向,以财政资金使用的去向和使用效益为导向设置指标。而目前的收支分类设置也避重就轻,便于政府管理而不便于监督。
三审稿还强调了全口径预算,规定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这四本预算的定义,并且明确了后三本预算的编制原则。
蒋洪认为,至少从形态上看,这比目前的预算法有了较大进步,但是这种所谓“全口径”,并没有将所有的政府收支纳入,比如目前为数不少的财政专户,并不在这四本账本当中,也就是说在预算之外。
再比如,其中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仅仅是国有资本经营成果的一小部分,小到不及10%,换言之,九成以上依然在预算外游离。另外政府的资产负债情况,也没有体现在四本预算中。
对此王雍君也表示,预算的完整性,在三审稿中表述为预算的全口径,这实际上将预算完整性这样的重要原则,矮化为一个统计口径,令人匪夷所思。
另外,国库的“经理还是代理”之争,在三审稿后依然延续。
现行预算法规定,中央国库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经理,而二审时这条规定被删掉,三审稿仍没有恢复。
施正文认为,中央银行经理国库,这是国际上的惯例,国库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单一账户,一级政府只有一个存款账户,由中央银行国库管理集中收支。现在财政上有财政专户,国库账户只管一部分资金,所以这不是单一账户,很多资金根本无法管理。目前情况下作为过渡措施,如果财政专户确需设立还可以保留一段时间,但设置权必须上收,需要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不能只是国务院同意。
蒋洪也认为,按照公司财务的一贯原则,会计和出纳必须分开,国家层面也是如此,人民银行担任出纳的角色,财政部担任会计的角色,两者应当有所制约。
地方发债进退
在地方土地财政吃紧前提下,预算法三审稿中地方债方面的规定,引发了公众关注。现行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草案的第一次审议,提出对地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二审稿则推翻了这项规定。
此次三审稿中,对地方债相关问题做了大幅度修改。草案明确举债主体,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对举债的方式、用途、偿债资金等作出规定,限于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用途应当是公共预算中必需的部分建设投资,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并应当有稳定的债务偿还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地方政府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等。
施正文认为,在地方债管理方面,三审稿与现行预算法相比没有实质性进步,依旧是授权于国务院,只是原来为空白授权,现在改由国务院控制,而且只有省级政府才允许发债。发债规模上现行预算法没有人大批准的规定,而三审草案规定必须由国务院报全国人大批准。
他认为,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应该有发债的自主权,至少要有相当的权限,如果发债权限完全在中央,那么地方债与国债无异。而且地方债真正的需求主体不在省级政府,而是市级政府,但按照三审稿规定它们不具备发债权。财税体制的财权过于高度集中,施正文认为,三审稿中地方债等条款强化了这一点。
蒋洪同样认为,三审稿中的地方债规定没有多少变化,不过他同时表示,中国现在还不到放开地方债的时候。
蒋洪对《财经》记者说,新草案中的地方债管理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现行规定是地方不允许发债,但国务院同意后可以发;修改后变为地方可以发债,但国务院不同意就不能发。看似两种规定,实际上是一种含义。
他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讨论地方自主发债的基本条件。他表示,地方政府举债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财政上独立,自己举债自己负责;二是地方政府应该是理性的。这两个条件现在都不具备,地方官员的举措都是短期行为,不为未来负责。
“打个比方,一个人的儿子财务上不独立,还傻乎乎的,这个人会同意他儿子借债吗?所以地方发债问题,目前是个伪问题。”蒋洪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在审议草案时表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需要“开明渠,堵阴沟,建防火墙”,其中最关键的是把“防火墙”修好,设定一系列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让地方政府举债阳光化,构建行政控制与规则管理相结合的多层面、有效的债务管理体制,处理好存量债务与增量债务的关系,防止出现地方政府举债开“前门”堵不住“后门”的局面。
辜胜阻建议,一要制定严格规则,构建行政控制与规则管理相结合的地方债务管理体制,对地方政府举债实行限额控制,设立多样化的约束性指标,防范“道德风险”;二要分类管理,对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债务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三要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构建多层面、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体系,让地方政府债阳光化;四要处理好存量债务与增量债务的关系,积极利用地方政府债券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化解存量债务。
修法宜准还是宜快?
法理基础不明,结构不合理,在王雍君看来,这是预算法三审稿中存在的两个主要缺陷,草案将修订重点放在了管理措施方面,比如地方债管理等,从而使法律沦为一份管理文件。“相当于立法机关委托政府部门搞一下调研,看看预算管理中存在哪些问题,调研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神圣的法律矮化为各种管理措施。”王雍君说。
“三审稿不是终审稿,就算我们有四审、五审哪怕到八审,也可以理解,只要我们没有把预算法的法律性质、定位认知清楚,匆忙出台一部法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王雍君说。
王雍君认为,只有把基本问题想好之后,法律基础明确,结构比较合理,而且能够解决实际中的重大问题,才算一次成功的修订。
财税领域的法律本来就不多,预算法是第一部至少会经过四次审议的法律。
据《财经》记者了解,全国人大一位负责人此前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表示,现行预算法与现实要求差距比较大,预算法修订的形势极为迫切,但同时现在通过修改满足社会需求达成共识的难度也很大。如果两者不可兼顾,只能更倾向于解决时间紧迫的问题尽快出台,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无法解决只能暂且搁置。
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接下来预算法修订可能不会再拖太长时间,但修法的目标有可能因此降低。
施正文表示,预算法修订案草案有可能于今年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但同时全国人大也考虑在明年3月“两会”召开的人大全体会上通过该修正案,放大预算法修订的积极意义。如果是后者,由于目前的三审稿并不成熟,那么预算法草案必须在今年底之前进行四审。“如果最终五审才能通过,四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可能性很大。”施正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