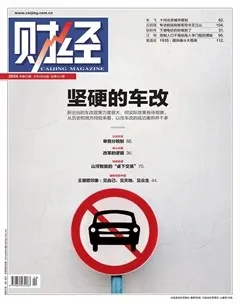中国如何输出能源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将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发展能源合作,为中国提供安全可靠的油气进口来源。笔者认为,在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过程中,不但强调中国将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稳定的能源输出市场,而且中国应该也有可能成为广义上的“能源输出大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如何承担起“能源输出大国”的责任,中国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考虑:
第一,在建设能源供应通道时,既有输往中国的油气“上载”, 过境国在必要时(如中亚国家冬季供暖需求)也可以“下载”部分油气,以满足本国需求。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冬天供暖缺气时。
在中国能源供应来源多样化的情况下,海上、西北、东北和西南建成的四大能源供应通道也使我们有能力适当调节各个能源通道的供应量,适应不同方向能源输出国和过境国的需求变化,允许一定程度的“下载”。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相关国家的能源需求,也降低了输向中国的能源通道的政治风险,客观上有利于各方长远的能源安全。
从这个角度看,四大能源通道之一的中缅油气管道值得称道。按照相关协议,在送往中国的油气过境缅甸时,缅方每年可以下载200万吨原油和24亿立方米天然气,用于推动缅甸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周边国家援建清洁火电厂,并大力推动电力联网。
在中国的周边和较为临近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阿富汗等国,都或多或少地处于缺电或至少是季节性缺电的状况。
相比之下,中国近年来全国电力供应相对充裕,特别是东北区域电力供应富裕较多,西北区域有一定富余,而南方区域总体平衡。而且,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GDP增速趋缓的大背景下,电力需求的增速也在下降。近年来中国火电每年新增装机维持在5000万千瓦左右的水平,2013年新增火电装机仅为3650万千瓦。因此,中国火电装备制造产能以及施工能力过剩,煤炭需求也陷于长期疲软。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借助资金和产能的优势,在周边缺电国家因地制宜协助兴建高效能的清洁火电厂,并推动与周边临近国家实现电力联网,调剂余缺,也可为国内西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提供新的出路。
第三,整合对外援助渠道,以大手笔的“光伏外交”推动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的可再生能源革命。
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的能源结构中只起一定的补充作用,然而在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家则大有可为。以岛国马尔代夫为例,其电力供应全部依靠进口的柴油发电,发电成本高达每度27美分-65美分之间,比煤电成本高出5倍以上,比光伏发电成本还高。马尔代夫每年燃油补贴高达1.15亿美元以上,人均补贴近370美元,财政难以为继。而且柴油发电对环境污染也很严重。
以中国的资金、技术实力,特别是在光伏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整合对外援助渠道和资源,在马尔代夫以及其他中小国实施“光伏外交”。
第四,分享能源发展特别是中国农村电气化的成功经验,体现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软实力。
虽然中国的能源管理体制、价格体系、利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诸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发展历程依然是一个典范。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如果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相当、起点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较,目前中国的用电人口已经占总人口比例的99.8%以上;而印度仍有25%的无电人口,也就是大约3亿人口没有用上电。印度的情况正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缩影,目前第三世界整体而言大约仍有25%的无电人口,总数高达13亿人。中国到底是怎样在30年间解决了近5亿农村人口用电问题的?中国应主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咨询”,分享农村电气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应为一个整体概念,不仅保障我们自己的能源供应,也顾及沿线国家的能源需求,这样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也为处于产能过剩的能源制造业走出去创造新机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