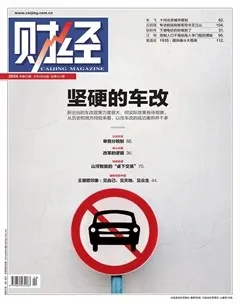自主创新不可脱离现实
与以往一样,自主创新继续成为新一届政府的科技政策核心。然而, 进入2014年以来,GDP增速下降,实体经济缺血顽症依旧,以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创新已经不能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表态。
自主创新是伴随着2020年初步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在2005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的。
口号一提出,就收获了两方面截然不同的反应。官方、大多数科技专家以及部分高调的大型央企反响热烈,在多个场合宣示决心。而在华外企起初似乎一片哗然,以至于笔者参加过的多个创新政策研讨会上,能看到包括时任副部长尚勇在内的科技部高官频频解释,自主创新不是封闭创新,自主创新是鼓励发展民族独立技术。
在自主创新这个口号提出将近十年后,我们很有必要检视一下创新可以如何“自主”,又是什么样的自主创新才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辨析自主创新
自从自主创新的口号提出以来,国内不但已有的载人飞船等技术突飞猛进,多款先进战机和航母也开始自主生产。这些技术是中国想买也买不来的,对于保持民族独立、强大国防而言,重要性说多少也不过分。除了这层意义,自主拥有核心技术以及以本土创新带动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正是在这个层面需要做更多辨析。
拥有大多数主流产品的核心技术,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最大化的收益。比如,在PC机一统世界的时候,微软-英特尔联盟就在坐着收钱。然而,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之际,任何一家企业,甚至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必要通吃核心技术。
固然中国厂商,以及更多在中国设厂的国际厂商不能像微软一样坐着收钱,但它们生产了全球大多数电子产品硬件。学术界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固然没有原始技术的创新,但通过过程创新实现了最大规模、最低成本的生产,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中国厂商虽然不如微软们赚到那么多钱,但毫无疑问,这种创新驱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
然而,这种基于程序、基于拿来主义的创新虽然推动了经济,却没有赚到垄断利润,这让支持自主拥有更多核心技术的说法有了更多的道义正当性。但拥有了道义正当性,并不等于就完全合理。仍然有一些绕不过去的问题需要我们回答。
首先,技术自主或者研发了世界首创的技术就可以成为核心技术吗?
核心的意思是指一组技术中,核心技术处于最为关键的位置,可以引领他人发展,如果专利保护好,则可以从这些发展中坐地收钱。实施多年后,自主创新的战略毫无疑问可以形成若干独立的、自主的技术,但这些技术能否被同业认可,并可获得技术转让收入和产品发展红利,这远非技术本身可以决定,更多是市场、资本与技术互动的结果。主要体现为研发政策的自主创新战略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拥有了核心技术就一定可以赢得巨额利润,推动和引领经济发展吗?
由于历史原因及客观存在的技术封锁,中国宇航业建立在拥有众多核心技术基础上,但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从经济回报上收获这一产业带来的利润。一种说法是中国航天的发展带动了工业制造能力的升级,但要注意的是,制造能力的升级是发展核心技术的溢出效应而并非收益。没有发展核心技术、主要给外企代工的富士康中国工厂,同样创造了中国经济制造能力的升级,甚至其技术升级程度,并不低于为宇航效力的军工厂。
第三,实现了自主创新,就等于拥有了所有或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吗?华为作为知名的全球电信设备制造商,并没有声称其设备或核心设备都是自己的实验室独立研发的。
思考以上这些问题,并非要否认自主创新,而是要强调,创新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自主”二字可能并不是唯一或者最主要的指标。
谁来自主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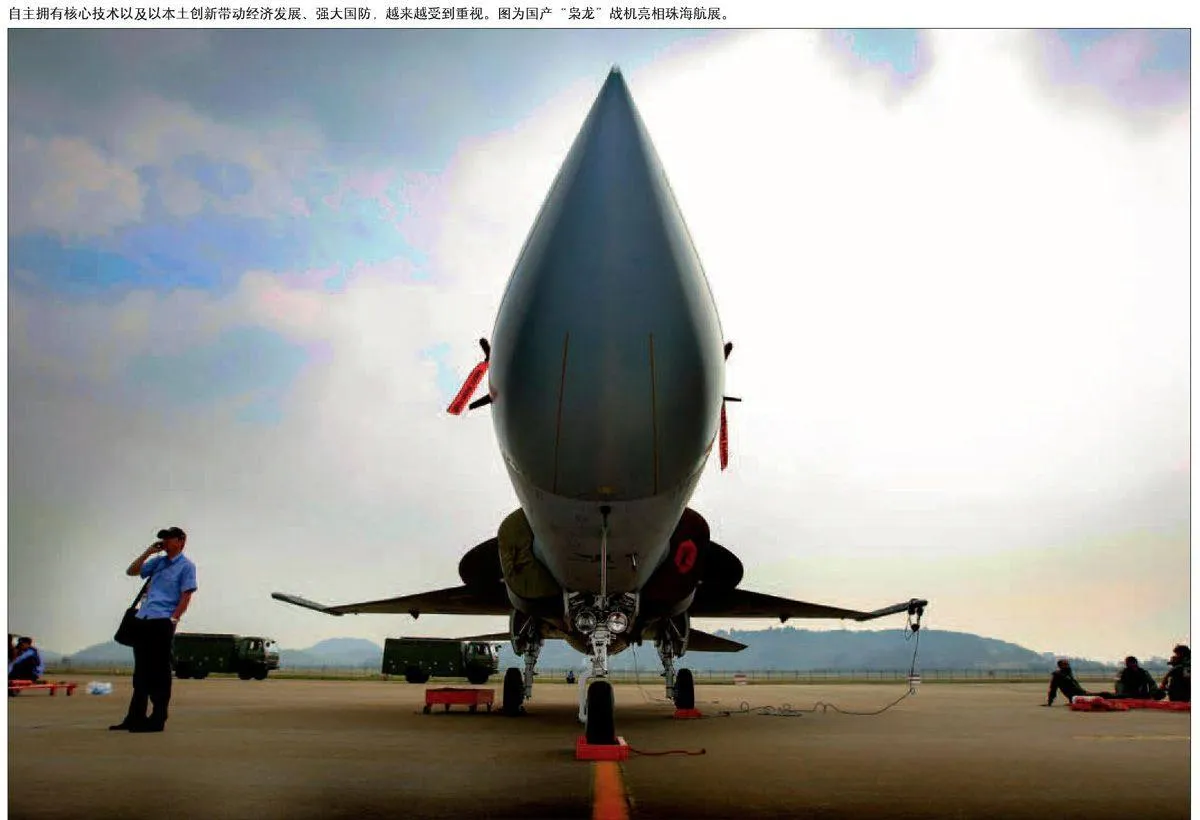
创新的主体在企业,这是社会共识。对于企业而言,做任何事都要围绕着盈利这一目的展开。技术研发即便不为今天赚钱,也是为了明天挣更多的钱做准备。因而,自主不是目的,甚至谈不上手段,至少不必是主要的手段。是否需要创新,要看市场的需要。是否需要自主,则完全是衡量成本收益和能力。
如果社会上有很好的可供转移的技术,即便是具备了相当财力和技术规模的企业也并非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或者有了研发中心也不一定要从源头研发技术。
也许有人会说,目前产能过剩、产品同质化严重,自主创新才能让企业赢得垄断或者超额利润。但在微观层面上,技术垄断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与自主创新并没有本质联系,即使不能像微软的坐收红利或者苹果那样有世界各地的“果粉”买单,也同样可能通过政策垄断、资金垄断、独家买断技术等,实现较高的回报。
因此,只有让企业完全失去可以依靠政策的垄断,限制其依靠其他资源的垄断,并在社会层面为技术创新营造可以依赖、可供选择的技术,企业才能真正调动起自身的资源做产品研发,并以此为核心,从而实现对创新过程的整合,更重要的是全力投入于对创新产品的营销。
显然,即便中国今日的研发经费超过万亿元,即便其占GDP的比例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指标,但中国企业在上述创新条件上仍然营养不良。这远不是号召甚至资助企业去自主创新就能够解决的。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设立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并以企业为主体完成项目来推动创新,有可能补给企业研发经费的不足,但并不能解决其他方面的营养。何况,国家科技官员并不一定知道市场的需求是什么,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并非能够清楚地被衡量。在若干重大专项项目上,企业与一些科研大腕“拉郎配”,先谱写一个优美的天下第一的故事获取经费,再把故事编写圆满即可交差,这样的事情当今中国科技界人士都不陌生。
如前所分析,天下第一并不能保证创新的成功,何况这个第一还可能只是个传说。
政绩与交差逻辑
既然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了美丽的、政治上永远正确的辞藻,中国强大的既有体制逻辑,就会不断地在其符号意义上做文章,而究竟哪些创新是自主,哪些创新不过是舶来加工,解释权并不在创新者本人(创新者本人如果只考虑自己的项目或技术,也没有必要考虑自主与否),而在于各级官员。但各级官员几乎不可避免的 “政绩逻辑”和“交差逻辑”必然会侵蚀实质性的创新机制。
即便如深空、深海探测等特殊领域,因无法以其他渠道获得技术使自主创新成为必然,也要小心这类创新的驱动力更多是基于政绩,而非真正的国家需求,更要防止以这类不得不自主的领域取得的成就来扩展自主创新的涵义,仿佛制造业领域的技术也只有具有“上天入地”的绝活才足够自主得让人放心。
以政绩逻辑而论,成绩可见的大工程项目更易获得优先支持。不是说这类项目不够创新,但它们的基础主要建立在大规模的工程试错的基础上,只要有充分的资源投入允许出错,其成功的概率就会高很多,也就更容易支持科技官员们的政绩。但工程试错式的创新能否符合对成本锱铢必较的市场逻辑,则并无定数。
与政绩逻辑紧密相关的是交差逻辑,依此很容易忽略这类创新对于市场、民生的实际效用。
最近一个值得玩味的例子,是网友传言“蛟龙”号官微删掉了留有深潜几千米雄心的微博,以躲避下海寻找马航失联客机的责任。这则谣言被愤怒批驳,理由是这些互动微博早在几个月前就被删除了。
谣言固然可憎,但作为国家科技成就象征的“蛟龙”号业主方,在如今再无存储空间之虞的社交媒体上删除微博的做法也值得深思。这说明,类似蛟龙探海这样的创新,并不在乎与公众真正的互动,自然也没有把删帖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而忽视与公众的互动,又如何能真正捕捉孕育在公众话语中的民生需求,甚至是市场商机,这不也恰恰是表功式、交差式的中国创新经常与市场结合不足的体现吗?
就支持创新的机制而言,在政绩与交差逻辑的背后,应是善于把握官员表功需求而非真正创新价值的研发者易获得更多经费支持。
贪腐侵蚀创新
各种支持自主创新的重大项目,也让长期以来鲜有贪腐新闻的科技界如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腐败。
2014年前后,先是浙江大学负责水污染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教授陈英旭因贪污945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紧随其后,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原执行院长宋茂强,也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之前,中科院院士候选人段振豪因贪污130万余元科研经费曾引发高度关注,最终获刑13年。
陈英旭们的贪腐是在科技资源迅速增加的大背景下发生。这类贪腐事件的发生,不仅说明科技项目的管理机制仍有欠缺,更体现了在自主创新的口号下,以科技赶超为目标的大型科技项目,与现有科研体制之间必然的张力。
值得深思的是,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看起来并不缺乏监督。相反,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在重大科技专项这类“花大钱”的地方,事先的财务审批和事后的审计极严。以至于宋茂强和段振豪这两位“大科学家”,不得不用大量冒名身份证、筹措的火车票和其他差旅票据一张张把几十万元经费虚报出来。他们的这种做法既体现了贪腐分子的“执着”,实际上也代表着科学界芸芸众生相,很多不可预期的合理开销,由于事先无法列入预算也不能提取,不得不采取各种猫腻。
这不是替宋茂强和段振豪等辩护,而是强调当合理的开销也不得不通过四处筹措火车票来解决时,不正当的经费支出就更能暗度陈仓了。
目标不确定、评审不透明、参与者熟人圈的重大科技项目的不断增加,为利用体制漏洞提供了更多机会。很多重大项目要求的就是重大技术实现自主创新,但如何算是自主创新,实在“难于言表”。
本来,绝大多数科学项目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经费使用细节不可预期这类特征,这种情况往往与财务官员事无巨细列出预算的职业喜好本质矛盾。 现代科学的发展通过科学界的自治解决了这一矛盾。项目该花多少钱,科学家们的小同行大体有数,而小同行往往会成为彼此的项目评委。
而经费大幅增加、实施细节又是各方都无经验,并以自主创新为衡量指标的重大科技项目,打破了这种科学界自治的惯例,再加上评审不透明、参与者局限在精英小圈子,几乎可以想见,今后会有更多陈英旭、宋茂强和段振豪等项目负责人东窗事发。
通过分析自主创新的实际应用、其与市场的关系、企业在其中的作用,官员的政绩思维与交差逻辑,来厘清 哪些地方我们不得不自主创新,而在哪些领域,自主创新并不一定就应当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企业应当发挥创新的主体作用,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政府要出钱资助企业以实现技术独立为目的的研发;创造显而易见的成果固然能提振国民士气,但其中蕴含的官员政绩追求和交差逻辑也不容忽视。
唯有此,才能将该强调自主的,努力贯彻独立自主的逻辑;该由市场判断的留给市场,哪怕此时此刻,市场并未将“自主”二字当成最重要的圭臬。
作者为《科学新闻》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