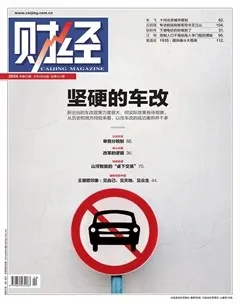“人的城镇化”中的法制构建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是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重大民生工程,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因此,城镇化建设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改革工作,更是当前的国家发展战略。
纵观中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经验,结合现阶段发展的难题和机遇,党中央和国务院抓住“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要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亦围绕“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就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通过改革释放城镇化发展潜力。
客观上讲,“人的城镇化”建设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包括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及环境保护制度等方面。因此,要真正破除现有城乡二元化的体制机制,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就必须要重新构建现有法律体制。因此,本文拟围绕“人的城镇化”之法律制度构建,特别是以土地和房屋为核心的物权制度构建问题提出以下观点。
现代物权制度的构建
人们通常将“人的城镇化”粗略地等同于“农民进城”,这实际上是对城镇化的误读。
“人的城镇化”不仅包括对现行二元分治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小城市(镇)的有序流动,也包括农民住房、农村交通、医疗、教育、养老、就业、文体等硬件设施和各种公共服务均等化,更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以主体(人)和客体(物)为核心的生产要素自由流转的法律制度。
单纯靠财政支持而产生的城镇化率提升并不是完整的城镇化,仅能够解决农民当前的迁移、落户问题以及在一定范围和一定阶段内的公共服务配套问题,产生局部和短期的效果,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科学的城镇化建设应通过激发农村内在的拉动力,以确保其有序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因此,实现城镇化的路径应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支柱的核心作用:政府发挥引导和政策支持的作用,市场发挥造血功能和激发内在动力的作用。否则,城镇化建设会因财政资金短缺而导致“烂尾”,甚至可能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城镇化问题,说到底还是要解决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
“人的城镇化”所涉及的法律制度较多,其核心是户籍制度改革和以农村土地、房屋为核心的现代物权制度的构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物权制度的构建是核心,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在没有理清农村产权关系、没有建立城乡统一的物权制度情况下贸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做法略显盲目,也会造成关键环节的脱节。
因此,“人的城镇化”应从城乡统一的市场主体构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明晰、完善二元化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完善农村土地房屋等产权使用权权能、完善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构建权利保障机制等几方面来系统性地思考城镇化法律制度构建问题。
城乡统一的市场主体
构建新型的、符合法律主体构成要件的、具备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城乡统一化市场主体是城镇化工作的基础,是解决长期城乡分治问题的桥梁。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个体、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行为和法律行为的基本主体。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户籍和集中居住为基础而构建的,具有人合性和血缘关联性的组织。
尽管现行法律赋予了其农村财产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内涵,不具备真正的法律主体资格,虚位和缺失现象成为常态。
在现有法律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存在主体虚化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却承担着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职能,即包括农用地、林地、宅基地、公益/公共设施建设用地/乡镇企业建设用地、四荒地在内的全部农村土地都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户的法律地位也形同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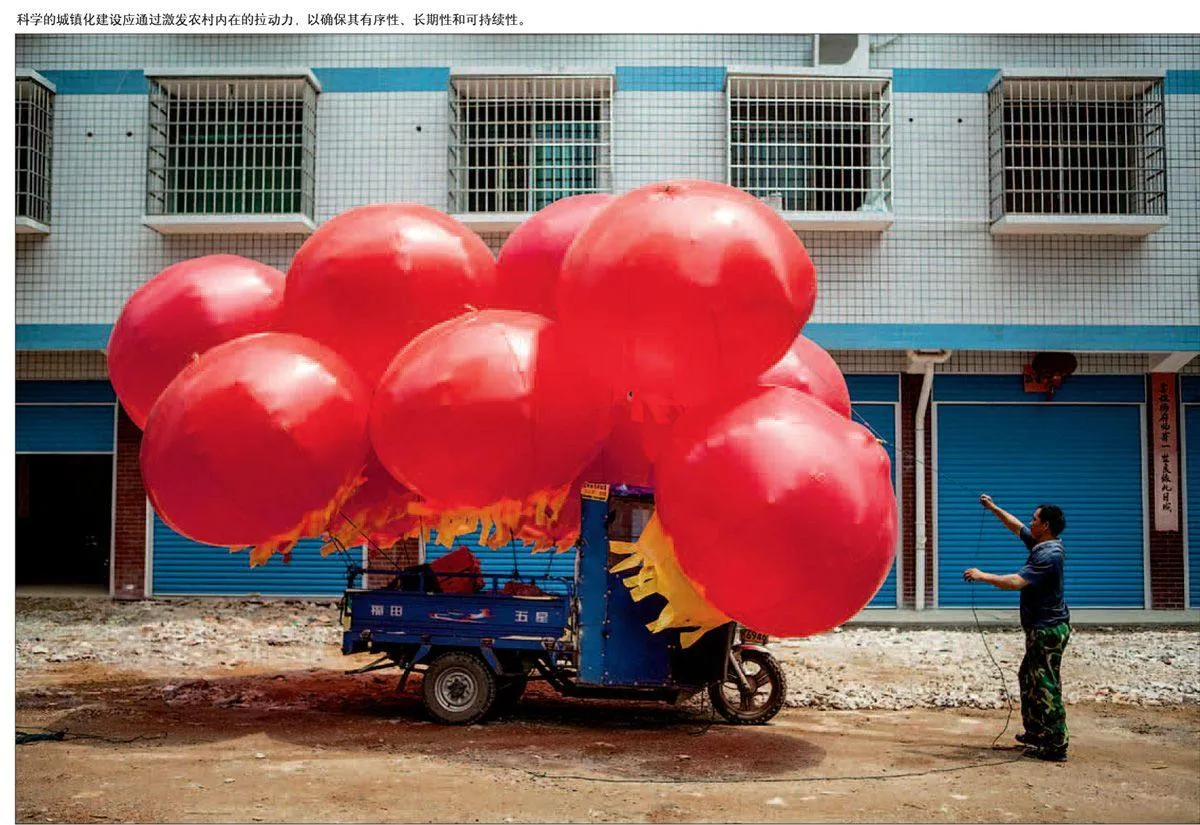
法律规定农民以户为单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承包经营权,但如何界定“农户”这一概念?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不仅制约了相应用益物权权能的发挥,且因主体不明而导致的权益纠纷频繁产生。
主体缺位或者虚化的物权制度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物权制度,而且必然会导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不彻底,进而给城镇化建设推进过程中农村资产的权益归属问题埋下隐患。
因此,需要重新构建明晰且具备法人主体资格的农村产权主体。
明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成员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权,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是法律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定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于这一身份权,可以享有集体资产的共有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分配权以及集体资产经营收益权。
但是,在当前进行的改革过程中,有的经济组织已经消失,有的则边界不清,那么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如何界定?对此在实践中均无解决的途径。有的地方拟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或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决议等形式来终止或变更成员权。
对此我们认为,现阶段在无法律规定的成员权消失的情形发生前,任何试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或集体经济组织自行决议或其他形式终止或者变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均有变相的侵权行为嫌疑。
法律制度的缺位,导致成员权及其相应的财产权无法得到保障,尤其是农村的资产和权属的固化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能否彻底。因此我们认为这一问题是整个改革的基石。
完善二元土地所有权制度
土地资源由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此为二元化的土地管理制度。但由于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目前面临的身份窘境,在改革中围绕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权利范围也难以厘清。
一方面,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即集体经济组织)主体虚化,以人人共有为机制的所有权制度在缺乏有效统一管理制度的条件下,实际上是人人都不享有;另一方面,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提出要稳定现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土地所有权实际上被虚化。承包权这一用益物权事实上成为一种农户家庭所持有的长久的固有权,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所有权的特征与权能。同时,大量的农村产权已经完成了资产量化和确权登记工作,做到确权到人、确权到户,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所有权被虚化。
因此,学者们开始对当前二元化土地管理制度进行反思和研究,思考现行二元化土地管理制度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并以此为契机对现行《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
只有解决了农村主体对土地的权利问题,方能明晰产权权益关系,为农民进城提供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否则,制度的缺失和进城高成本将会阻碍农民的有序流动,在此基础上对《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也仅仅是一种改良,难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经济效果的有机统一。
健全农村房屋、土地权能
所有权应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现行制度下,由于农民取得土地具有身份性、无偿性、福利性等特征,导致农村土地、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权能受限,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流动机制无法建立,具体表现为:一是农村房屋和集体土地不能向城镇居民流转,城镇居民也不得购买农村房屋;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向城镇居民转让,只能出租;三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而不能入股有限责任公司。
有的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允许确权后的农民带资产进城,但由于农村或者农民的资产物权权能受限,进城农户无法将资产投入有效的市场流动,从而无法体现资产的真正市场价值,使之变为“鸡肋”,不仅无法解决其进城成本问题,反而会导致农村资产的浪费或者闲置。
因此,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完善其权能,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流转市场并最终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有序流转,才能“物尽其用”,同时也为进城农户提供生存发展的基础物质保障。
有效的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
城乡分割而治的土地管理体制和因土地用途不同而形成的“九龙治水”式的土地管理体制,增加了土地资源管理的难度。
土地规划是土地利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和手段。
但是现实状况是各大城市的土地管理本末倒置,规划跟着用地走,调整随意且频繁,土地用途管制不如领导一句话,致使部分地方政府借以城镇化之名,盲目建设工业园区或圈地占地,无视规划,甚至侵占耕地乃至基本农田的情形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对城镇化有意曲解与误读;另一方面应归咎于现有土地规划制度本身的不完善,留出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随意修改的空间,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审批机制,这让“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的法律规定成为“橡皮条文”。
因此,必须完善现有土地规划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以保障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为底线和基础,否则城镇化将可能被扭曲为“圈地运动”,其最终的效果将与其建设目标背道而驰。
协商和司法双重保障机制
有效避免城镇化进程中以改革名义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是平稳、有序、和谐推进改革进程的重要内容。
城镇化中的矛盾高发点无疑集中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围绕如何减少拆迁纠纷,各地都在探索征地制度改革,具体做法包括划分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目录、逐步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增地补偿标准等。但仅仅依靠这些举措难以解决根源问题,原因在于导致拆迁补偿矛盾的核心并不仅仅是补偿费用的高低,关键是补偿机制的不合理和非市场化。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逐步减少政府在土地上的利益索取,通过经济杠杆探索开发商与土地使用权人之间的直接补偿办法,建立国家对农用地的有效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除了要建立事前公平协商机制外,还要考虑打通事后救济途径的问题,保证农民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即保障农民的司法救济权利。政府让位于市场,行政手段让位于司法救济途径。
综上所述,人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现实条件下各种法律关系的变动,在农村物权制度尚不完善、城乡统一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只注重面上的改革而不考虑其内在的制度障碍会埋下隐患,对城镇化进程形成阻碍。
因此,应当着力完善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各项法律制度,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依靠政府和市场两条腿走路,在财政大力支持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打通市场渠道,激发农村自身造血的功能,以此为动力而推进的城镇化建设才能称之为“人的城镇化”。
作者为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