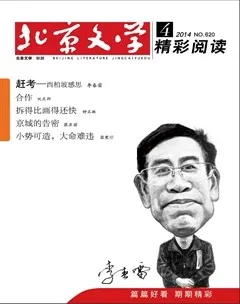那年的阳光
在我的感觉里,工业区的季节是不分明的。短暂几天的寒俏刚至,冬天还睡眼惺忪尚未足意,乍的转眼,似乎就是骄阳似火、炙烈如焚的夏日了。一年四季,太阳火辣辣地注视着大地,海风沾着浓郁的盐腥味,没头没脑地吹。南方的阳光是明亮的,但有点毒,光芒促急又夹着些彷徨。后来,我把它叫作没有春天的开始。少了春的熏染与滋润,自然少了许多的妩媚与柔情,工业区的生活常常像被敲打的铁质一样,坚硬,炽烈,枯燥。
新兴的工业区却春草一样,夹着道路丛生,一茬接一茬,像拼凑起来的大鸟巢,黑压压地笼罩着、盘踞着。春笋般兀起的工业厂房,侵占和覆灭着南方乡镇迷离的河脉、田野与山冈。只在最遥远的边沿,偶尔留下一小块稻田,夜静风清时,有菜花幽亮,蛙声依稀。
1999年新春刚过,我来到工业区,进入一家台资自行车厂谋生。多年以后,说起工业区,我觉得就宛如说起一些旧亲戚和他们的家常,怅然有些疏远,但亲切自然。在那濡湿的时光里,在工业区广袤的荒野上,我恍然看到,一些青春的草籽,有着挣扎的苦涩和悸动的骄傲。
生活在工业区的人,都是为生活奔波的过客。很多人和我一样,挂着外省籍的身份,说着夹生而难懂的普通话,展露笑容,隐藏内心。我们像游鱼一样潜入水底,偶尔才钻出水面晃露一下真容,难得地吸一口自由的空气。我们浮萍一样游荡在工业区的大街小巷,结识一些新朋友,又辞别一些故人。我们按部就班地生活和工作,有点寂寞,又隐忍着无奈。
在工业区的流水线上,我学着成为一个匿名者。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匿名者,我和我陌生的工友们,只是生活在工卡上,籍贯与性别都已悄然隐退,工号和工位成为我们的替身。这里似乎没有人,只有会说话的机器。开发,检验,校正,打磨,烤漆,涂装,组装,测试,打包,直至装柜出货。所有的工序都经过严格的设定,所有的人都只是特定工序上的一个环节。
我必须和我的同事一道,把笨重的毛坯铁架搬上校正平台,挪动调节着夹具把铁管固定下来,钳住,然后推动一个蘸满润滑油的校验钟,铿——锵——!不停地撬动检验钩爪,修正不合格的“阿婆脚”。铁架的两个钩爪长短不一,我们叫它“阿婆脚”,有这种“脚型”的架子是不合格的,必须矫正过来。这只是整个制程链条的一环,实际在珠三角的每一个加工车间里,每一个产品的每一个部件,都经历过类似这样亲密的抚摸与甄选。
不容置疑,我们都曾被一种巨大的热情吸引而来,只是现在,有的热情正在消解,有的热情隐藏得更深了。那种曾经在我内心里嘶咬的激情,仿佛已经波澜不惊。随着时间弥久,工业区生活越发平谈了,而我,似乎正在慢慢地适应和习惯它。工业区总是悄无声息地包容着这一切,而人们很容易就漠视了自己的年轻。
有一段时间,我靠练习普通话来打发无聊。在宿舍外的走廊上,从“剥,剖,摸,佛”开始,第次练习声母韵母;然后找出预先选好的一些精美文章的段落,忘情诵读。这一刻我会完全地陶醉在朗读的喜悦里,感觉那些音标和词语在舌头指挥下,千军万马般列阵奔跑。舍友们跟着就嘲笑起来,我旁若无人的神情,常常招致他们诧异不解的白眼。
而厂区外面,是大片等着被开发的空地,它们是未来的工业区。此时,空地上长满了野草。这些野草庞杂丛生,枯荣自便,显得孱弱又顽强。夜风渐起时,它们带着被剔除与忽略的命运,在风中唱出丝丝的歌谣。它们随风而寄,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屈辱与欢乐。它们,有时候也是一群失去身份的外乡人。
这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陕西安康的同事。他姓杨,个子敦实,眼神倔强,梳着四六开的小分头,嘴角微微上扬,嘿嘿笑着荡起的小酒窝里,隐藏着黄土高坡人特有的狡黠。“陕西有八大怪,油泼辣椒儿,也当菜——”他说话时拖着浓浓的秦腔调,充满高原韵味。他就睡在我对面的下铺,床头一本厚厚的《平凡的世界》,已经被翻得破旧不堪。
这个工业区里的“孙少平”,他有两个理想,一个是要在元旦节前穿上“带兜的裤子”;另一个最大的理想是赚点钱回去打一口好窑洞,让父母过上舒服体面的生活。“带兜的裤子”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很潮的休闲裤,裤身前后挂满口袋。他的想法很现实,他要从衣着形象开始设定目标,具体地改变自己。他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至少,在生活方式上应当如此。我欣赏他的思想,同时深深地理解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奋斗,来捍卫生存的尊严。
为了打发紧张日子间的空虚和平淡,我和杨君策划了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我们首先在女同事中间锁定目标,计划着联手出击各个突破的可能。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精心挑选了小礼物,当然,礼物也不过是一些糖果、饼干之类的小零食。然后潜伏在她们下班必经的路口。那一刻,我们忐忑如初出林莽的小鹿,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意中身影的出现。
捏着一手心的冷汗,我们终于口齿不清地把礼物送出,然后如释重负。接下来一整夜的漫长想象,弥补了那个年龄莫可言状的缺憾。第二天,女生们开始掩面而笑。她们把我们的举动看成半真半假的试探,她们内心里荡漾着小微澜,但她们学着矜持和不置可否。
这些可爱的小姐妹,她们大多数十八九岁,正值青春年华,姣好的面容绽放着自然的光泽。她们身着工衣,在流水线的工位上,如小雀鸟窃窃私语,如小牛犊不知倦怠。她们不知不觉地享受和挥霍着她们的美丽,她们仿佛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忧虑,她们安然知足,不时地笑出一串串清脆的铃音。
由于青春时期天生的笨拙,使得那尚未萌芽的爱情像笑料一样草草收场,不了了之。它或许成了活泼的女工友们内心里不得而知的秘密。此后生活照常,只是彼此的眼神里多了些人间的亲近与温情。她们都跟我一样,外表刚强,内心脆弱,她们似乎还经不起一次风霜的侵袭,所以必须学会谨慎,学会小心翼翼地自己保护自己。
若干年以后我才惊讶地发觉,当时光飞转盘回,那些在1999年美丽过的事物,它们倏然醒活。那些生产线上跳跃过的身影,她们的美丽历经岁月的磨洗丝毫没有褪色。是的,我仍爱她们,那些单纯而热情的姑娘,那些流水线上的花蕾。她们以青春为底料,滋养了这个国家成长历程中最活跃的经济细胞;她们无怨无悔,毫无保留地展现着她们的犹豫和真实。她们的质朴与灿烂,像沉淀在南方大地上透亮的蓝宝石。
据说后来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夏天,在一小旅馆里,杨君通过一番穷追猛打,得到了久违而短暂的爱情,同时献出了自己的贞操。再后来,他具体而现实的愿望一个一个实现了。他穿上了带兜的裤子,他有了他的自行车,他重新有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他在家乡山冈上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宽敞明亮的新窑。杨君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多年闯荡生活的摸爬滚打,让他摸索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生存哲学,他内心欢喜并引以为豪。
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使命,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或许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工业区成为很多寻梦者人生的第一站,很多人在这里重新认识生活,脱胎换骨。但它终究只是驿站,它抚慰不了人们激荡不安的心灵。工业区每天都有新人到来,也有人离去。工业区留下一些人的忧伤,也让他们慢慢地成长,只是,成长过程是多么曲折和漫长。
工厂的生活是机械重复的,是单调局促的。打卡,上班,吃饭,加班,再打卡,下班,睡觉。时间是被限制的,空间也是逼仄的。流水线皮带被旋转阀轮拉得吱吱作响,涂装车间刺鼻的天那水气味泛滥如潮,四面都是拉着铁丝网的高墙,白炽灯成为唯一闪烁的星星和太阳,这样的日子无疑会让一个人陡然生闷。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走出厂门往右拐一个弯,步行数里,独自走上一块隆起而开阔的小山丘。山丘不远处即将修建的一条环城通道已经动工,深层的土壤被翻垦出来,袒露出了赤诚的本色。坡上横列着一片郁郁的荔枝林。采蜜的蜂儿已经归巢,微风轻拂处,轻枝和细叶儿亲密地厮磨着。
伫立山头,感受习习的凉风,哼着跑调的曲儿,或对着远方纵情一喝,听回音袅袅。此时,林子里鸣叫的雀鸟成了我忠实的观众,那些无名的青虫都是我贴心的友人。极目虚渺的天边,一轮夕阳摇摇欲坠。如果铅色的天空是一张铺开的信笺,那么落日必定是来自故乡的一枚红印章;是天涯滑翔的白鹭把它衔带来的吧,那宁静无言的寄意,刹那间把我温情地贴慰。
如果恰巧是周日,我会约三五同事好友,穿过隐在高速路下的一个小涵洞,顺着一条凹凸不平的泥沙路,涉往林山深处。荔林浩如烟海,顺着盘山的小路一弯一拐,嗅着清新的草香,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远离城市的喧哗,暂别素日的枯燥,谈笑风生地回到大自然的怀里,本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我看到路边和野地里,丛生着不出名的野菜与草花;我看到秋收后漏网的红薯,还在土地里挣扎着吐出新叶,它和时间较劲。
在山林的更深处,有两口汩汩不息的水井。一口是人工打出来的,一口是自然生成的,两口井相隔不过百米,前来打水的人络绎不绝。水井带给我永远的遐想和滋养,隔三岔五的,我便会去水井边玩,我要用那纯净的井水,淘洗寄居生活的嚣尘。后来,我写过一首相关的小诗,题目就叫作《井》:
抵达一口井,只需牵出小吊桶
和一根柔韧的井绳
而要捞出井中的影子
水必淹过我所有的脚印
我还未来得及
从水井中取出你所馈赠的珍珠
唱着旧儿歌的雀鸟就已飞走
它们惊颤的翅膀
拍碎了井底波澜不惊的容颜
我将坐在攥满时光苔藓的井沿
看这晃荡的海
正从花季涌向暮年
这时,一种深深的失落和怀念再次无声地将我缠绕。我固执地认为,水井是来自大地的馈赠,有水井的地方就靠近故乡。
除了上面描述到的一切,在工业区的边沿,我还看到很多棚居在荔枝林里的人。他们白天在城市间加班劳作,夜晚才宿身荔阴;他们起居简陋,分住在用石棉瓦或楠竹编饰而成的简易棚子里,拥挤逼仄,随地而安。他们中间,有浑身沾着黄泥巴的建筑工人;有躲避查暂住证的流水线职员或临时工;有卖水果、做小生意被城管驱逐的小商贩;有些是收废品、捡垃圾的老人和妇女,形形色色的“战利品”占据了住所的大部分空间;有些人在山上承包果园,还在林间空隙里种植蔬菜、蘑菇;还有一些人在山坳的池塘里,养殖着成群的水鸭;有一户人家在林子里养猪,几十条仔猪抢食刚刚从工厂回收的潲水料,猪圈的门口盘坐着一条舔着舌头的老黄狗。
这些边缘者,候鸟一样穿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都是我似曾相识的乡亲。他们抛家舍亲来到城里,却一直游离和生活在城市的边沿。他们都是优秀的匠人,他们运用自己娴熟的手艺,把别人的城市养得滋润光鲜,却被拒之千里,遭受鄙视和驱赶。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在城市没有根的人。
夜以继日的工作之余,我在这里给远方的朋友写去信笺;我给家人打电话说自己“过得很好”;我在生产报表的背面,写下漂泊的诗行;我在狭小暗淡的窗前,眺望工厂外面高阔的天空。就这样,在一个叫作赤岭的工业区,我成为一颗钉子,过着机械重复的生活;我挤出了自己的青春,而未来虚渺,春天遥远。
1999年的阳光不紧不慢地挪动着,闪亮着,偶尔夹杂些阴影与乌云。它们照在工业区的上空,它们穿过我年轻的身体,它们俯瞰着工业区生活的真相,并在我柔软的心灵上留下斑驳的投影。随着颜容日损,韶光飞逝,我渐渐觉出一些温和,也有点躁动不安起来。
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的内心里有些惶恐,又生出些莫名的期待,总是思忖着要去做点什么。最后和几个要好的同事相约去工业区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相片里大家不约而同地表情灿烂,笑得甜甜的,看不见一丁点的黯然与愁容。
那天晚上的最后一刻钟,我意外地收到一张远方寄来的明信片。有友人嘱我珍重,愿我平安和幸福。那是世纪末最后最珍贵的祝福,让我由衷地感动和觉得温暖。流乡千里,友别亲离,从此天涯,思恋断肠。那天晚上彻夜难眠,我趴在摇曳的铁架床上抚着这份牵挂,思绪翻越千山万水,心情久久难平。
那一夜,工业区似乎倏地安静下来,整个世界都沉浸在跨世纪的惊喜中。这种惊喜让我沉迷,也让我无由地庄重起来,我特意起身跑到工业区寂静的街道,捡了几片泛黄的落叶夹进日记本里。我想很多很多的节日或仪式,生来就是让人虔诚和纪念的。唯有经过那个庄严的时刻,我们才最终领受一场心灵的洗礼,自此洁净新生。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一刻,我已经在心里酝酿着要离开工业区。是的,我迟早要和它告别。
责任编辑 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