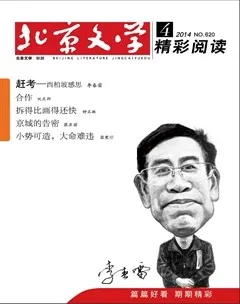小势可造,大命难违
一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是之在《龙须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程疯子。他当时只是一个23岁的青年人,可是演出却“一炮打响”,演绝了,誉满全国,被北京市文联正式嘉奖,奖品是一套灰色布质的中山装。他的表演还被评价为:“这出戏是奠定了北京人艺的基础,也奠定了于是之的基础。”显然,这里是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道路的艺术基础。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那时,是之不但跑到龙须沟边上老街坊们那里深入生活,还要天天都写一篇有心得感受的“演员日记”。由于他非常熟悉城市的平民生活,在排练开始以前就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勇敢地、创造性地写出了6000多字的“程疯子自传”,把程疯子的家庭、地位、经历、文化、性格、思想、感情……一一细致入微地道来,而且交代出这个有钱人“外家”生养的儿子,以及自己母亲的悲惨命运。最后他们又是怎样完全破落下来,他万般无奈地沦落在天桥撂地卖艺,过着屈辱、贫困的日子。因此,真实可信地写出了程疯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个人原因、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这个自传完全可以当作优秀的短篇小说来读,不但受到了导演焦菊隐的充分肯定,更受到了剧作者老舍的高度赞扬。大约,从这个戏演出起,是之就已经算是“成名成家”了吧?
二
然而,好景不长,道路坎坷曲折。仅仅三年以后,是之在《雷雨》中扮演大少爷周萍,由于对生活不够熟悉,难以展开想象力,而碰到了“鬼打墙”。如他所说:“‘程疯子’成功了;后头就是《雷雨》的周萍,惨败。足见演员是骄傲不得的。《龙须沟》里的人物几乎都是我童年时的街坊四邻,《雷雨》里的就不行了,特别是周家的人,他们从未在我的生活里露过面。为了排戏,也找了一家名门望族去看了几次,谈了谈,只觉得听着新鲜,引不起我任何举一反三的想象来。戏组里的同志们也用他们所记得的生活启发我,同样无效。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就像一块湿劈柴,怎么也燃不起火苗来。”后来,戏组的工会小组在每周“工会日”里,都要拿是之当作重点,帮助突破表演创作上的难关,这种“隔靴搔痒”式的帮忙,只能越帮越忙,最后到了无路可走的可怕又可悲的地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是之竟然对导演苦苦哀求说:“干脆你教我吧,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吧!”最为严重的时候,他排起戏来由于紧张而站位不对,导演硬是上场用手大力掰动着演员的双脚,而且根本没有掰动。于是,是之羞愧难当,面红耳赤,连连摇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想想看,是之是一个要求自己很严格,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如何受得了如此的对待啊?在这种情况下,是之完全丧失了排戏、演戏的信心,他甚至出现了要马上辞职,改行去做共青团工作的念头,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块能演戏的材料”。甚至,是之还极为难过地认为“自己这么年轻就成了浮名过实的没有出息的人……”他实在是不肯也不敢再想下去了。此刻,是之在表演创作的道路上,已经跌入了惨不忍睹的低谷。人生莫测,风云突变,确乎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三
有人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很可惜,是之是经过了长长的“六年半”之“冬天”,才迎来了“春天”的。那是1957年,在梅阡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剧本《骆驼祥子》完成以后。是之看了剧本,就热血沸腾,忍不住地跃跃欲试了。他并没有申请扮演主要角色骆驼祥子,而是立即写了申请扮演次要角色人力车夫老马的报告。同时,申请报告的字数并不比老马在戏里的台词字数少,其中已经包括了他对人物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丰富想象和全面理解。是之经过艺术创作上的迂回徘徊以后,终于欣喜若狂地再一次找到了“大海里游泳”的美妙感觉,再一次找到了当年扮演程疯子以前的那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和激情。是之早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住在北京城的—个大杂院贫民集中居住的地方,院子里就有一位拉人力车的车夫,胡同的附近就有—个专门租给车夫人力车用的车厂子。是之正是和邻居拉人力车的车夫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知己知彼,非常熟悉的。那些车夫们有个“请会”组织(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经济互助形式,大家把血汗钱集中起来,以解决穷哥儿们一时的急需之用),一当要发个通知,记记账本的时候,就都要找是之——大杂院里少有的“知识分子”,过去帮忙抄抄写写。为此,是之又一次在深厚生活积累的启发、激励下,全身涌动着饱满的、热烈的、不可多得的创作热情与灵感。他甚至觉得如果不扮演老马,不把这个自己熟悉的人物送上舞台扮演好,那就会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痛苦感觉折磨自己,也愧对当年的那些老邻居们、那些同甘共苦的穷人们。是之所以看中了小角色老马,大约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对这样的人物有着熟透了的生活积累,可以充分展开想象力的翅膀高飞远行;其次,看中了人物身上那些难能可贵的哲理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塑造成能够入诗、能够入画的艺术形象。是之在创造老马形象的时候,真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从外部形象,到内部形象都是如此;从一举手,一投足,到一个表情,一句台词,无不引发出观众的丰富联想和深刻感悟。这个只有两场戏,二三十句台词的小角色,最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艺术容量,是能够写出一篇出色的短篇或中篇小说来的。戏剧评论家称赞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里于是之从生活走到生活,而不是从后台走到前台。他的身后,有着一片可以引人充分联想的生活空间啊。”是之也说过这样十分动情的话:“老街坊车夫老郝叔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辛劳都化为乌有。他奔波一世,却仿佛从未存活在人间。说也怪,人过中年,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一次,评论家问:“比较而言,你更喜欢自己创造的哪个角色呢?”是之想了想回答:“《骆驼祥子》中的老马还好一点吧。”
四
是之乘扮演老马的东风,接着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1958年的春节,北京人艺上演了老舍的新作《茶馆》,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从《茶馆》刚刚交稿的时候起,是之就深深爱上了这部戏,并且积极申请扮演主人公王利发掌柜。他说:“我特别喜欢《茶馆》。它是通俗的、平民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还有,它美。”“我觉得在还能演戏的时候,演上《茶馆》这样的剧本,以后再去干什么别的事,我都知足了。”他继而更十分坦率地表明:“我狭隘地不喜欢高贵的、情节太多的作品;喜欢以性格为主的作品,觉得后者更真实些;不喜欢浪漫主义而喜欢现实主义。因此,在戏剧上,喜欢《龙须沟》《茶馆》。不是不想更开阔些,但始终未能突破。这大约与身世有关。或者可以说,从《龙须沟》到《茶馆》塑造了我。”是之扮演的王掌柜是继扮演程疯子、老马之后,又一次获得了可喜的成功。如果说《茶馆》是一曲人生的交响乐的话,是之扮演的王掌柜就是这交响乐的灵魂。在《茶馆》首演的当天夜里,老舍看完戏以后兴奋不已,回到家中夜不能寐,坐到写字台前大笔一挥,为是之留下了这样的墨宝——“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然而,更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是之收到这条幅以后,竟然一声不吭地锁进抽屉里,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更没有裱起来挂在墙上,连平时接触比较多的朋友也一无所知。而且,这一锁就是30个春夏秋冬,如同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同时,是之却是这样谈到了《茶馆》的艺术魅力之所在:“这个剧本写得‘真’,就像老舍先生为人那样‘真’。老舍先生是结交三教九流的,他是精通世故的,他不精通世故写不了《茶馆》。但老舍先生对人对事又是非常真挚的,我觉得缺少了这种真挚也写不成《茶馆》。一个老人,精通世故而不世故,返璞归真,待人特别真诚,我觉得这种品格,就决定了他写东西不撒谎,不浮夸,不说假话。我们看过老舍先生《出口成章》中的那些文章,他有时不惜用比较刻薄的话反对那些充满生造的新名词、华而不实的文章。由于老舍先生有那么一种品格,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头,就没有故作多情的东西,没有矫饰,没有文字上的做作和雕琢。而且对那种文学现象,老舍简直是深恶痛绝。但评价他的真实,我不愿用‘提高’‘加工’这样的词,倒情愿用提炼或筛选这样的词。他的《茶馆》,真像沙里淘金一样,排除了大量沙子之后,找出了本身就有光的那点东西,他既没有拔高,也没有夸张。……在第一幕戏里,写了清末帝、后两党的斗争,结果慈禧胜利了,杀了谭嗣同。这个‘胜利’,是一个多么残酷、多么腐败的势力的‘胜利’。这是一个黑暗的胜利,腐败的胜利,残酷的胜利。到底用什么表现这个‘胜利’最合适、最形象呢?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听说过什么太监娶媳妇呀,什么某太监真的传了代呀等等传说。老舍先生就用了流传在民间的这些传说来表现这个‘胜利’。一个太监要买一个15岁的女孩做媳妇,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最形象地说明慈禧的胜利是多么黑暗,多么残酷,多么愚昧。老舍先生把这个作为表现后党‘胜利’的情节,这个情节带有象征性。它是现实生活,但看着真有些荒唐。它是荒唐的,但又是真实的。看了之后,那种难过不是一般的。老舍有自己的真实,而这个真实不是一般化的。”显然,是之把《茶馆》辉煌创作成就的首功,如实地奉献给了剧作者。
五
一声霹雳,“文化大革命”似乎从天而降,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它就已经来到了身边。是之刚刚从国外出访回来,下了飞机,就被关进“牛棚”里,行动失去了自由。理由是他属于“公安六条”(当时中央规定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员)上的“罪名”。人艺过去演出的《茶馆》更是成为特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草”,被军、工宣队领导人逢会就加以严厉批判,甚至破口大骂。是之后来说:“对《茶馆》的批判,批判中也点了我的名。我惶恐,我要求自己要‘态度老实’,于是我批判了自己,也批判了《茶馆》。假如老舍先生还在,我会坦率地告诉他这些事的。他将怎么对待我呢?大约是宽容,但我更希望受到他的责备,这于我能够心安。”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之连演戏的资格也根本给取消了。后来,是之自嘲地在叶浅予给他扮演的角色画像上加以说明,三幅画——1948年《大团圆》里拉提琴人;1958年《茶馆》里王掌柜;1978年《丹心谱》里丁文中。“正好十年一幅画,很可惜,1968年由于‘文革’中丧失了创作的权利,没有扮演角色,也没有可画之对象。”更加让人动容的是,是之十分悲伤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才39岁,就让人家从舞台上给轰下来了……当时那种难受劲儿,比让我去死好受不了多少……”
六
1989年,是之已经63岁的高龄,深感过去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再多演几个戏。于是,他毅然主动地申请在我写的《新居》中,扮演主要角色澹台文新——一位经历坎坷的老翻译家。澹台文新被打过“右派”,还因为冤假错案坐过牢,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他不顾年老体衰,依然拼命地把中国汤显祖的古典名著《牡丹亭》翻译成英文,准备推向英语国家作专门的介绍,而且坚持要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与同年代英国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一比高低。这个为改革开放时代唱赞歌的剧本,就是在是之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写出来的,他功不可没。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个受到观众欢迎的戏,刚演出了8场就被上级命令停演了。理由竟然是“剧作者为有问题的知识分子说话,打抱不平”。剧场已经卖出去的票,也让全部把钱退还给观众。是之对此十分不解,我也十分不解,但无奈地只好去执行。事后,上级又改了说法:“这个戏修改以后,还可以演出,并不是大毒草!”是之反问对方:“请你们查查发下来的文件,看看到底是怎么写的?”为了这场演戏风波,是之已经被折腾得心力交瘁,大病了一场。他激动地对我说:“他们真不知道,轻易‘枪毙’一个戏,给创作人员带来的伤害会有多么的大!”何谓惆怅?大约就是一种面对美好事物的流失的无奈、一种面对痛苦又不得不接受的无奈。是之再次深深地感受到惆怅。
七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是之这时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上出现了老年痴呆病(也就是弥漫性脑血栓病)之先兆。具体地说,就是记忆力明显减弱,伴之以越来越口齿不清的毛病。在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1992年7月16日的时候,老版《茶馆》于首都剧场进行告别演出。应该说,这既是《茶馆》的绝唱,也是是之扮演王掌柜的绝唱。那天,不但观众席里坐满了人,就连剧场两边靠墙的通道上也都站满了人。然而,是之几度忘掉了台词。是之说:“两三年前,我就有了在台上偶尔忘台词的毛病,这逐渐使我上台就有了负担。再演《茶馆》,久不登台,我这负担就更觉沉重了。果然,演了400场的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病。我害怕第一幕伺候秦二爷那段台词,它必须流利干脆,前两场就已经出了些小毛病了,那一天就自觉要坏。开幕前,后台特别热闹,院内、院外的朋友们纷纷要签字留念,我就特别紧张。我跟天野同志说:‘我今晚要出毛病,跟你的那段戏,你注意点儿,看我不成了,你就设法隔过去。’天野叫我放心,他说他‘随时可以接过去’。幸亏他有了准备,届时我真就忘了词,他也就帮我弥补,勉强使我能够继续演下去。这以后,不只一处,每幕戏都出漏洞,我在台上痛苦极了。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我得带着满腹歉意的心情向观众去谢幕。我愧不敢当,观众偏鼓掌鼓得格外的热烈,而且有观众送花束和花篮,还有不少观众走到台上来叫我们签字,我只得难过地签。有一位观众叫我在签字时写点什么话,我不假思索地写了一句话——‘感谢观众的宽容。’我由衷地感谢那位观众,他赐给我一个机会,叫我表达了我的惭愧。当听到一位观众在台下喊着我的名字说‘再见啦’时,我感动得不能应答,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爱和严格,从来没想到观众对演员有这样的宽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之说过一句自我调侃又充满悲愤的话——“也许我在舞台上说得太多,老天爷惩罚我不让我再说话了!”
八
在1995年秋天,是之又有一次模仿毛泽东讲话的严重失语。同行者是这样回忆的:“这天晚上宾馆组织了一个联欢会。观众是住在宾馆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一些旅客听说大名鼎鼎的于是之在场,十分希望他能即兴表演一个节目。主持人走到于是之面前说:‘是之老师,您行吗?’于是之答:‘行!行!我今儿行!’于是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著名表演艺术家、全国人大代表于是之先生也来到了咱们这个联欢会场,接下来,请是之老师为大家表演节目!’人们欢迎的掌声是非常热烈的。于是之拿着一个写好的纸片走上小舞台。所谓于是之的表演,仍然是保留节目,用湖南口音模仿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那段讲话。会场上安静下来以后,于是之开始表演——‘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毛泽东的讲话只念了半句,便卡在那里。停了半分钟之后,他静了静心,重新端起纸片,开始第二次试着往下念,但第二次又卡在那里。于是开始第三次念,而第三次只念了四五个字,就念不下去了。片刻之后,他把纸片从眼前挪开,双手垂了下来,十分沮丧地说——‘念不了了……’在场的观众一惊,停了半天,于是之又重复了一句——‘念不了了!’主办方的人见状,匆匆走上前把他搀扶了下来。于是之嘴里嘟囔着——‘这儿灯太暗,纸片上这字儿看不清楚……’后来,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于是之瘫坐在椅子上。几个小时之间,他好像老了十岁,他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完了!这回真的完了!真完了!全完了……’多少年来,我从没看到过于是之的神色那样惶恐。不管我怎么劝慰,他嘴里喃喃着的只是几个字——‘完了!真完了……’夜已经很深了,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突然,他坐起身,眼睛盯着我跟我说——‘看来,我是绝对不能再回到舞台上去了,我完了!’说到此处,于是之热泪盈眶,接着就轻声啜泣起来。”在片刻以后,于是之竟然又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我这条鱼(于)算是他妈的背透了!一辈子走到哪儿赶上的尽是开水!”
九
虽然,是之在坚持表演当中,一再努力失败,又一再不肯服输。表面上看似平静,内心里却从来没有罢休。他与舞台确实有着难舍难分的不解之缘。1996年秋天,是之的戏剧生涯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怎么能够轻而易举地走下献出了青春,又献出了终身的艺术“圣坛”呢?这时,是之竟然爽快地同意了在我执笔的《冰糖葫芦》里,客串扮演一个只有两次短暂出场的、只有几句台词的群众角色。我们选择了和他一起主演过《雷雨》《虎符》和《洋麻将》的老演员朱琳大姐做搭档。他们扮演一对知识分子老夫妻,每天早晨都要出来散步,而且几乎每天都要互相提醒不要忘记带上家里防盗门的钥匙。这天,老先生发现自己的钥匙不见了,很着急,一再埋怨是老伴儿拿错了钥匙;老太太根本就没有丢钥匙,坚持认为是老先生把钥匙胡乱放在什么地方,自己忘记了。经过认真的、风趣的争论以后,在老先生衣服的口袋里找到了钥匙……我和是之商量好:“这段戏的情节比较简单。同时,我只给你写10句左右的台词,而且每句台词都不超过4个字。”他连连点头,表示:“只要这次没有问题,咱们以后还可以接着来!”仿佛眼前出现了能够继续演戏的曙光。那天排练场上的气氛是严肃而热烈的,大家非常关心地来看是之排戏。导演陈颙也格外地耐心,告诉是之不要着急慢慢来,戏不多,很快就会完成。朱琳对是之说:“我已经把两个人的台词都背下来了,万一你忘了,我可以提醒,一定会很顺利的。”是之更是笑着点头,表示感激。他们坐在那里对台词的时候还好,基本上可以丢掉剧本了;站起来走位也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出人预料的是在休息以后,导演进行细致的排练时出现了麻烦——有几句台词是之总是说不出来,特别是“钥匙”两个字老卡住壳。只有四五分钟的戏,硬是排了将近一个小时也不能完整地串下来。可以看得出,别人都没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但是是之的脸色渐渐泛红起来,显然是有些着急。排练场上变得安静极了,大家都有所担心但又不肯吭声,期盼着情况能够有所好转。是之不时皱着眉头,连连地摇头,样子显得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尴尬。越是心急就越是说不上台词来;越是说不上台词来就越是心急。导演想缓和一下气氛,让大家休息一会儿。在休息的时候,不幸的事情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是之突然有些激动,手在发抖,站起来用很不连贯的语言,对自己,又对导演说:“我是有病……不然……这点儿戏早就排完了……你们着急,我更着急……我耽误了时间,实在对不起大家!……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到底该怎么办呢?……”导演赶忙解释:“你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千万不要着急,今天排得基本上差不多了,再从头儿顺一顺就可以过了嘛。”吃午饭的时候,郑榕和我以及陪同来排戏的是之夫人李曼宜,把包子和稀粥端到是之的面前,劝他吃点儿饭,先休息休息、放松放松。是之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不肯吃饭,也不吭声。他的脸色苍白,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楼窗以外很远很远的地方,心潮翻滚,痛苦已极……这时,我想起了是之不久以前,在他楼上书房窗子前边说的话:“我好几回都想顺着这儿走下去!”
十
如今,是之和林连昆都已经辞世,这里是他们生前的一个“镜头”——
在是之住医院期间,一天,他在电梯间里意外地看到了同样来住医院的林连昆。两个人相对无言,很久很久,一个是说不出话来,一个是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四只眼睛互相凝视着,心里都有说不出,又说不尽的话……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位的表演风格是很相似的,又是取得巨大艺术成就的好演员。是之曾说:“我的表演,只有林连昆能够说得清楚。”医院里这最后的一幕,没有任何语言的一幕,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
是之很喜欢表演,一生的最大愧疚就是没有把戏演到底。他也很喜欢书法,在晚年曾经写过两幅墨宝——一幅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一幅是“留得清白在人间”。或许,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声吧。
只有能够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也许才能懂得什么是生命。
是之说:“人的性子就是命,咱们不能和命争。”
人有命运吗?有时候,命运是很不公平的。人们在命运的随意摆弄面前,常常是无能为力的,很无奈的。真是——小势可造,大命难违啊。
人生的许多道理是在你经过以后方才知道,那已经为时很晚。大约,这就是我们永恒的惆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