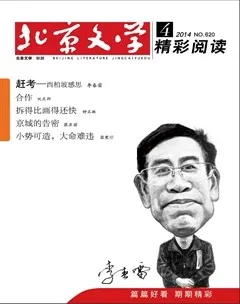人活一张脸
1979年,我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老师说,重点高中是县里的最高学府,这里的学生相当于古时的秀才了。回到村里,我不知道向大人们打招呼。有时,看到村头有很多人,等到天黑了再回家。更害怕见到村里的老师,不知该说些什么。爹狠狠地批评了我。从此,我不再躲避。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我见了村里人都会主动打招呼。哪怕离我很远的人,也要走过去,递上一支香烟,问一下家长里短。爹说,儿女就是爹娘的脸。儿女把事情做排场了,爹娘脸上也光彩。
我很喜爱徐怀谦的一段话:“老家,承载了我童年的梦。犹记夏夜乘凉时,躺在庭院里的草席上,看繁星满天,听知了鸣唱,长辈们叼着烟袋,火星明灭间,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懒婆娘的故事,讲孤魂野鬼的故事。也许太有趣了,风也赶来偷听,蹑手蹑脚的,听了几耳朵便窃窃私语着离开了。老家,因了父母的存在,挽系住了一颗游子的心。”
在村里,谁家有红白事,大伙都去帮忙。农村人最朴实,最实际,人与人交往也讲究礼尚往来。过去礼金10元、20元的,如今都是100元、200元的,水涨船高嘛。我对这种交往明白得太晚。以前,只有亲戚家有事,我才参与一些场面。那年,爹因病去世,村里来了许多人帮忙,我很感动。娘对我说,不是冲着我来的,村里来的人是爹的面子。爹与村子里很多家都有来往。那之后,村里谁家有红白事,我都尽量到场。即便请假,也要回到乡下,给事主家帮忙。实在到不了,给事主家打个电话,说明不能回去的理由,取得当事人的谅解,让家人把礼钱先给我垫上。
县里曾流行一个局长的故事。说某局长回到自己的村庄,都是坐着小汽车一溜到自家门口,即便见了村里人也不递香烟。有人到局长家里,局长的夫人也不给做饭。局长的爹死了,局长不去给村里人磕头,没有人去帮忙。最后,在族人的数落下,局长逐一给村里人磕头,村里人才答应去帮忙。不管你是哪一级的官员,在村里人面前,永远不要有官架子。项城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老家,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袁世凯回乡省亲,到了项城地界,下轿,步行到家。
人生存首先要的是基本的温饱。这是出自人的生理本能,是自然的有充分理由的需求。如今,农村生活也好了,谁家摆几桌酒席都不是问题。儿女婚事,从提亲到迎亲,要“六礼具备”。每一项议程主人都要招待,都要喝酒。喝酒就要有氛围,有场面人物作陪。自家一家人关起门在屋里吃喝,要被人笑话的。被请的人都是关系要好的。如果甲的儿子结婚请了乙,乙的儿子结婚却没有请甲,甲就不高兴,二人的关系就要疏远。就是一般的人家也要请行政村支书、主任、小组长作陪。我也多次被人请去作陪。酒席上,只有辈分,没有官职大小。即便在县上当一个小官,也不要显摆。最好不要喝醉,喝醉了要被人笑话。我老家的村支书,干了30几年,德高望重,谁家有事都请他,他都去,但不喝酒。喝酒不醉才是雅。
不要小看农村人的这种交往。不光是面子的问题,更多的是承载着一家人的幸福。上个世纪的某个特殊时期,上高中、参军、当干部时兴推荐,与干部是亲戚或关系好,就会被推荐。上学和参军是农村娃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上辈人的友谊,也是下辈人的幸福。感叹人生,如今就是考公务员能没有情感因素吗?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全在于他的工作认认真真,有大部分在于疏通人际关系,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会碰得头破血流。
城市里结婚可以大操大办,尤其是当官的家里办事,可以收礼,变相受贿。城市里结婚也可以简办,那叫移风易俗。但农村与城市不一样。农村的红白事就是联系亲情的平台,考量着一家人的道德品位,也考量着一个家庭的影响力。民俗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需要传承和发扬光大,而不是阉割和舍弃。
人活着,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有情感的交流。说到底,人是为感情为面子而活着。
责任编辑 张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