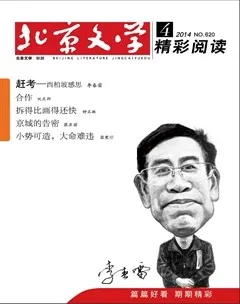小说之外的刘庆邦
刘庆邦的声誉源于他的小说。写庆邦即使无力评价他的作品也应该说一些他和创作有关的事,比如他出版了几百万字的小说,获得了多少多少文学奖项,或者大年初一仍然埋头写作什么的。可晓升主编给我派这个活儿的时候,要求我把庆邦写得好玩点儿。这样,我上面的想法就不合适了。想了想:一个作家无论写出过多么伟大的作品,其写作过程都不可能是一件好玩的事。把不好玩的事写得好玩不是不可以,太可以了,只是就我自身的能力而言,有些费劲。所以还是避重就轻,把小说放远点,单说说小说之外的刘庆邦。
我和庆邦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候他就是我的师长和兄长。现在还是。20多年的交往中,我坚持不和他开玩笑。但不开玩笑并没影响我们一起做一些好玩的事。比如我们一起采风,一起出国,一起开会(这个不好玩),当然最多的就是在一起喝酒。
庆邦能喝酒。能喝酒的人很多,不同的是,庆邦能用酒把情绪压住,他是那么从容,那么安静,不像我等之人几杯下肚就开始躁动。酒桌上的庆邦一点不闹,也不叫着号地拼酒。不温不火,张弛有度,其风格,说白了就是一种享受的节奏。其实还不仅仅是享受,我觉得他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境界。有段时间,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点状况,好像血脂高吧,他伤感地说,医生说不让我喝酒了。没等我回应,他又一脸惆怅地说,不喝酒哪行呀。那天晚上他照喝不误。像往常一样,先是来者不拒,后来便转着桌子去回敬,一个一个地敬,亲近着,和蔼着,依然是那么豪爽,不仅杯杯见底,还要不时地发一声感叹:好酒!
常在一起喝酒的朋友,都说从没见庆邦喝醉过。其实我见过。有一年在外地开个什么会。好几桌人,是怎么喝乱套的就不说了。喝完了还搞联欢。联欢挺好的。庆邦擅舞,什么交谊舞迪斯科,都行,可劲儿跳呗,还解酒。但有几个想让他出洋相的人不让他跳,让他唱。他唱的是李叔同的《送别》,声音不大,一咏三叹,长亭古道一遍遍送,送得难舍难分。关键是他还一手拿麦克一手捂着半张脸。当时朋友们都觉得特有意思特好玩,说庆邦老师这次可喝大了。大就大了。那毕竟是在煤矿。大凡到过煤矿的作家,没喝大过的可能也没几个。
其实庆邦就是个煤矿人。从煤矿走出来的作家挺多的,陈建功,谭谈,孙少山,周梅森,谢友鄞等。遗憾的是浅水养不住大鱼。这些成名的大家儿都相继离开了煤矿,几年前庆邦也调到了北京作协。人才流失啊,说起来就感慨就心酸。好在这些离开煤矿的作家没有疏远煤矿,他们对煤矿的文学事业可谓有求必应。单说庆邦,他每年都要到煤矿去走几趟,短时三两天,长则半个月,且与矿工同吃同住。此外无论到了哪,他都要到井下去看一看。实话实说,哪的煤矿都差不多,无非就是钻地球,打眼放炮做支护,铁皮溜子拉大煤,矿工兄弟能战斗,一身汗水一脸黑。要是个首长什么的,到矿井里看一看可能还有点教育意义,一个曾在那种环境里摸爬滚打过的人看什么呢?可庆邦总是要看。如果因为时间不够下不了井,他整个人都发蔫。有一次,我们在乌达下矿井坐的是猴车。我也是煤矿人但没坐过猴车,不知道怎么个“猴”法,踌躇间,只见庆邦已经抓住一个由上而下的猴车,两腿轻松一跷,便熟练地骑了上去。然后悠然而下的同时,还不时地与对面升井的矿工打招呼,声音比酒桌上要宏亮。我想不明白,一个写过那么多煤矿生活作品的作家,一旦到了煤矿,他咋就那么兴奋呢。
文学圈里有许多人喜欢打牌。我曾见过几个作家在飞机上还打得急赤白脸。我不打,主要是不喜欢。我曾跟那些喜欢打牌的朋友说过,我坚决不打牌,如果你们非让我打点什么,我宁可打人也不打那个玩意儿。不过我还是打过一次。那次有庆邦,好像还有徐坤徐迅或者其中一个是魏微,记不清了。总之他们是三缺一,玩不起来,于是便勒令我充个数。我充了一会儿,庆邦高兴得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他说永鸣会打牌!可不一会儿他又失望了,说永鸣的确不怎么会打。我就偷着乐。别人打牌都是挂点彩的那种,庆邦打牌是干戳手指头。但他依然打得兴致勃勃,甚至到了迷恋的程度。据他自己讲,一旦抓到一手好牌,比如两个大猫什么的,他就会手心出汗,热血上涌乃至于心跳脸红。又据周晓枫描述,她说庆邦老师打牌的时候特好玩儿,那么多张牌拿在手上,每张牌之间的距离都相等,摆得溜齐儿,他一边看着牌,一边皱着眉头作思考状。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在玩上都能做到这么认真细致,他还干不好用来吃饭的活儿?
再说个喝酒的事儿。那次我们在楼上喝完白酒,又聚到楼外的湖边儿上喝啤酒。湖边是草坪,还有树;来的时候看见湖里有水鸟和黑天鹅等一些美好的事物。现在天黑得啥都没了,就光是喝酒。后来酒也喝散了,就有人在草坪上溜达,还有唱歌的,聊天的,嘻嘻哈哈。后来就有保安像一根棍似的站过来说,请不要大声喧哗。再后来,好像把湖边的灯也关了。当时天上有没有月亮忘了。其实有没有月亮都问题不大,我们又不是李白。我们是一帮煤哥们儿,我们是当代的普罗米修斯,通俗地说我们就是给人类以光明的太阳。喝点酒怎么了?不行呀?于是又接着喝。喝了一会又开始乱。这时候庆邦不让了。他也没说不让乱。他说我有个提议,请大家闭上眼睛,静默两分钟,然后我们就散好不好?好!他说开始!于是这个世界一下就安静了。感觉上我似乎回到了遥远的童年。这个由庆邦营造的时间与空间太广大,也漫长了……事毕,旁边一个女的悄悄问我听到了什么。我想了想说,挺抽象的。
拉杂了这么多,如果我说这些事和庆邦的小说创作没有任何关系,谁信呢。
责任编辑 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