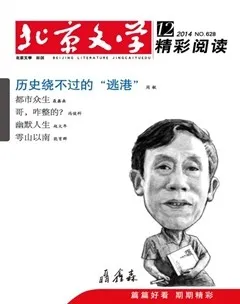好大一颗泪
霜
一母所生,不敢以姐姐,向花间晨露相称;更有谁怜,那份凛然,只是季节的惶恐。
山丹
红透了,是一茎茎艳丽的芭蕾。她不上莫斯科的舞台,更不添巴黎少妇的艳腻;她生在山顶的北坡,最先向夏季角度最低的晨曦,展示那富于灵异的美丽。
山菊
开在山场,摇曳风中,是一簇簇星;有白,有黄,有蓝,还有一种似轻喷浅洇出来晕晕的红;手集盈握,像抽自万花筒;去梗入臼,捣作糜齑,裹布细拧,聚汁以澄,点入兔眼,无论外创,无论火发,其目自明。
——山菊呦!童年的稔熟,今儿几乎把你忘个干净。
萝卜花
寒冬枯景,难耐的寂寞与孤独。父亲去串门儿,我作小狗样儿跟着。在那土屋的门前,白灰剥落,黄泥斑驳,阳光照上去倒像是暖洋洋的。主人把一根粗壮的白萝卜,横挂在墙上。萝卜的背上,看是挖了道水槽,六七茎蒜苗,绿盈盈地生在上边,萝卜却向上弯着头,长出尺把长的嫩茎。茎上耸着挤在一起的一大串花蕾,细若小米璀璨金黄,在阳光中闪着莹莹的水鲜。我欣然伫立,——不曾想晚上它被吊进黑洞洞的土屋里,会是什么光景?当下就只想——把自己的心也挂在上边。
花事
扯开淡淡薄雾,觅春需往远处,过了几道山梁,方见深坳几处:山桃缤纷,杏花迟露,村姑不应有问,东君自知失手。待得村头杏花时,落英纷坠,桃红方吐……黄莺未肯归顾,低枝短墙,麻雀争逐。
秋风
落入怀中,去了点闷浊,添了些伤情。洗过长空,白日孤零,云丝挂不住,险些跌落苍鹰。
炊烟
那是田园风光的古韵,你不能身临其境,感受它淡淡的微醺,那种说不出的最原始的感伤,便无由回忆。
晴晨,风静,潮气亦浓,炊烟不起,在村头,如云丝一样绕树。
日午,天燥,热气下泻,直压得烟气翻卷,弥漫于灶间、院舍,便是往烟囱出来,也只在热浪滚滚的房顶打转。
只有傍晚无风,日朗气清,地面的热量向上蒸腾,炊烟才会随着向上的气流,袅袅直升。一柱,两柱,三五柱……古人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才是真时真境。
蝴蝶
白色,翩翩的,让人想起孀居;黑色,闪闪的,让人想起坟地;而那种蓝色的小东西,飘忽在荆棘丛生的沟崖,更给荒古的山野,穿引出游丝如缕的妖味。
狗叫
童年的狗叫,有时是那么温馨,它告诉我叔婶哥嫂们来串门儿;少年的狗叫是那么伤心,英武高大的父亲,让人扭出家去上会,门上还挂起了白纸做的牌子;中年的狗叫更让人烦心,征粮缴税的干部,撬开闩紧的大门,还把砖头从窗口掷进了屋里;昨夜的狗叫恁地嘈杂,天明才知道,“120”拉走了醉倒的街邻。
家乡
没到过我的家乡,您不知道我的家乡。童年的贫苦,也充满着喜悦,少年的风雨,也飘着鸟语花香。田埂上,小伙伴扬着手奔跑,蒲公英种子,雪白也似绒花一样,在春光里飘荡。清清的溪水,滋润着满坂的新绿;弯弯的河浜,流淌出五月的槐香。家乡的猫头鹰,就叫“呱呱呦”。没住着老鸹的人家,才显得枯丧。紫花布大袄,是乡亲们的质朴,千百年小米谷子,是乡俗的淳良……没有到过我的家乡,想您知道我的家乡,那山,那水,那牛,那羊,四季轮回,风儿扯着童年的情肠。
责任编辑 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