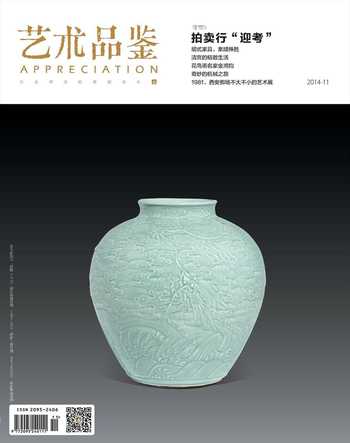美人如玉 清风与归
陈一清
2005年秋末,我从安徽屯溪回东至,途经祁门大北埠好友陈清明处,清明君以此物出示,大契我心。开脸之美,摄人心魄,迥异晚清民国牙雕仕女之俗态。“真的看到了诗书浸润的风华。”晚明的感觉一下子袭上了心头,从此再也拂之不去。
清明君不久举家迁往屯溪,并欣然将此物借观于我。没有了牵挂,激情变身为理性。细细把玩,略显头大于身,明显受到明代万历时期版画的影响,身材过度修长而呈现出大头仕女,彰显出明代工艺的特征。洗炼的刀工无半点拖沓,流淌的衣纹有一种肥诺诺的味道,如望春花厚厚的花瓣,折射出明人一抹柔婉的目光。云髻堆翠,香肩如削,不禁让人浮想起杜子美“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的诗意来。最动人的还是那似笑非笑的桃靥,一种找不到形容的感觉,平生第一次感到文字失色的无奈。连雅昌艺术网雕塑版的沙子版主也觉得“太美了”,更有网友直呼“明风外泻”。呵呵,好的东西看来是不乏知音的。安徽省博物馆《鉴宝江淮行》来池州,言是明末清初之精品,后在相关资料上定为雍正,严谨之风现在看来已属难得了。细细对比,还真的像焦秉贞笔下的仕女。
明徐渤《红雨楼题跋》:“画家人物最难,而美人为尤难。绮罗珠翠,写人丹青易俗,故鲜有此技名家者。吴中惟仇实父、唐子畏擅长。” 明中叶以后,仕女画才真正步入高峰期。唐六如的端丽,仇实父的华美,文衡山的飘逸,乃至陈老莲的高古,可谓名手辈出,一时龙象。
窃以为,明人仕女画之所以有如此的成就,其实是文人画者自己内心的一份优雅。流风所及一、二百年,以致秦淮河流淌的不再是胭脂铅粉,也散发着一缕诗书的清香,才有了柳如是、李香君丹青一样的艳色、文士一样的情怀。是诗书涵养了秦淮,还是秦淮润泽了丹青,仿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画里画外都共同走向了时代的鲜活,给后世文人以无限美好的追慕。仕女画清中期以后就没有多大看头了,一种美人迟暮的感觉。雍正时焦秉贞的笔下尚能见到一丝明人的影子。改七芗之下一味病弱,仿佛看到的全是汤药,没有了血脉,真的是潇湘馆中的林妹妹了。江河日下,到了晚清的钱惠安更是不堪,彻底村姑化了,直到民国以后仕女画才有了像样的一振。
记得一位画画的朋友说,画柳要心中无柳。柳本柔弱,以阳刚之气画之,反倒得婀娜之态。一位收藏佛像的朋友说,观音得男像才美。唐宋的观音造像雄伟雍容,那才叫气象。阴柔阳刚之,泥污高华之,实乃中土之大道,丹青莫不然之。“秦淮八艳”若无诗书诸艺的浸润,岂能风流百代,不过是几株风尘败柳,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晓风残月之中。
题扇仕女体裁多见于明清牙雕。一手持笔,一手持折扇,作觅句诗思状。笔与扇为活动配件,可以安上也可取下,故流传日久多散失不存。题扇仕女以我拙见,应源于红叶题诗。朱力先生《明清古玩真赏》辑录的明朱小松款《秋叶题诗》竹雕笔筒,所刻仕女与此极类。折扇又叫撒扇,本东瀛物,明代永乐年间朝鲜国入贡中国的。明代中期,苏州折扇附丽书画,精工细作,成为风靡一时的“怀袖雅物”。以扇替叶,估计与当时流行的时尚有关。此件笔、扇皆失,然七寸来高的大小最适合把玩摩挲,盈盈一握,便有一种“美人如玉,清风与归”的感觉。
好友清明君也不催要,以致此女子在我家足足小住了三年。难得的是清明君仍以当初所出之价易我,得以正式迎娶。我开玩笑,可见过我这么痴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