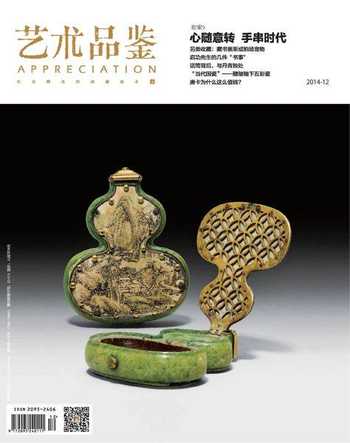话筒背后,与丹青独处
蒙海虹 张珍珍



2014年5月,对于刚刚过完50岁生日的朱军来说,确实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作为全国观众最熟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又饰演了人生中另外一个崭新的角色——画家。
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画学会共同主办的“杜蘅情怀——朱军绘画作品展”于5月17日15时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巡展帷幕。10月6日,古城西安的西安美术馆也迎来了朱军绘画作品巡回展的第三站。参展作品是朱军近年所作,包括人物、花鸟两个系列。人物画以西藏风情人物为主,这是他在西北生活多年内心感受的表达,其中《康巴一家人》更是他对和谐社会以及中国梦的写意,人物眼神中无不表达出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花鸟画是他对传统中国文人画的继承和创新。同时还有朱军临摹中国优秀的传统作品如八十七神仙卷、永乐宫壁画、敦煌壁画等。
朱军说:“我是西安女婿,来这里不知道多少次了,但这次不一样,第一次带着画来陕西这个文化大省亮相,就像是来考试一样。”
《艺术品鉴》杂志记者有幸采访了朱军老师,与他一起笑谈主持背后的丹青生活。
:朱军老师,您好!在我们眼里,您一直是一个成功的节目主持人,而这次来西安办画展,您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朱军。作为主持人,您的工作繁忙、辉煌,充满喧嚣;而作为一个画家,您则需要安静、平和的状态。您在这两个身份中的转换可谓得心应手,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朱军:可能在热热闹闹的场合里待的时间长了,我的内心就特别渴望那份安静。人往高处走,可是高处不胜寒。水往低处流,谁知低处纳百川。我想要的或者说我更渴望这样一种海纳百川的心态,其实这样的心态也就是静得下来,耐得住寂寞的一种心态。对我来说,我特别享受这样的一种沉静下来的状态,它跟热热闹闹、灯火辉煌的场合是一种互补。比如主持春晚,一定得情绪激昂,饱满热情,要调动现场的气氛。但实际上,你想一下,作为一个具体的操作者来说,这种情绪沸腾后,总要有一种办法让他冷却下来。对我来讲,绘画恰巧是让我冷静或者冷却下来最好的方式。而且绘画的时候,我不用打扰任何人,直接和宣纸对话。无论什么样的情绪,即使垃圾情绪,我都可以宣泄在纸上。
就像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5月18号,中宣部搞赈灾义演,那场演出,平心而论,是我主持的所有演出中最累的一场。我指的是心累。因为在演出现场,有很多身在第一线的抗震英雄和受灾群众,他们经过了大悲痛大灾难,和我们面对面站在一起。就拿蒋敏(汶川地震,最坚强女警)来说,当时,她整个人是飘着的。好像大灾之后,所有人的悲痛一下子都没有了,我问她地震的时候,她的家里多少人遇难?她说九口人。她的这种平静反而让人受不了。所以那场晚会基本上是在台下痛哭流涕后,上台说一段话,然后下台抱头痛哭,再上台说那么一段话,特别累。而且义演时间又特别长,一直到十一点四十七分直播时间才结束。本来时间还要长,但因为过了十二点,就是国哀日。国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
我主持完回到家,十二点多,躺床上睡不着,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失眠的日子,一直到凌晨四点多,还是睡不着,就干脆不睡了。起来之后,拿起一张纸,我就开始画,也不知画什么,画笔随心而走。画了一片废墟,然后中间画了一支鲜花,画完之后还不过瘾,就给上面甩了很多斜点一样的东西,然后题了一个名字叫“生命礼赞”。后面我记录了一下这个事,大意是公元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及周边地区发生了8.0级地震,5月18日那天中宣部组织义演,席间宣布19号到21号为国哀日,中国所有省区及驻外使领馆届时将降半旗默哀,船舶码头鸣笛、致哀等等。这是中国第一次为她的平民百姓俯下她的头颅。写此以记之。画完了,心里就舒服点了,一直压抑的情绪宣泄出来,也放松一些,然后躺床上,睡了。所以我觉得绘画就是我情感的一个出口。
:动静结合,绘画和您的工作真的是一个互补。
朱军:是啊。我干的是综艺主持人这个工作,这些节目的场面都是锣鼓喧天、灯火辉煌、热热闹闹的,可以说我几十年的时光都献给这样的场合了。但我的内心,在某些时间,可能更渴望回归平静。对我来说,绘画首先是可以让我一动一静、调整自己的最好方式。其次,在绘画的过程中,就是在所谓与艺术“独处”中,我很享受,这是一种快乐。而且我发现自己在不断地变得更丰富,绘画也让我体会到“成就”的快乐。所以在画册后记《学着与艺术独处》中,我写到:“到了这个年龄,所谓知天命之年,我希望把责任留给电视屏幕和真实的生活中,我希望在绘画的世界里再做一回少年,信马由缰,肆意挥洒,按照天马行空的精神画出一个我另外的人生。”
:挥毫泼墨,抒发情感,快乐并充实着。
朱军:对,实际上我的画就承载着我内心的情感。尤其是画人物的时候。比如说我画《母与子》,脑海里想的就是我的母亲。我在想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在领我去看病的路上,花五分钱给我买一碗油茶吃,她自己舍不得吃,吃完后领我打针,然后带我回家。我的母亲即使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她也从来没有弯下过她的腰杆,她永远乐观地面对生活,这在我的印象里非常地深刻。我在构思这幅画的时候,就想让画里的人物背负一个东西,以象征着生活的压力,但这个东西又没有把她压趴下。所以我给画中的母亲身后画了特别大的一个大筐子,筐子已经巨大到和人物不成比例,尤其放在在现实生活中,更是不成比例的。但我把它放在画里头,旁边画一个小孩,别着脚,抓着母亲的手,头依偎着母亲,母亲看着远方,带着慈祥灿烂的笑容。画好那天,《中国新闻周刊》的社长刘晓青来了,一进门就看到画墙上那幅画,站着看了很长时间,真的,我就看着眼泪从他的眼角流下来。他和我同岁,他说看到画,想到的也是他的母亲承受的那种生活的辛苦和压力。然后他跟我说画中那个筐子勒在“母亲”的肉里头,“母亲”手垫在筐子那里的那个感觉,那些细部特别能够打动他。他看懂了,我很欣慰。这就是我的画。
:绘画之所以能成为您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可能和您小时候的一些接触有关系?据我们了解,您的绘画,也是有着“童子功”的基础。
朱军:“童子功”谈不上,但的确接触比较早。上中学的时候,美术老师对我和班上另外一个维吾尔族同学,可能觉得我们有点天赋吧,比较偏爱,老给我们两个人加小课。每天下午四点多放学,他就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或者宿舍,从画鸡蛋开始,然后画几何体、画石膏头像,画素描速写,就这么一点一点开始学。我们学校的大礼堂里有一张毛泽东主席的标准照,就是美术老师带着我们两个学生完成的。其实也没干什么,我们画衣服,就是老师把颜色调好后,我们往上抹。但这件事对于当时还是孩子的我来讲,很重要,也很激励我,就好像那时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认知绘画并且喜欢。所以有次书画频道的主持人采访我时,问我:“您拿话筒多少年了?”我说“小三十年了”。他说,“拿画笔呢?”我说“小四十年了”,他非常惊讶。随后我说“我还没说完呢,括弧,如果不间断的话”。
后来我当兵,从事文艺工作,又从相声改到主持,整个过程漫长、无暇他顾,把画笔也就放下了。直到十年前,可能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性情慢慢稳定下来,包括家庭、生活、事业等等,基本都稳定了,又开始拿起画笔了。
:这个阶段,您临摹了大量的传统绘画作品,并以国画作为自己主要的创作形式,这里面是否包含了您对中国古代文人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朱军:不敢这么说。我并不是有意的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是觉得经常绘画,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让我很惬意。我画画,是因为我感到愉快。当我坐在书案前面欣赏我完成的作品,我会觉的“哎呀,画了这么一张好画,这一天真没白过”。绘画就是这样能给我以愉悦。
:在这个临摹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画作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朱军:首先我觉得人不能没有根,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根。就像倪萍主持的公益节目,《等着我》,央视1套晚间播出的一个找人的节目。节目里有好多人,他们被遗失或者被拐骗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家在哪。虽然他现在在这个家庭生活也很幸福,但是他就是要找他的生身父母,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本能,人要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我临摹传统国画就是这样“寻找自己的根”的过程。当我临摹完《八十七神仙卷》的时候,我对中国画的线条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了。甚至于我看自己画的线条时,感觉也完全不一样。原来的线条,虽说过得去,也比较流畅,但临摹完一遍后,我发现自己画的线条更有弹性,也更立体了。临摹八大山人的画,也是慢慢走进他的作品的过程,更可以切身体会中国文人画蕴含的那种情怀。似乎我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又活了一回,似乎体会到了一个明朝贵族在清朝生活时,他那种落寞的心态。你仔细看八大山人画的鸟,不是瞪着眼就是闭着眼,画的那个树什么的,也给人以飘零孤傲的感觉。所以我说临摹传统作品实际上也是在寻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更何况在寻根的过程中,在一遍又一遍的临摹中,绘画的本事也增长了,包括对意境和构图的把握,都在提升。
我这次展览,就专门展出了几张我临摹的画。像永乐宫的壁画,敦煌的壁画,还有虢国夫人游春图,八十七神仙卷等等。之所以展出这些,我也是想告诉大家,我在寻找中国文化的根脉。在中国美术馆巡展的时候,范馆长提议说这里写一个卷首,字数不要多。我写了卷首,大概这么个意思:这些古画实际上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密码,破解它的方式只有一个,一笔一划的去临摹。临着临着就会走进它们,一旦走进这些古画,它们会安抚在现代生活中或许困顿迷茫的灵魂。我觉得这就是寻根的意义,当你把根找到后,你可能就不再困顿,也不再迷茫了。你会更清醒,我觉得从情感上来讲是这么一种体会。从绘画技巧上来说,真的很多方面我们的先人已经做到极致了。只有老老实实的跟着他们学,才可能有所掌握。这种敬畏、临摹是永远的,我现在还在坚持。
:我们知道您是师从国画大师范曾先生的,是怎样的机会让您与范先生有了这段师徒缘分?
朱军:其实是一个很巧的机缘。六七年前,范先生六十九岁,准备过七十的生日。有一天,姜昆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跟他去一趟范先生家,说先生准备办一个寿宴,庆祝七十大寿,想让我去帮着策划一下。那天先生带着我参观他家里的一些陈设,从画室走到他的小书房聊天,先生问我,“喜欢做什么”,我说,“喜欢写写画画,不过到了您这儿,我也不敢说这个话”。先生说,“那过几天你拿你的作品来看看,给我看看”。我说“行”。我们就这么就聊着聊着,不知不觉的过了一两个小时,直到姜昆进来找我们。
吃完饭,先生的几个博士生来上课,我就在旁边听。听着听着,肃然起敬。我就觉得这个老人家,不只是我印象中的那个画家,他的学识尤其是他对国学的掌握,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你随便问什么,他好像都在肚里装着,谈古论今。这让我非常佩服。这就是我对先生的第一印象:很随和、很健谈、很博学。
从范先生家回来后,过了一个星期,他身边的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是范先生邀请我去家里玩。一来二去的,一晃,一年就过去了,这一年我没事就总去先生家。有一天,我带着我的一张画儿去范先生家里,先生看了说“你这结构布局还不错,但笔墨上还得下点功夫”,然后先生给提了跋,这让我受宠若惊。
后来到了08年的3、4月份,范先生应邀给人民大会堂画一张大画《唐人诗意》,这是张巨画:十一张丈二的画纸,连在一起,有十多米长,五六米高。我观摩了先生从头到尾完成这张画的整个过程,他从一个高士的头部开始画,到完成这整张画,用了三天时间,一笔铅笔稿都没有打。这当时给我的震撼太大了,真是让我由衷地佩服。
大会堂为了表示感谢,请先生吃饭。先生也叫上我了。席间,我看到先生很高兴,就有了一个想法,跟先生提了一下看能不能收我做徒弟,但当时范先生没有答应,把这事岔过去了。过了几天,我还在想拜师这事,因为这话都说出来了,不再努力一下,我还是不死心。于是我就跟我师娘说我想拜在先生门下做徒弟,没有别的,就是想学习,请师娘做做先生的工作,师娘当时也答应了。
这一说又过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先生给我布置了一些作业,比如说临摹一些中国古典绘画作品,像八大山人的作品等等。我将那些作品认认真真临摹后,拿去给先生看,先生看了就很高兴,而且全都题了跋。后来,先生让我临摹《芥子园(画谱)》。回来以后,我就找了一大卷的皮纸,有二十多米长,一段一段画,临摹《芥子园》。直到我把这卷纸画完,拿去给先生看,先生很高兴,给我题了一个一米多长的长跋。
这么一来二去,过了挺长一段时间,我都快把拜师的事情忘了。有一天,我师娘跟我说,“你上次说的那件事,先生同意了”。我还问“阿姨,什么事儿?”阿姨说,“你上次不是说想要拜师吗,先生同意了”。我可以说是欣喜若狂啊。后来,在08年的4月份,就在先生的家里,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拜师仪式,我正式拜范曾先生为师。拜师后,过了一段日子,我问先生,“您怎么就想通了将我收做关门弟子呢?”先生说,“很简单,首先你在主持人这个行业能做成这样,说明你是个聪明人,因为笨蛋也做不成你这样。第二,前面那段时间,我给你布置作业,让你临摹传统作品,你临摹了;尤其有些线描的作品,你也临了,说明你还愿意下笨功夫。一个聪明人肯下笨功夫,这事就比较靠谱。”就这样,我就拜在先生门下了。
:你和范先生之间就是一个互相认识互相赏识的过程,而且真诚有感情,令人羡慕。
朱军:真的,有时候老师的点拨我觉得特别重要。中国画,线条是基础,或者说是基因。范先生,毫无疑问,是把中国绘画的线条运用到极致的人。他的画的线条,那真是不能再美了。实际上,在跟随先生学习的过程中,先生对线条的掌握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先生在教我们绘画的同时,也在带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向中国文化的更深处。这让我受益良多。即使教授绘画,先生也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这一笔该怎么画,那一笔该怎么涂。他只告诉我们这张画差在哪,画的气象不足,毛病在哪。
比如有次我在先生家画画,他说“画的挺好,但是还差口气”。我说“这口气在哪?”他说“为师且给你改两笔看看”,先生拿起笔,蘸点儿墨,就那么淡淡抹了几笔,画就不同了,一下子我就就知道这个画的气象在哪、韵味在哪。为什么这么画,就活了,那么画,就死了。先生就是这么点拨,我们茅塞顿开,受便益匪浅。
:除了范先生,您在书画界的良师益友应该非常多吧!
朱军:是的,在学画的路上,我很幸运。除了我的恩师范先生之外,比如说康宁先生,他也是我们中国顶尖的国画大师。我拜了范先生之后,先生曾经当着我和康老师面说,“朱军除了喜欢画人物,还画一些花鸟。他在花鸟方面呢,康老四(康宁与范曾为同门师兄弟)你好好带带他”。康老先生对我,真的跟对待徒弟是一样的。还有刘大为主席,冯远老师,都给过我特别具体的指导。我觉得这个和我先生教授我的知识是互补的。范先生就从来不给我具体的指导,而这些老师都在跟我讲一些很具象的东西。
还有我的邻居,原来是西安美术学院的教授,刘选让。大家是邻居,又都是西北人,还都在新疆军区当过兵,算是战友,一来二去的就熟了。我有时画画,觉得画烦了,画不下去了,就找他去,半夜也敲门:“刘老师!刘老师!”他来开门:“哎呀!闹啥呢吗,大半夜的。(陕西话)”我说,“不行不行,画不下去了!”刘老师说,“又咋咧,走,走,看一下,看一下(陕西话)。”
所以说我很幸运的,遇到了这么一帮人,绘画经验更是比我丰富的多,又不断地指导我,也无私地帮助我。想起来,心存感恩。
:艺术是相通的,除了您身边的书画家朋友,您做《艺术人生》这个栏目时,遇到的其他艺术家,比如表演、音乐、舞蹈等等,他们应该也会给您些营养,也能体现在您的画作中。
朱军:那肯定是。这些年,同这些嘉宾的交流,是我人生珍贵的一笔财富。当他们回忆过往,比如说战争年代,他们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那种坚定、刚毅;当他们回忆亲人间的情感,脸上荡漾的那种温暖,所有的一切,我觉得对我都是一种积淀,一种积累。这些情感和经历在我的心里不断的堆积,然后不断的裂变,直到有一天找到了绘画这个出口,它们一下子就释放了,释放在画作当中。
你看我画的那个藏族老人的半身头像。有些行家评价说,这幅画画得好。我说好在哪?他们说,你这幅画画的很放松。我说对,这是其一。还有一点,凡在西北生活过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眼睛上戴的那个眼镜,是石头镜。这在甘肃和陕西的人都有特别的体会,这个眼镜是水晶石的,绝不是玻璃的。如果让我评价这幅画,我也觉得自己画得好,是因为我用笔墨画出了水晶石的质感,而且从镜片后面,还能透出眼睛来,还能看到他的眼神。这个我觉得就是我生活的积累、感情的积累。
:我们看到,您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是五月份,您刚刚过完50岁的生日。
朱军:对。我是四月二十六日的生日,展览在5月份,是在美术馆的5号厅举行。这是我有意要求的,而且特别幸运如愿以偿:中国美术馆,5月份,5号厅,我50岁。等于我给我自己一份生日礼物。我在四十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时刻准备着》,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自己得给自己四十岁的时候留点什么。我就在39岁的时候,用了一年的时间写这本书。但50岁的办展,动这个心思,时间挺长了。一直不敢说,因为我不敢肯定我的作品,能不能过关。一个是过自己的关,一个是你得过美术馆的这帮专家的法眼。中国美术馆并不是说,朱军你是主持人,你在群众中有点影响,你就可以来办展。真不是这样。
:是的,中国美术馆要求高,审查很严格的。
朱军:对。中国美术馆有一套很严格的审核机制,审核是无记名投票,并不告诉参加审核的专家画家是谁,只是画往那一搁,请这十多个专家看,然后大家无记名投票,过了就过了,没通过谁也没招。我特别幸运,通过了。
所以,我一直不敢随便说要办画展。中国美术馆审核如此严肃,不是谁说要办展就能办的。而且说句实在的,我当时心里对自己就一个要求:我第一次办画展,一定要在中国美术馆,要不就不办,因为我不希望大家说我在玩票。我不希望大家说朱军在那就是附庸风雅,就是随便抹抹写写画画。我要么就不画,我既然画了,我就希望能得到业界一个基本的认可。所以我给自己定的要求就是,我的画作如果没有通过中国美术馆的审核,我就不办展。
:事实证明,您不仅通过审核办了展览,而且,您的画展可以说是很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
朱军:美术馆给了我十二天的时间做画展,我用了两天布展,展出了整整十天。这十天里,每天,在我的那个展厅里,人非常多。撤展时都没办法,人流不断。真的很感谢大家的认可。
我到西安办展真挺忐忑的,因为西安著名画家太多了,西安美术学院在那,黄土画派、长安画派两大画派在那。所以刚开始有人说到西安办展时,我有些犹豫。后来我是咬着牙来的西安,刘文西老师全程参加了我西安画展的活动,包括开幕式、研讨会、晚上还有一个答谢晚宴,王西京老师专门派了他的两个助手手下来帮忙,西安美院的老教授、西安美术馆的馆长,都帮了我很多忙,这让我非常感动。
:您这次画展的主题想表达什么?而且,在知天命之年,举办这次画展,您一定也是将许多人生感悟融入到画展的主题之中了。
朱军:这次画展,是我五十年来人生的一个思量,也是我人生感悟的另外一种表达。从心里来讲,绘画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时候办展,除了给自己五十岁送一个礼物之外,也是一种汇报。有人问我“杜蘅情怀”中的杜蘅是怎么回事,其实,杜蘅就是一种生长在水边的植物,不很起眼,散发着淡淡的芬芳,又是一种中药。我想告诉大家:虽然我平时站在风口浪尖上,其实生活中的我希望自己像小草一样,不那么张扬,然后还有用,还很丰富。从我内心来讲的,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您在西北生活了很多年,这次回来办画展,有何感想?
朱军:我在西北从出生到离开整整三十年,这对我来讲,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西北那片土地真的是给我太多太多东西。它的丰富它的多样它的千姿百态,实际上已经在我的画里呈现了。也正因如此,这次展览选择的是清一色的藏族题材,因为那种生活我更熟悉。从绘画上讲,藏族的服饰风情,比咱们汉族要丰富。甘南,那么大的藏民的聚居区,保留着藏族的传统习俗。像拉布仑寺,我在青海当兵的时候,每周都去那劳动。我有一张画,画的是藏族的老阿妈,拄着一根木棍,手里拿着转经筒,她身后是在雪中起伏的经幡。老阿妈的形象就是我当年当兵时,房东老太太的形象,永恒的留在我的记忆里,闭上眼,我就能想起她来。
:您今后打算向专业画家转型吗?
朱军:我觉得这要顺其自然。不管什么事,事前我都不会设立什么目标,包括我做主持人,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我在甘肃电视台,从来也没想过去中央电视台。后来我应节目导演的要求去北京,又留在北京,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
我画画也是这样,并不是非得当专业画家。我个人觉得绘画这个事,无所谓专业不专业,要看作品说话。你的作品专业了,你就专业了;你的作品不专业,你就是吃着国家的饭,说自己就是个画家,但画不出作品来,不是更丢人吗?
所以我就觉得画画是个顺其自然的事儿,没有必要非得要求自己将来成为什么样的画家,那会把自己累死,而且会束缚住、禁锢住自己,也就没法儿往前发展了。我现在随性而作,乐在其中,挺好的。你说我画得好,我高兴,你说我画的不好,我就是一业余画画的,也没关系。这种自然洒脱的状态,多好啊。
:以后如果有人提出收藏您的画,那您打算出手吗?
朱军:碰到真正喜欢我的画,能读懂我的画的藏家,我还是挺乐意分享的。因为从我办画展到其他,我都很喜欢和大家分享。如果有愿意收藏我的画的藏家,他会比我自己更珍惜这幅画。
:《艺术品鉴》杂志是一本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典藏类文化期刊,内容涉及典藏、艺术、人文,您对杂志有什么建议?
朱军:我觉得,这个杂志和《艺术人生》是一样的,如果要单纯追求收视率,就不要做。做真正和艺术相关的东西,是要耐得住寂寞的,说白了,你要寻找看得懂它的人群。真正的艺术是小众的,不是大众的;有时候真的就是小众艺术引领大众艺术。对于《艺术品鉴》杂志,我的建议就是坚守、坚持。范曾先生之前说过,创新重要,坚守同要重要。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这么辉煌的历史文化,是因为有一代一代的人在坚守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没有放弃。
:我们杂志的受众群体不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亦是艺术品收藏领域的主流群体,对这一部分收藏群体,您有什么建议?
朱军:中国收藏其实挺有意思的。首先,收藏群体越来越大,是个好事。收藏过程本身会丰富自己。藏家收到一张好画,他就会去研究画的年代,画家的地位,当年的风格,当年文人的情怀。这种研究对藏家本身就是提升。另一种现象就是中国所有的事物好像都是商品,我不否认艺术品也是商品。但如果抛开艺术,艺术品商品就没有意义了。就像绘画作品,抛开艺术价值,那何必花几千万买一张纸呢?几千万都可以买栋楼了。藏家买这幅画,首先还是要懂这幅画的意义,而不是只懂它的价格。我觉得藏家首先要弄懂藏品的价值和意义,内在的东西,再谈收藏。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与我们分享您与丹青独处的情感与快乐,谢谢。
——中国美术馆藏文学插图精品展
——中国美术馆、南京博物院藏明清肖像画展
——中国美术馆藏书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术作品广西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