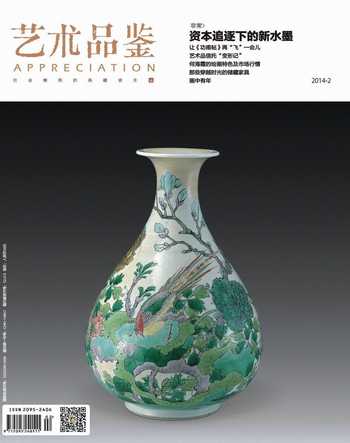李盛铎“旧藏”敦煌古卷的前世今生
黄薇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敦煌文书等。指敦煌所出5至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包括官私文书。清光绪二十六年,道士王圆箓于莫高窟第16窟发现了“藏经洞”。1902年,甘肃学政、金石学家叶昌炽成为最早发现这批文书价值的中国学者。其后,国外探险家们接踵而至。将大批文书珍品捆载而去,流失海外。劫余的文书,于1909年由清政府学部解省送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敦煌遗书已分散于世界各地,目前最大的四个庋藏处是: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中国,各地有多处敦煌文书藏家,日本、欧洲等地亦有零星收藏。敦煌遗书在内容上可分为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等类。
图1为一张近年来公之于世的敦煌残卷,编号为“羽019R-1”,为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秘籍》之一,内容是《庄子·让王篇》第五节“颜阖”的一部分。该写本每行17字,前端文字残断严重。图2编号为p4988,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8年从敦煌攫取的《庄子·让王篇》,起自第三节“亶父”,至第五节“颜阖”的“国家,其土苴”,共28行,每行17字,前3行下残,后3行上残。全文字迹基本清晰,卷中有“世”字缺笔。两相对照,两古卷从纸型的断痕到字体、内容文字完全可以拼接﹔而两卷背面均写有《大目干连冥界救母变文》,可见这两份抄卷属同一份文书断裂所致。日本“羽019R-1”残卷上盖着“敦煌石室秘籍”的收藏印。
日本杏雨书屋所藏的敦煌写本共有700余件,是最晚公之于众的整批敦煌文献,被学界认为是“敦煌学最后的宝藏”。其中最重要的432件均源自李盛铎,“敦煌石室秘籍”就是他的收藏印。
李盛铎对前述432件敦煌古卷的“入手”开始于1909年。那一年,李盛铎在清廷学部任职。
敦煌遗书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浩大丰富的敦煌遗书的世纪性发现,为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广大学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珍贵资料。
9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北京,把他从敦煌“获得”的部分写本及文物展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均前往参观、抄录。为了避免敦煌古卷再遭遗失,学部命新疆巡抚何秋辇负责把残存的古卷运到北京。1910年这批文物运抵北京后,何秋辇之子何震彝约同精通版本目录学的岳父李盛铎等利用职务之便,将古卷中的精品“取走”,然后又把剩余卷子中较长的撕裂成为数段凑数。根据李盛铎自己编录的《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记载,他“收藏”的敦煌写本共有432件之多。此事虽被人揭发,但由于辛亥革命爆发,终于不了了之。
进入民国后,消息不胫而走,如王国维在1919年9月10日致罗振玉信中就提到:“李氏诸书,诚为千载秘籍,闻之神往。”后来叶恭绰于1921年11月组织了“敦煌经籍辑存会”,邀请李盛铎参加。到了1923年,抗父发表《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在综述“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写书”时,对李氏所藏敦煌文献更有明确的报道。
1928年10月7日,一位名叫羽田亨的日本学者到天津英租界黄家花园家中拜访了李盛铎。这位羽田亨,精通十几国语言和满、蒙古、藏等多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是元蒙史、古代中西交通史、西域史和敦煌学的世界级学术权威。据说访问的当天,李盛铎慷慨地展示了所藏的《志玄安乐经》等一批敦煌古卷,还同意羽田亨抄写其所需要的经卷,并允许他研究后发表。
1937年李盛铎去世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与李氏后人磋商,希望收购其藏书,但在价格上双方相差甚多。虽然李盛铎藏书最终归于北大图书馆并保存至今,但其中并不包括敦煌古卷。据1935年12月15日及21日《中央时事周报》刊登的《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所载,李盛铎的敦煌古卷432件,已经“以八万元日金售诸异国”某氏。从此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另据日本学者后来考证,1936年,日本某“资金提供者”把李盛铎的这批敦煌古卷交给了羽田亨。1938年羽田任京都大学总长后,将这些古卷保管在总长室,并进行了整理研究。1945年夏天,日本败战在即,为免遭战火焚毁,“资金提供者”要求羽田将这些敦煌藏品于7月13和15日两次送到大阪武田制药的工厂中保存。到8月1日,藏品又被转移到兵库县多纪郡大山村西尾新平氏宅的仓库中。当时除了购自李盛铎的古卷432件外,还有其他存于日本的写本300多件,羽田亨分别编纂了《目录》,并拍摄了照片。羽田亨去世后,照片被陈列在羽田纪念馆,而李盛铎旧藏的敦煌古卷和其他日本藏品一起被保存在日本杏雨书屋。
随着各国学者对于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横向合作的不断开展,英国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都公布了各自所藏文献的图版。如今,在沉寂了多年之后,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五大敦煌文书收藏者的杏雨书屋,终于决定以《敦煌秘籍》之名将所藏敦煌古卷的内容整理出版,预计全部内容包括目录1册、图版9册。目前,随着目录册、影片册1、影片册2、影片册3的相继面世,原本属于个人的这批敦煌古卷终于和其他各国收藏的古卷一起,成为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