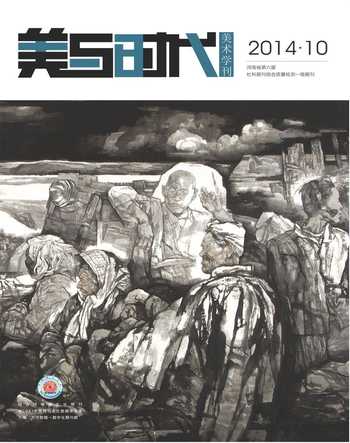乡土记忆中的市声
摘 要:对应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一时的都市繁华,同时期的油画创作可以被视为这“摩登时代”的绘画表现。以庞熏琹等画家的创作为代表,早期海上油画记录的都市生态,其中蕴含的现代主义艺术特征与文化意义影响深远,启迪后人。
关键词:乡土社会 新之崇拜 摩登时代 徐悲鸿 庞熏琹
导 言
我们也许可以远在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作品中,看到勾栏瓦肆与城市景观的绘画表现。不过描述城市景观与经验的作品在中国绘画史上历来是稀缺的,因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1]。现代都市的真正崛起在中国是20世纪初的事情。作为最具世界性的对外通商口岸,上海是民初中国乡土社会瓦解,工业化、城市化的滥觞之地。同时,做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与商业中心,上海又是画家聚集,美术团体与美术教育蓬勃发展的城市,油画家们对这新旧交替的都市充满着描述的热情。早期海上油画的研究文本,一直以来关注民初时期上海的殖民地身份,对油画作品的评述大多置于“中西结合”或者“救亡图存”的语境中进行。——相对于艺术创作活动的复杂性、丰富性,所有的阐述都有“过度诠释”或简单粗疏的危险,但是不同视角的解读同时增加了我们面对作品的丰富感知。本文试图将早期海上油画的部分作品纳入都市文化研究的视野,对其做一些时代背景与艺术思想的梳理。
一、乡土社会的都市经验
对中国人而言,油画是舶来品,对它的理解自然应该建构在与本土绘画的对照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 山林野趣与田园情调一直是绘画表现的主流。假如说“成教化,助人伦”的儒家精神是绘画追求的一面,那么“做濠濮间想”的道家哲学在创作中更起根本的作用。“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2]。宋元以来,随着禅宗在文人中的广泛的深刻影响,隐逸精神的追求更成为绘画的主流。山水、花鸟画的兴盛远远地超越了人物画,面对自然的澄怀观道成为文人重要的生活逸趣,绘画往往用来栖息对无限的想象,感受一种宗教情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各地域乡土的文化与艺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铺张,巴洛克或包豪斯式样的楼房矗立起来,面向高山大川、名士淑女,草虫鸟鱼建立的笔墨对此显然是尴尬的。传统乡土社会建立的审美价值观遭到质疑,欧洲绘画中的写实传统与现代绘画的丰富形式,成为改造传统绘画的主要参照。在西方文明的强势渗透之下,无论是潘天寿的“中西拉开距离”,还是黄宾虹的集传统之大成,都后继乏人,而徐悲鸿和林风眠的“融会中西”成为时代主流。由城市化工业化已经普遍的今天回望,对传统绘画及其精神的坚持,实质上越来越成为民族的怀旧心态,旧时的艺术已成为我们遥远的乡土记忆。
近代中国的美术革新热潮正是中国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展开。油画自17世纪传入中国,20世纪初才真正在中国成为影响深广的艺术,其中既携带了欧洲科学精神的基因,又披挂着令国人向往的现代文明的“进步”外衣,它代表了全新的价值观和审美经验。尽管在随之而来的“中西融合”的努力中,许多画家更倾向于将传统水墨画的语言与油画融合,使得这一新鲜画种有了种“中式古典”的面貌,成为泱泱帝国同化异族文化新的佐证。但同时,对西方油画在彼时一种“进步”、“前卫”姿态的迷恋,成为另一部分画家作品的精神诉求,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与当下都市的生活经验结合,创造了富于现代感的作品。对应于都市生活经验的油画作品,主要体现了现代主义的追求,同时又不尽如此,其思想与审美的复杂,反映出时代与地域的特殊。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是中国最富于现代都市气质的城市。在十里洋场与各国租界,都市的景观呈现出非常西化与现代化的趋向。尽管充斥了殖民主义的色彩,五光十色的城市在一段时间里还是富于魅惑力的,在这一氛围里培育出新的文艺气象,一直到中日战争爆发,救亡图存的呼声才唤醒一时的繁华幻梦。在张爱玲和苏青的小说,甚至茅盾的《子夜》中,我们可以阅读到这种都市生活的鲜活描绘。这时期的上海,也是油画创作与传播的中心,上海艺专、决澜社等绘画团体的艺术活动风起云涌,使得对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表现,首先在这时期的油画创作中得以体现。
二、“新之崇拜”与都市绘画
茅盾写于1930年的名作《子夜》开篇,描绘了上海的现代图景:“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瞑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然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NEON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3]。
小说的描绘令人联想到倪贻德20世纪10年代画的上海街景,以表现主义画风简洁地表现了城市的工业气氛。高楼、电车、商场、不同肤色的行人,完全是一幅世界性的图景,我们几乎难以区分这是上海,还是香港和巴黎。
被本雅明名之为“19世纪的首都”的巴黎,至20世纪之交,仍是思想和文艺的发轫地,现代都市的样板,上海与东京在当时即是巴黎在远东的翻版。当时留法或者留日的中国画家,多选择上海为归国后的生活与艺术创作之地,这繁华都市里洋溢的一种世界主义气息,是熟悉且被认同的。庞熏琹20年代留学法国,1930年归国,1931年创作了组画《上海印象》与《巴黎印象》,除却画面上人物造型一为西方人一为中国人,气氛与手法的运用别无二致,画家显然把上海看成他在巴黎的都市幻梦的延续。都市的印象在画面中以盛妆的人脸和迷幻的重叠予以表现,可以看到对立体主义画风和拼贴手法的借鉴。
1932年,庞熏琹联合傅雷、倪贻德等人组建决澜社,倪贻德与庞熏琹均是决澜社的主要成员。决澜社诞生于当时中国最为繁华的都市上海并非偶然,它表明了现代主义美术运动与大都市生活经验之间的密切关系。
现代城市发展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工业文明之上的“现代主义”或启蒙理性。启蒙理性批判神学偶像,反对君权,弘扬人本精神和科学精神,将自然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抬升为普遍法则,进而成为批判话语,成为精神解放的工具。它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是一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精神,是“今是而昨非”的历史批判之学。都市文明发展的思维方式鼓舞着艺术家对“艺术进化论”的崇拜。最终在20世纪初叶,现代艺术的各种流派纷呈而至,以惊世骇俗的姿态不断地变幻观点与作品,这些艺术迅速地滋生与消亡,一个接着一个,无限开拓视觉与精神的各个层面。做为当时中国最富于普世特点的画种,油画在文化中扮演着先锋角色,往往在对城市的描述中抒发了类似的“新之崇拜”。
决澜社的艺术实践最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新之崇拜”的激情。决澜社的宣言正表达了鲜明的现代主义之诉求,它几乎是我们现在所知的,那个时代中国最世界性和乌托邦的呼声了:“我们承认绘画决不是自然的模仿,也不是死板的形骸的重复,我们要用全生命来赤裸裸地表现我们泼辣的精神……我们厌恶一切平凡的低级的技巧,我们要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以来,欧洲的艺坛突现新兴的气象,野兽派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Dadaism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现出一种新兴的气象了。让我们起来吧!用了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4]
这既是欧洲现代绘画运动激情在中国遥远的呼应,同时也是上海都市现代气息所鼓舞的结果。
三、摩登时代的记录
民国时期是西学东渐,东方世界向西方取经,甚至一切向西看的时代。东汉时印度佛教传入东土,其思想被吸收融进了中国人的哲学和生活方式之中,近代西方文明借助船坚利炮到达保守的古老帝国,一切习以为常的生活和信念都被动摇了,它的深刻程度一点不亚于前者。无论是“德”先生、“赛”先生之新观念,还是形而下的衣食住行的新风尚,都根本改变了昔日帝国,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千年的乡土中国被颠覆了,按照西方人的理念,上海这样的“摩登”都市生长起来。就像当时文学家们半文半白的“五四文体”,在十里洋场的新上海新民国,人情世态的真实面目也是新旧兼备,异常微妙有趣的。比较起革命的绝决态度,世界和人心的变化要复杂、含混得多。画家们以他们的生花妙笔向我们展现了其生活的民国社会。
新的都市景观在风景画中可得到最直观表现。就可见的作品来看,油画对当时城市面貌和工业氛围的描绘并不普遍,许多留洋归国的画家将目光投射向乡郊与园林,如颜文樑,留法时描绘艾菲尔铁塔与巴黎圣母院,回国后,倾心于 “中国式风景”的创作,关注起广大的乡土世界。刘海粟甚至于画起了油画山水,毕竟身处一个有千年山水画传统的国家,画家的山水情结是根深蒂固的,而对乡村世界的关注向来是风景画的主要旨趣。
对上海租界和西洋建筑的描绘成了更多决澜社画家风景画中的内容。如倪贻德以表现主义画风表现了南京路等城市的街巷,使人联想郁特里罗曾画过的巴黎的街景。类似的作品还有陈抱一的《苏州河》和《外白渡桥》,手法略为平实,倾向于普通的外光写生。而庞熏琹画于1948年的《窗外》与《蒲园》,则描绘出作为生活居所洋楼的优雅和诗意。这些作品在上海常见的欧洲建筑和现代景观描绘中,体现了画家在欧洲接受的审美熏陶,没有勉强的“中西融合”嫁接的努力,却另有番自然真切的面貌。
都市是现代的产物,对都市景观与生活的体现,自然以现代主义风格的绘画为主。民初油画“写实”与“理想”两派,“理想”一派如决澜社,着意于表现“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写实”一路,则倾力于现实形相的描述。“写实”画派的代表徐悲鸿,在三十年代有《田横五百士》这样富于忧国之思的巨制,也善画笔调婉约的都市女性肖像。1936年创作的《孙多慈像》,以一种新古典主义的谨严手法表现了东方女性的内在含蓄之美,人物的背景摆布着希腊雕塑的石膏复制品,既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居室的西式风格,又暗示了画家的留洋经历。孙多慈穿旗袍,烫发,着高跟鞋,十足时髦的都市名媛打扮。对女性美的描绘让人联想同时期的月份牌年画。事实上,在徐氏出国学油画之前,曾经画过类似月份牌的美人画。“1915年徐悲鸿再次来到上海,结识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这一时期他受到流行的商业美人画的影响,画出了有着月份牌画风格的作品。审美书馆曾出版徐悲鸿有着月份牌画风的美人画明信片”[5]。
与月份牌在商业上获得的成功类似,徐氏的“美人图”也有不错的市场感召力,绘于1939年的《珍妮小姐像》,人物姿势及道具酷似《孙多慈像》,获重金酬谢,用于抗战募捐。直至2005,《珍妮小姐像》在保利秋拍出2200万元高价,是当年油画的市场神话。而描绘 “旧上海”之风情在徐氏1937年作品《月夜》一画中更表达得淋漓尽致。画中有徐氏画中常见的女子吹箫的形象,表现月光下人物影影绰绰的光色韵味,较之他对形象轮廓一贯的准确严谨追求,显得放松,逸笔草草,甚至有点表现主义的趣味。徐悲鸿通过对女性肖像的描绘把其所捕捉到的上海摩登气息表现了出来,而这种表现我们只能多年后在陈逸飞与王家卫的电影中重温,这些作品和胡蝶的歌声,阮玲玉的电影一起,构成我们对那个年代摩登上海与新式女性的想象。
然而就图像的记录意义来看,写实油画对这摩登时代的反映,远没有晚清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对世风的揭露来得彻底,当时的主将,关心最多的自然是国家兴亡,徐悲鸿的激情更多地在于通过绘制宏大的历史画来教化民众,就其内心情感来说,对这殖民之下的花花世界的繁华,无疑是抵制的。
四、焦虑的声音
都市的生活方式和物质都让人沉迷,绘画对此充满正面的礼赞。同时,对城市批判的声音也从未停歇过。对都市的批判,在西方历来和都市化的进程同步。海明威赞美的 “一场流动的盛宴”之巴黎,同时是波德莱尔笔下衍生“恶之花”的罪恶深渊。城市和工业同时带来人的异化,产生马尔库塞所谓的“单维人”。在中国,这种焦虑更和殖民状态之下对家国的忧虑与尊严纠葛在一起,汇聚成左翼画家们振耳发聩的呼声。
庞熏琹于这时期创作的《无题》,具有象征和隐喻的表现特点,画面挪用了立体主义的几何造型方式,以一种“超现实”的空间移植方法,将多种形象内容组合在一张画面中,各种形象的并置表达出作品的现实批判内涵。庞薰琹自述这幅画作的意义时说:“画面主要画的是压榨机的剖面,前面一个是机器人,一个是我国农村妇女像,一个是象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达,一面是象征落后的中国农业,三个巨大的手指在推动压榨机,象征着帝国主义,反对的政治与封建势力,这是对我国人民进行压榨的三种势力,也就是迫得我走投无路的三种势力。”[6]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浮华异常,在随后的战争来临后终成一场幻梦。日本军队的枪炮轰炸,使沉醉于“海上都市梦”的人们不得不惊醒。这时期的上海文艺经历了一段繁盛时期,这种繁盛景象最终却被浓密的战争阴云遮盖起来,战争、灾害、死亡与逃难的阴影从未在生活于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心头中散去。决澜社四次展览后即退出历史舞台,也正是因为庞熏琹等人逐渐认识到,上海毕竟不能代表大部分的中国,随着战争的到来,这种“新之崇拜”的激情逐渐被忧国忧民的沉重思绪所替代。庞熏琹紧接着有画风苦涩的《地之子》、《大地的女儿》诞生,无关都市繁华、风花雪月,关注起广大的劳苦大众。对战争的控诉成为1937年上海失守后油画展览的主题,如张充仁的《恻隐之心》(1937年)等作品,司徒乔的灾情画展(1946年),社会影响都很大。
自清末《点石斋画报》开始,中国艺术已经开始机械复制的时代,摄影和电影成为大众文化的宠儿,油画在那时候出场,已是阳春白雪的角色。对城市与战争的批判,木刻版画远比当时的油画来得尖锐。在此后颠沛流离的战争流亡生活中,“上海摩登”逐渐成为一个远去的幻景,绘画叙述的激情转移到了对战争和乡村的关注。
结 语
“上海作为都会在30年代早期算是登峰造极了,并一直持续到1937——1941的‘孤岛时期;一直要到1945年抗战结束,因通货膨胀和内战使得上海的经济瘫痪后,上海的都市辉煌才终于如花凋零。”[7]美术界的情形也是如此,1937年上海失守,除去小块租界,城区为日军占领。“由于‘孤岛格局的形成,上海地区的油画家迫于战乱的危机,纷纷内迁和北上,无形之间,西画中心宣告解体,“上海时代”宣告结束,而相应衍化于‘孤岛文化的情势之中。[8]
海上繁华,连同体现这种繁华状况的都市现代主义绘画,终成明日黄花。而在远隔六七十年之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油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初油画之现代精神遥远的回响。20世纪初海上油画笔下的都市景观与现代主义精神,记录和表现了一个时代,其艺术视角与绘画形式,更对当下生活于城市中油画家的创作富有启发意义。
注释: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页
[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8页
[3] 茅盾.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1页
[4] 李超.中国现代油画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178页
[5] 陈瑞林.城市大众美术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7(03):51页—58页
[6] 庞熏琹.就是这样过来的[M].北京:三联书店,2005:142页
[7]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6页
[8] 李超.中国现代油画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208页
作者简介:
丁海涵,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徐悲鸿经典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