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护照的贫富差距
蒂姆·哈福德
我算是个幸运儿,从小享受着各种“优势”。许多优势如今说来有些敏感,但却值得拥有。比如,我是个白人,我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而且是个“牛剑”后代。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些优势与个人成就的关系不大,因为另外一项更为重要:公民身份。这一点优势的价值大于其他所有优势之和。
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所有人按贫富顺序排队。每人身边放一叠钞票,来标明个人年收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世界的财富分配有多么的不公平:世界上占总人口1%的最富裕阶层(人数约7000万左右)与最穷1%人口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鸿沟。你的税后收入需要达到3.5万美元,才能成全球最富有的7000万人口中的一员。一个四口之家的税后收入则需要达到14万美元。或许有些人觉得这个标准有点低,但这已经是世界上最贫穷人口收入的100倍了。
而事实上,富裕人群通常都居住在富裕国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是纽约市立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是《穷人与富人》一书的作者。据他估算,世界上约80%的财富差距是由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造成的;仅有约20%的财富差距源自国家内部。牛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确实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出生在英国,而不是孟加拉国或者乌干达。
公民身份在决定财富收入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但在讨论全球贫富差距的时候却经常将其忽略掉。其实很早以前,全球贫富差异并没有这么悬殊。1820年,英国人均收入是中国和印度的3倍,是当时最贫穷国家的4倍。不过,在那之后,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就不断扩大。现在,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5倍,是印度的10倍,是那些最贫穷国家的50倍(如果考虑中国和印度的物价水平的话,这差距会更悬殊)。与19世纪相比,美国、欧洲或日本公民在经济方面会享有更大的优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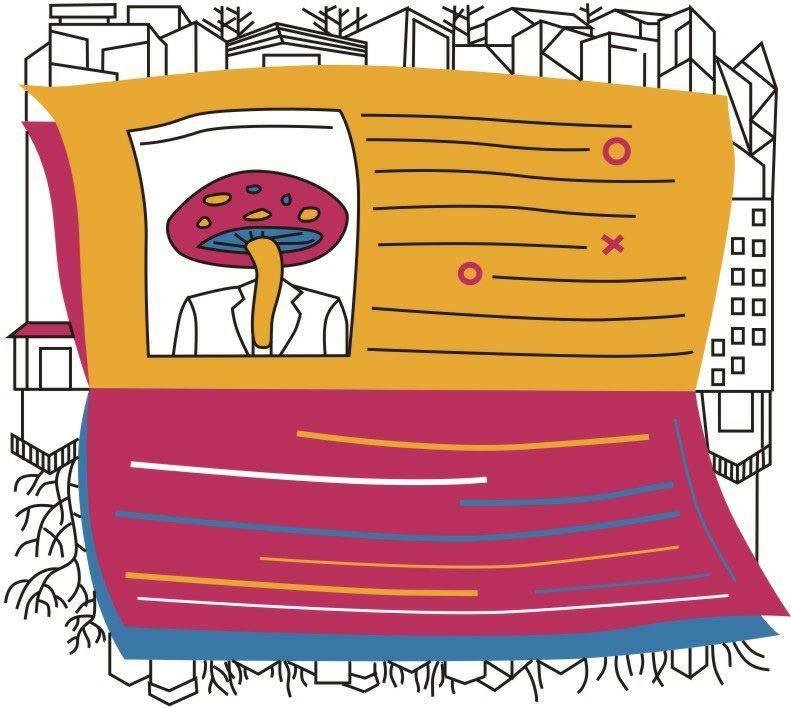
在两个世纪以前,阶级比国籍更能带来“优势”。来看看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描绘的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贝内特的未来收入水平完全取决于她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取决于她嫁给谁。伊丽莎白的家庭人均收入是430英镑,如果她嫁给达西先生,达西1万镑年收入中的一半将归其所有,这样一来,伊丽莎白的个人收入将增加十倍以上(按照上述收入水平,达西先生属于富裕1%阶层)。如果在伊丽莎白出嫁前她的父亲去世了,她的年收入也有40英镑,是当时英国人均年收入的两倍。与19世纪相比,如今各阶级间的贫富差距已大幅缩减。根据2004年的数据换算,作为富裕1%的达西先生的年收入可以达到40万英镑,伊丽莎白的个人小金库也将有2.3万英镑入账。在19世纪,婚姻让伊丽莎白的收入增长超过100倍,而在21世纪,婚姻只让她的收入增加了17倍。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与19世纪相比,阶级对贫富的影响大大减弱,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则被加强。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似乎是向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他和托尼·阿特金森等人创建了“全球顶级收入数据库(Top Incomes Database)”,对高收入者进行分析。进入这个数据库首先要选择你想要分析的国家,因为它是就单一国家进行分析的。西蒙·库珀和托马斯·皮凯蒂的逻辑也不无道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确实值得关注。我们关注它是因为政府应当有能力解决它,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国内贫富差距再度拉大,而全球贫富差距正在日渐缩小。
但是,当我审视自身“优势”的时候,我还是不能忘了最重要的那个:英国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