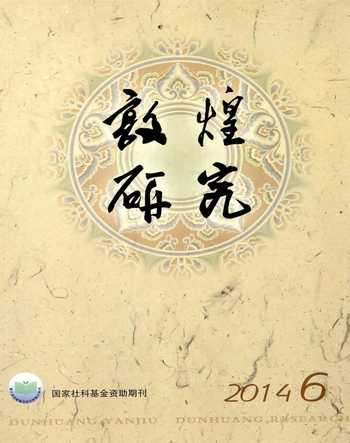敦煌本《佛法东流传》及其作者考
刘林魁
内容摘要:缀合敦煌文献中的6个卷子,可以完整展现《佛法东流传》的原貌。从内容来看,《佛法东流传》与智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基本吻合;但从文章内部透露的相关信息推断,两书不可能出自智昇之手,而很可能源自释法琳《释老宗源》。《释老宗源》因收录了《汉法本内传》被“禁断”传播。智昇以续补《集古今佛道论衡》的名义,将《释老宗源》中的佛教部分辑录出,以《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之名顺利入藏。至于敦煌本《佛法东流传》,早在《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成书之前就以单本形式流传于世了。
关键词: 《佛法东流传》;《续集古今佛道论衡》;《释老宗源》;法琳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6-0097-05
一 敦煌卷子所见《佛法东流传》
《敦煌宝藏》与《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有6个“佛法东流传”卷子。从这批卷子来看,《佛法东流传》的内容大致由三部分构成:
佛陀生平文献:此部分仅录《周书异记》,记述周昭王二十四年、周穆王三十二年、周穆王五十二年天象变化与佛陀生灭之时间对应。
佛教入华文献:此部分包括《世传记》、《汉法本内传》引文。《世传记》记述佛教正法、像法、末法的时间。《汉法本内传》记述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入华以及佛道争斗事,包括明帝感梦求法品、问佛生灭品、与道士比较度脱品、明帝大臣称扬品、广通流布品等五品内容。
佛教东传弘法文献:包括《玄通记》、《魏书》、《吴书》、《后凉书》引文以及未注明出处的北魏正光元年(520)道士姜斌与僧人昙谟最论议事。
这6个卷子没有一个是完整抄录《佛法东流传》的。P.3446v、P.3376抄录佛陀生平文献的全部和佛教入华文献的部分。P.3446v共43行,首全尾残,卷首题名“仏法东流传”,题名下有两行小字,字迹漶漫,可辨者大致为“明仏法”、“造寺□僧正法流通然□仏焉”,卷尾至《世传记》。P.3376共83行,亦首全尾残,卷首题名“法王本记东流传录”,题名下有两行小字“明仏法兴□,外道定其优,与从兹建寺度僧,□法流通,然识仏法□”,卷尾《汉法本内传》第三品未抄完。
P.2654v+P.2763v抄录佛教入华文献的大部分。P.2654v共50行,首尾俱残,卷首约从《汉法本内传》第三品第40字起,卷尾第三品仍未完。P.2763v共106行,首尾俱残,抄录《汉法本内传》第三品部分与第四品全部。P.2654v尾行为“无宗,荡寂空无,自然淡薄。二者报身,独立无侣,朗然无”,P.2763v首行为“匹,光耀世界,自然隐现。三者应身,备诸形色,言行无端,任物千”,两卷衔接处正好是《汉法本内传》第三品语句。P.2763v与P.2654v字迹相似,内容又前后衔接,此两卷当为同一卷子。
P.2352v与P.2626(P.2862v)抄录佛教入华文献与佛教东传弘法文献。P.2352v共353行,首尾俱残,卷首为《汉法本内传》目录,大致识读为“□□□□□王本□”、“□师□灭品 第三与道□□”,卷末抄至道士姜斌与僧人昙谟最论议事。P.2626与P.2862v两卷缀接,两卷可合为一卷,P.2862v成为空号。P.2626共229行,首尾俱残。卷首约从《汉法本内传》第一品之第90字始,卷尾至《魏书》引文。
从敦煌卷子抄录情况来看,《汉法本内传》占据了《佛法东流传》近2/3的篇幅,是《佛法东流传》的核心内容。但是,敦煌文献中4个题名“汉法本内传”的卷子,并非抄自《佛法东流传》。
S.5916共3行,首尾俱全,卷首题名“汉法内传”,题名下有小字“远依《历代法宝记》□格取此条”。《历代法宝记》一卷,成都保唐寺释无住(714—774)弟子编撰,敦煌遗书中有完整写本。与之对照可知,S.5916出自《历代法宝记》,非出自《佛法东流传》。
P.3475、P.4032和P.3740这3个卷子,《敦煌宝藏》与《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均拟名“汉法本内传”。其中,P.3475共62行,首尾俱残,内容记述吴主孙权与尚书令都乡侯阚泽论三教、魏明帝时舍利灵验、北魏太祖崇敬佛法、北魏太武帝灭佛、北魏孝明帝时道士姜斌与僧人昙谟最论议等5事。
P.4032由两部分残片构成,可分为P.4032A、P.4032B,A、B两部分均首尾俱残。P.4032A残卷共10行,内容为姜斌与昙谟最辩论事,文字与P.3475衔接,P.3475末行为“记仏之言,出在中备。仁者善自披究,足得开晓。姜斌曰”,P.4032A首行为“孔子圣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法师对曰:唯仏是众圣”,衔接处正好陈述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姜斌与昙谟最论议事。故而,P.3475与P.4032A可能为同一卷子。
P.4032B共72行,1—26行下半行残缺,60—72行上半行残缺,始于《仙人请问众圣难经》引文,此后所引文献依次为《仙公起居注》、《仙公请问上经》、《上品大戒经校量功德品》、《升玄内教经》、《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仙公请问上经》、《法轮妙经》、《周书异记》、《书》、《符子》、《牟子》、《内典天地经》、《清净法行经》等,此下又有霍去病讨匈奴得金人事、张骞出使大夏知佛法事、楚王刘英崇佛事、襄楷叙佛教事、《后汉书》载明帝求法事,卷尾为《后汉书·郊祀志》叙佛教的内容。P.3740共99行,首尾残损明显,1—3行下半行残缺,第87行文字存右半面,88—99行上半行残缺,卷首为《后汉书·郊祀志》叙佛教文字,与P.4032B卷尾衔接。P.4032B末两行残存之下半行文字为“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皆□□□□□□□□”,P.3740首行残存之上半行为“修道,以练其精神,练而不己,以至”。两卷衔接处,《破邪论》为“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后受形。所行善恶,后生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练其精神。练而不已,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2],基本相合。故而,P.4032B与P.3740可能为同一卷子。
对照现存法琳《破邪论》可以断定,P.3475、P.4032、P.3740的内容抄自《破邪论》卷一,并非抄自《佛法东流传》。因此,4个《汉法本内传》卷子与《佛法东流传》毫无关联。梅弘理将4个《汉法本内传》卷子并入古写本《佛法东流传》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二 《佛法东流传》作者考
《佛法东流传》的内容,基本与智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吻合。所谓基本吻合,是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直接从《汉法本内传》开始,没有《佛法东流传》中的《周书异记》、《世传记》。但现存《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中,“当此之时,佛生王宫。壬申之年,十九出家……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3]一部分文字叙述混乱。对照《佛法东流传》可知,这段文字当由正文和注释两部分构成。正文是《汉法本内传》第二品的内容,注释有汉统法师、齐国大统法师等引言和《周书异记》、《帝王世记》、《世传记》等引文。《佛法东流传》之《周书异记》、《世传记》,正出现在《续集古今佛道论衡》这部分注释中。这样来看,《佛法东流传》与《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很可能有同一个文本渊源。
梅弘理将这个渊源定为《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他考证了诸卷子的抄写时代,P.2626(P.2862v)约750年,P.2352v约757—764年,P.3446v、P.2654v、P.2763v约769—781年,并由此推断出,敦煌写本比宋刻本要早约4个世纪,是《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最早的文本[4],亦即《佛法东流传》的作者就是唐玄宗朝僧人智昇。不过,这批卷子的抄写时间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如姜伯勤认为P.3376、P.2626(P.2862v)的写年为武德七年(624)[5]。两种说法孰是孰非,目前尚无定论。如果依据姜伯勤之说,则《佛法东流传》早于《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其作者自然不会是释智昇了。
《佛法东流传》与《续集古今佛道论衡》都以辑录、转引文献为主,但其间也有辑录者的叙事。这些叙事不但将割裂的文献连缀起来,而且透露了辑录者的部分信息。比如:有一段叙述佛陀涅槃后佛教东传中土的文字,两书于此有所差异。敦煌卷子P.3446v:
案《世传记》云:“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经云:“息用名灭,非死灭也。”一大(“大”为“本”之讹)无像法,有正、末二法。记从仏入涅槃计至汉明帝永平十年(67),凡一千廿年。从汉明帝永平十年至唐武德七年(624)甲申岁,五百五十八年,合得一千五百七十八年。计吴赤乌四年(241)康僧会将仏法至江东,至武德七年甲申岁得四百十二年。
《续集古今佛道论衡》:
案《世传记》云:“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经云:“息用名灭,非死灭也。”一本无像法,有正、末二法。记从佛入涅槃计汉明帝永平十年,凡一千二十年。从汉明帝永平十年计至大业十年(614)甲戌岁,凡五百四十八年,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从大业十年至贞观十年(636)岁次丙申,二十二年,通前一千五百九十年。[3] 398
《佛法东流传》选了三个参照时间,汉明帝永平十年、吴赤乌四年、唐武德七年,用来叙述南方佛教、北方佛教各自的发展历史;《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也选了三个参照时间,汉明帝永平十年、隋大业十年、唐贞观十年,叙述中土佛教发展史。两书上引文献的差异足以说明,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历史的叙述视野具有开放性,其参照时间之最近者可以随编纂者、传抄者生活时代而变化。故而,两书参照之最近时间,应该与其成书时间密切相关。又,《佛法东流传》中叙述佛教入华时参照的吴赤乌四年与其中所录康僧会江东弘法时间正好吻合,故而《佛法东流传》的叙述似乎更符合原貌,其成书时间似比《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早一些。
《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约成书于开元十八年(730),其书编纂历来存在诸多困惑。如,《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绝大部分内容与唐高宗朝“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重合”,有学者因此怀疑 “以智昇撰《开元释教录》这样博深的佛学名著的根底”“至于写出这样差的著作来”[6]?智昇《开元释教录》记载两卷《汉法本内传》被“明勅禁断,不许流行”[7],但他的《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中又何以详细著录此书?释智昇为什么要在自己编纂的著作中选择一个百年前的时间参照来叙述佛教历史?等等。现依据《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中叙述中土佛教历史的参照时间,可以断定,他应该成书于太宗贞观年间,其作者自然不会是智昇。
搜检唐高祖、太宗时期佛教典籍,可以发现,《佛法东流传》、《续集古今佛道论衡》辑录之文献,都出现在《破邪论》卷一。这种文献的相似,以至于陈士强断言,《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从唐法琳《破邪论》上卷抄来的”。虽然如此,但《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与《破邪论》只有极少数叙事文字高度重合。那么,《佛法东流传》与《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会不会源自释法琳的另一部著作?
释法琳(570—640)是活跃于唐高祖、太宗朝的著名僧人,道宣《续高僧传》置其于“护法”类中。其著述30卷,包括“诗、赋、碑志、赞、颂、箴、诫、记、传、启、论,及《三教系谱》、《释老宗源》等”[8]。其中,《三教系谱》从名称来看,体例可能更接近谱牒一类,与《佛法东流传》之文献辑录体例不吻合。至于《释老宗源》,从题名上来看当是关于佛教与道教渊源历史的记述。考虑释法琳的宗教态度及唐初二帝时期佛道争衡异常激烈的宗教环境,《释老宗源》自然要扬佛抑道,甚至要攻击道教。《佛法东流传》的内容,就是记述从佛陀在印度降诞、成道、涅槃到佛教入华,以及南方佛教和北方佛教的发展历程。此中记述不就是立足于唐代探究佛教的宗源吗?这样来看,《佛法东流传》很可能源自法琳《释老宗源》。
这一推测,与《佛法东流传》的实情大致吻合。《佛法东流传》的成书有三个特点。第一,编纂者佛教信仰坚定,对道教有强烈的排斥态度。《汉法本内传》中既有道士自憾而死,又有道士皈依佛教;姜斌与昙谟最论议失利后,在佛教的叙事中差点被北魏明帝所杀。第二,编纂者意欲向帝王和上层社会宣扬弘法理念。《周书异记》中的周昭王、周穆王和太史苏由、扈多,《汉法本内传》中的汉明帝和太傅张衍,康僧会江东传法事中的孙权与都乡侯阚泽,姜斌与昙谟最论议事中的北魏明帝和侍中刘腾、中书侍郎魏收、尚书祖莹、太尉公萧琮、太府李寔、卫尉卿许百桃、吏部尚书邢峦、散骑常侍温子升等群臣,他们或者讲解佛法或者支持、崇敬佛教。第三,如前所论,编撰者当生活在高祖、太宗时期。从这三个特点来看,法琳与此吻合:他是唐高祖、太宗朝最为坚定的佛教徒,撰写《破邪论》破斥傅奕攻击佛教之说,撰写《辩正论》回应道士李仲卿、刘进喜两人贬量佛教之作,最终因道士秦世英的诋毁徙往益州,途中患疾而卒;为弘扬佛法,法琳常奔波于帝王权臣之间,与高祖、太宗辩论,与上层士人密切交往,虞世南为其《破邪论》作序,东宫学士陈士良为其《辩正论》作序。由以上几点推断,法琳极可能就是《佛法东流传》的编纂者。
若以上推测成立,就可以断定《佛法东流传》的编纂时间为武德七年。唐初数部佛教弘法文献中,如《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法苑珠林》等,都会将梁武帝舍道事佛、北齐文宣帝禁绝道法两件事与《汉法本内传》、姜斌与昙谟最佛道论议二事放在一起叙述,以表述佛优道劣的宗教评判。但《佛法东流传》对佛优道劣证据的搜集,还没有关注梁武帝与北齐文宣帝。此两件事被佛教徒关注,就现存文献而言,始于法琳《辩正论》。因此,《佛法东流传》的成书应该在《破邪论》和《辩正论》之间。《破邪论》和《辩正论》都是法琳著述,前者成书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后者成书于武德九年(626)[9]。敦煌卷子《佛法东流传》以武德七年为最近的参照时间,与此正好相合。
《释老宗源》可能对《破邪论》有所继承。《破邪论》撰录时搜集的大量文献,正是《释老宗源》编纂的依据。《释老宗源》之“释教宗源”,以“佛法东流传”的题名单独流传,佛教徒抄录流传至敦煌。至于“老教宗源”,可能因法琳排斥道教的决绝态度致使其过于偏激,为以老子为祖祢的唐代帝王所限制,没有保存下来。
《释老宗源》似乎为当局禁断过。智昇《开元释教论》记述,《汉法本内传》被“明敕禁断”。如前所论,《汉法本内传》占据了《佛法东流传》2/3的篇幅,可能也在“禁断”之列①。智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的成书,也可能与法琳著述在当时被“禁断”有关。智昇出于保存法琳著述的目的,在“明勅禁断,不许流行”的压力下,以续补高宗朝僧人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著作的名义,更换《释老宗源》或者《佛法东流传》著述的名称,改编成《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一卷,顺利入藏。至于《周书异记》、《世传记》引文,以注解形式出现在《汉法本内传》第二品中,为智昇改编还是为后人增添,就不得而知了。但注解与正文混淆,为后代传抄所造成,当无疑义。智昇所参照《释老宗源》或者《佛法东流传》,可能源是贞观十年或稍后《佛法东流传》或者《释老宗源》的修改本。其中有关佛教历史叙述的参照时间已被重新梳理,变南方、北方佛教史为中土佛教史。这样就更符合南、北佛教的融合趋势。
■
参考文献:
[1]梅弘理(Paul Magnin).《佛法东流传》的最古代版本[C]//敦煌学论文集续编(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日内瓦,1981:51-123.
[2]法琳.破邪论[M]//大正藏:第51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970.
[3]智昇. 续集古今佛道论衡[M]//大正藏:第5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97-398.
[4] 耿昇.八十年代的法国敦煌学论著简介[J].敦煌研究,1986 (3):78-88.
[5] 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C]//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76.
[6]陈士强.大藏经总目提要·文史藏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47.
[7]智昇.开元释教录[M]//大正藏:第5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25.
[8]虞世南.破邪论序[M]//董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1400.
[9]张遵骝.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附范文澜《唐代佛教》)[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