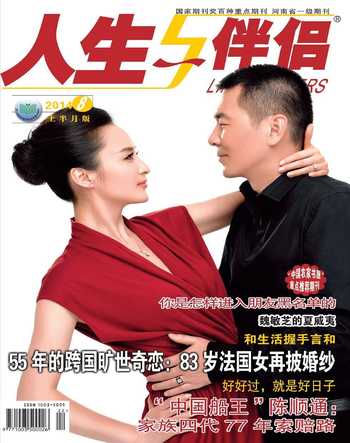“中国船王”陈顺通:家族四代77年索赔路
琴心
传奇陈顺通,建中国首家独资海运公司
189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陈顺通,14岁闯荡上海滩,由见习水手成长为一名技艺娴熟的船长。一次偶然机会,陈顺通救了被军阀追捕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日后,张静江担任了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为报答救命之恩,特举荐陈顺通为国民船运公司经理,为北伐军暗中运送军火立下汗马功劳。
北伐胜利后,陈顺通在上海均泰钱庄优惠信贷支持下买入“太平”号货轮。1930年9月1日,陈顺通的中威轮船公司成立,此为中国第一家独资海运公司。在以后的6年里,中威轮船公司不断扩展新业务开辟新航线,先后从英、澳购进“新太平”、“顺丰”、“源长”三轮,其中的“顺丰”号时为中国最大的货轮。中威公司船只总吨位2万吨,陈顺通被时人称为“中国船王”。后来的香港船王、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当时曾是其助手。
1936年10月14日,应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要求,陈顺通代表中威与大同在上海签订定期租船合同,将6725吨的“顺丰”与5025吨的“新太平”租给“大同”使用。合同规定,从船舶交付之日起,租期为12个月。合同于11月1日生效。为预防风险,中威分别将两轮向日本“兴亚”、“三菱”两家海上保险株式会社投了船体保险。
1937年“8·13”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响应国民政府堵塞航道防御日本大举进攻的要求,陈顺通将中威剩余的两艘货轮“太平”号和“源长”号分别自沉于江阴口与宁波湾航道。
而日本大同租船期满,“顺丰”与“新太平”两轮却下落不明,中威海运业务全面停止。1939年春,陈顺通赴日找到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对方說两轮均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而且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也濒临倒闭。
陈顺通东京之行一无所获,而他在上海维修船只的中威机器厂亦被日本占据。一代船王回到上海大病一场。
陈顺通不知道,事实上1938年12月21日,“新太平”号就已在大同的营运中在北海道触礁沉没。他更不知道,若干年后的调查表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亦早将此船的保险金领取。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顺通凭此信请求国民政府赴日代表团索取被“捕获”的两轮,并向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发信求援。这时他才得知战争中两轮均已沉没(“顺丰”号1944年12月25日在南海触雷沉没)。伤心的陈顺通一病不起。陈顺通当时罹患癌症,明白自己时日无多,在1949年8月8日定下遗嘱,把“讨船”的任务交给了长子陈恰群。
除了责任,交到陈恰群手中的还有1936年陈顺通和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一份租船合同。从那时起,这份租船合同,就是陈家人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物品。“中国船王”陈顺通,于1949年11月14日病逝。
受“船王”嘱托,儿子陈恰群赴日打10年官司
1958年,陈恰群自上海迁居香港,并重新注册中威轮船公司。也因此,这份珍贵的租船合同以及其他重要的原始文件得以完整保留。租船合同就好像家族的命根子一样。也因为保留好了这份租船合同,陈恰群后来才得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日本政府。
当时,他的母亲、妻子、孩子都在上海,而陈恰群的选择是,离开家人去完成父亲的遗命。此后,他21年都没有回来,和家人全靠书信往来。
陈抵港第一件事就是与日本大同联系。他注册的中威轮船就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把官司打下来。而大同每次都以人事变动和船只为日本政府夺去,应由日本政府负责等作答。
心有不甘的陈恰群1961年奔赴日本,开始了漫长的索赔之旅。他根据大同海运株式会社1940年的信向日本政府索赔,不断在日本外务省、大藏省、日本递信省之间奔波。日本政府经1961年至1964年的漫长调查后做出答复:两轮被日本政府“依法捕获”一事查无实据,不予认可。
陈恰群聘请曾代理韩国向日索赔获胜的日本著名律师绪方浩做自己的律师,绪方浩建议与日本政府打官司,陈遂委托绪方浩组织4人律师团起诉日本政府。
1964年到1967年,日本东京简易裁判所受理关于中威公司与日本政府的民事调停。26次调停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政府答辩:此两轮是否为日本“捕获”情况不明,拒绝做出赔偿。
1970年4月25日,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日本政府,“陈恰群诉日本国”成为上世纪70年代日本轰动一时的报道。
不过,此案开庭所需的巨额费用让当年的“船王”之子陷入窘境时,幸得有“日本良心”之称的绪方浩的资助使得诉讼能够进行。
经过数十次庭审,1974年10月25日,10年为此案付出全部精力并花费60万美元的陈恰群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判决:时效消灭。这个结果又让陈恰群大病一场。
10年日本诉讼被画上句号。日本律师要求陈恰群在东京高等法院继续上诉,已经拿不出钱继续上诉的陈恰群被视为撤诉。
在日本奔波十多年,花费60万美元打官司的陈恰群肝肠寸断。为了履行家族责任,陈恰群变卖了家中很多珍贵的古董,而公司收益也大多花在了打官司上。1985年,陈恰群积劳成疾,67岁时不幸中风。
尽管这场官司陷入困局,但陈恰群把希望放到了儿子陈震和陈春身上。中风之后,陈恰群立下遗嘱,要求陈震和陈春代替他继续索赔。遗嘱中写得清清楚楚,官司打赢之后次子陈春要重新组建真正的中威轮船公司,恢复祖业船运。索赔款中大部分应用于家族事业,其余的赔款应照顾好陈家的兄弟姐妹。
“船王”第三代:长达20年的诉讼终有定论
陈恰群日本索赔失败后是漫长的山重水复。但1987年1月1日颁布施行的《民法通则》为陈氏带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因《民法通则》的时效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凡是在《民法通则》颁布前民事权利受侵害未被处理的案件,在《民法通则》颁布后的两年内提起诉讼都有效”。中威船案可在中国本土受理。
陈恰群已于1985年8月中风半身不遂,将中威船只索赔案的接力棒交到了第三代人陈震、陈春兄弟手上,陈氏兄弟以北京中国法律中心为诉讼代理,于1988年12月31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向日本公司追索“顺丰”轮、“新太平”轮船
租金及经济损失。
这次在中国本土打官司,陈氏家族组织的律师团人数创造了中国民事案的纪录。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美国法学界名流的律师团和顾问团成员总数多达56人。
而这个教科书式的异常复杂的案件,此时的被告则由日本政府变成了日本的企业并且被告对象一变再变。因为律师团仔细研究后发现,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当年对“船王”陈顺通称两轮被日本政府“捕获”无任何证据,是欺诈行为,应负全部赔偿责任。
但是,当年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20世纪60年代并入日本海运,日本海运又在20世纪80年代并入日本NAVIX LINE(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1999年4月它又被并入日本第二大海运公司商船三井船舶株式会社。
不但被告在变,原告亦在中途由中威轮船公司加上了陈震、陈春两位自然人。
此案于1991年8月15日第一次开庭审理,到2003年11月26日,一共5次开庭。可由于年代久远、文书材料浩繁等种种原因,一直到2007年,法院才做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赔偿款项折合人民币约1.9亿元。2010年,该案二审终结,维持原判。在被告向最高法提出再审申请被驳回后,法院于2011年依法发出了“执行通知书”。
长达20年的诉讼终有定论,但案件仍未终结。遗憾的是,老船王之子陈恰群并没看到最终的结果,他1992年4月在香港去世时,两个儿子都在身边陪着他。当时陈恰群老人紧握拳头,已经无法说出话来。其实他就想打赢官司出一口气,希望儿子们帮他出这口气。他和父亲陈顺通一样,是在愤愤不平中离开的。
更令人遗憾的是,2012年3月,同样是耗尽了一生心血后,70岁的陈春因为突发心梗在上海去世。此时,他和哥哥虽然打赢了官司,但因难以跨国执行等原因,上海法院判决的这1.9亿元的赔偿款,日方并未交付。
拿到2.4亿赔偿款,曾孙为“中威船案”画上漂亮句号
陈春去世,给儿子陈中威这个原本普通的数学老师出了一道选择题——是继续过简单的老师生活,一家4口过着平常的日子,还是接下父亲的接力棒,继续扛下家族的使命?
陈中威原本的兴趣就是当老师。父亲突然离世,家族的索赔案虽然大局已定,但判决何时执行、索赔款何时拿到却尚无日期。
在家族的紧急会议上,包括伯父陳震在内的长辈认为,陈中威是第四代中的长子,也了解船案,而且名字中又有“中威”,应该承接责任,负责之后的索赔。于是,家族的接力棒交到了陈中威手中。
陈中威选择了“家族使命”。“我喜欢当老师,有朝一日可能还会回去教书。但是我有这个家族使命,我希望对父亲有交代后再去做自己的事情。”
或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半年前,陈中威全家定下了陈春(骨灰)在老家下葬的时间,是4月20日。彼时,距离陈春亲笔写下提交判决强制执行申请已经两年半,何时会执行,陈中威并不知道,只是等待。巧的是,2014年4月19日晚上,陈中威忽然接到了律师的电话,告诉他为执行生效判决,就在当天,上海海事法院已经正式扣押了日本商船三井公司一艘28万吨的轮船,作为赔偿原中国中威轮船公司在二战期间遭受的财产损失。
“那种滋味什么都有,激动、复杂、欣慰,太奇妙了。”4月20日,陈家30余口人驱车前往宁波,参加陈春的下葬仪式。在车上,陈中威宣布了这个消息。
4月20日,宁波下着淅淅沥沥的雨。1969年出生的陈中威捧着父亲陈春的骨灰盒,眼泪默默地顺着脸颊淌下来。他对着骨灰盒轻声说着话:“爸爸,你放心吧,法院已经强制执行了。”安葬完父亲,陈中威和其他30多位陈家人发现,下了一天的雨停了,阳光从云缝中透了出来。在离这块新墓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国第一代“船王”、陈中威的曾祖父陈顺通的墓地。
4月23日,日方公司主动支付了40亿日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表示尊重法院判决,尽快解决被扣货船问题。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首起胜诉案!消息传出,引起世界关注。
前后77年、跨越两个世纪;两份遗嘱、四代人的接力,这个家族传奇故事,终于画上了漂亮的句号!
编辑 / 孙鲁宁
(E-mail:sln90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