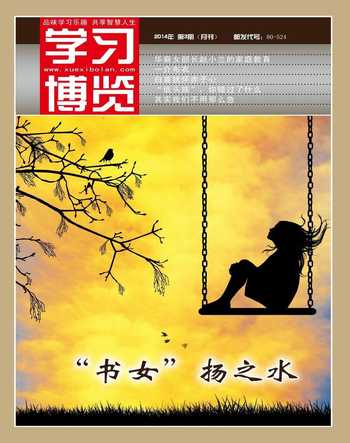“烂英语”才是全球语言
苗炜
90年代初,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跑到人民大学转了一圈,校门口假山石后的小树林里,就是当时颇有名声的“英语角”,树林里有百八十人,三三两两地聚集着,我凑到这圈里听听,再凑到那圈里听听,到最后也没好意思加入谈话,讪讪地离开。过了些日子,我转移到了人民大学对面的理工大学,参加“实力英语”的托福培训班,教课的老师叫宫东风,当年的名气可不在俞敏洪老师之下,班里的同学大多打算考托福,拿奖学金,去美国念书。
我当时不知道,法国人正掀起一场抗击“美国文化”入侵的运动,目标直指巴黎郊外的“欧洲迪斯尼乐园”,一位法国戏剧导演说,示威者应该在迪斯尼乐园点一把火,那是“文化上的切尔诺贝利”。1992年7月,250名法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和诗人,上书密特朗政府,要求“光大法语”,在教学、会议、电影中使用纯正的法语,“御英语于国门之外”。
转眼到了2008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还在学习《新概念英语》第二册。这一年,卢旺达政府忽然宣布,该国对外交流将使用英语,学校里要教英语,那些父母都说卢旺达语的孩子,也要学英语。有评论说,卢旺达弃法语改英语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埋怨法国政府没能阻止卢旺达大屠杀的发生。但卢旺达负责产业和贸易的部长说,“只有法国人说法语,还有西非的部分地方,和加拿大和瑞士的部分地区,说英语的地方要更多,英语正在成为全球语言。要加入全球化进程,就要学英语。”2009年,继马达加斯加之后,卢旺达申请加入英联邦,这是“后殖民时代”语言的力量。
我学了20多年英语学得痛苦不堪,忽然有一天,有个人跟我说,现在的孩子瞎学什么英语考什么听力啊,电视里要是有CNN,有HBO,看电视就行了。我觉得吧,电视里没有CNN,没有HBO,互联网上没有GOOGLE,都是抵御文化入侵。咱们是大国,得有大国的风范,不能像新加坡似的,领袖总嫌国民英语不好。
李光耀毕业于剑桥,1970年代,在新加坡推行“英语优先”政策。新加坡是个语言混杂的国家,马拉语、中国话、英语、泰米尔语都被民众使用,中国话里又有广东话、潮州话等等。1978年,李光耀上电视,专门讲“新加坡式英语”的问题——我们说的英语不够纯正,新加坡人讲英语不够完美。他举例说,新加坡式英语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是,说完一个句子,总要加上LAH这么个音节。1979年,新加坡政府又发起了一场“讲好普通话”运动,想让那些说潮州话、客家话的华人都讲普通话,这一运动没能持续展开。1987年,新加坡政府规定,不管小孩子在家里说什么,到了学校一概用英语教学。2005年,李显龙总理又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地说好英语——在家、在工作中、在社会活动中。我们可以用新加坡口音来说,要表达完整,不要在句子结尾还要加上Lahs\Lors这些音节。看看新加坡,政府讲了20多年,领导人那么重视,句子结尾还老是“啦啦”的。
咱们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阵英语热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前有一档英语教学节目,叫Follow Me,里面有个花老师Kathy Flower,80年代红极一时。如今花老師退休,生活在法国,有个叫《英语的故事》的纪录片采访了花老师,花老师说,中国人学习英语文化的热情是我20年前不能想象的,中国家庭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很多家庭都愿意在教育上花大本钱。不过,你要离开城市到农村看看,你会发现,数亿人能完成基础的母语教育,就已经是毕生了不起的成就了。
英语的霸权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有一位法国人奈易耶说,他在IBM工作期间,发现母语非英语的巴西、韩国同事,只用1500个单词就能顺利沟通,英语不掌握在英美人手里,而是掌握在全世界人民手里,英语不是“全球语言”,“烂英语”才是!
(摘自《新民周刊》)